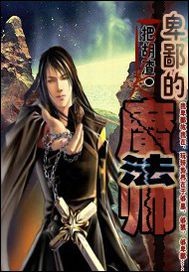谁都没料到,他这样一个怯弱之人竟然能干出这样的事。
此时一个坚硬而冰凉的东西击中了托尔的额头。绿色玻璃碎片从额头上向四方飞溅,在闪动的营火光雾之中像雷电一般危险地飞过。在托尔尚未弄明白,这是弗兰克的一个同伙用空香槟酒瓶对准自己的脑袋砸过来而破碎之时,他就已经感觉到有热乎乎的浓血从自己的左眉毛上方流下。他心里希望,在自己被头晕目眩和疼痛击倒并且暂时跌入之前,一个瞬间内便能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稳。
然而看起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问题。
他只是短暂地感觉到左眼有些不舒服———短暂地绷紧,犹如一种痉挛,仿佛这痉挛之魔在抵达不该造访之人的不该造访的身体部位之后,发现自己找错了目标,于是便像它突然到来那样,仅仅持续了半秒钟便突然消失了。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会不会是因为他陷入了休克状态,故而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呢?
那个弗兰克的同伙一时之间也被搞懵了,他看一眼还一直握在自己手中的瓶颈,又看一眼托尔,在他脸色变得煞白,扔掉破瓶颈,在托尔面前倒退着溜走之前,他就这么左一眼右一眼地来回看了好一阵子。
史黛拉则呆若木鸡一般站在旁边,她双目圆睁,不知所措地盯住托尔,同时,她的嘴巴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大张着。
难道真的只是由于极度震惊而使得托尔呆呆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吗?难道是由于极度震惊而使他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巨大力量,因而砸碎了弗兰克的颌骨吗?他竟然打伤了一个人,这到底怎么回事!要不然就是某个恶魔侵占了托尔,以他把自己的灵魂出让给它为代价而使他获得力量?
起码在这一瞬间里,所有人都瞪着托尔,仿佛他被一群魔鬼迷住了。
托尔转身便跑。直到树林里的黑幕将他完全笼罩住,才放慢了脚步。走到林间空地与宿舍之间大约一半的地方,他跪了下来,让自己羞愧与惧怕的泪水涌流而出。
他本以为自己这个样子蹲在树林里哭泣已经很久了,可是当他最后重振精神站起来继续朝前走的时候,他却断定,自己在此处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他到达修道院绿荫的时候,史黛拉气喘吁吁地从他身后的矮树丛中钻出来,她只比他晚到一点点儿。
“托尔!等一下!”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但托尔并不停步,反而加快了步伐。他为自己感到羞愧,羞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此时他必须直视她的眼睛,那必然是极其痛苦的一眼。尽管如此,她还是追上了他。
“现在你给我站住!”她抓住他的手腕,同时停下自己的脚步,这样一来,他就只能站住不动了,因为他不想强行挣脱她的拉拽。这辈子他再也不会用暴力来对待任何人了,即使是为了自卫也不采取暴力。
“滚开!”他不时用暴力而是言语粗暴地对她吼道,“你不要过来打搅我行不行!”
史黛拉满脸关怀地看着他,松开了拉着他的手。托尔一转身便急匆匆地往前走,史黛拉依旧固执地紧跟着。
“我很抱歉,托尔。”她小声说道。一听此语,托尔站住不走了。
她有什么要道歉的?难道她邀请自己跳舞就是为了要激怒弗兰克吗?是为了让这个理该遭到狠狠诅咒的十足的大坏蛋明白,她并非他的私有财产吗?哦,对了,他曾发现,她斜着眼睛从舞池向弗兰克投去轻蔑的一瞥,而他当时正处于兴高采烈的情绪之中,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瞥后面的含意。如果她所指的就是这一点,那她道道歉也无妨。
“是的,我的行为确实不光彩。”史黛拉与他肩并肩走着,还无可奈何地耸起肩头。“我本来就该想到,弗兰克这样的傻瓜会因为受到这样的刺激而大动干戈的。”她满怀期望地从侧面打量着他。“我很抱歉,真的。”见托尔没有反应,她便又说了一句,同时又一次使劲把他拉住,满怀关爱地抚摩他的脸庞,还以谴责的目光察看他眼睛上方的伤口。“现在还是让我来看看你这倒霉的脑袋吧。”
他很勉强地让她察看自己的头部,心里却对她的触摸大为反感。他在心里谴责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他绝对不应该参与这一切,他绝对不应该让一个姑娘触及自己的内心。他原本应该坚守住斯图塔对自己无声的期望。他绝对不应该脱离修道院的庇护与安全环境,他应该完完全全集中精力毫无危险地阅读往昔美好时代流传下来的那些尘封已久的发黄文献。
真可恨。他刚刚开始认真考虑离开斯图塔的问题,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刚强足够成熟,能够踏进外面的广阔世界了。可是,才走了多远呢?走了还不到一千公尺,就可悲地失败了!
“这……怎么根本就不出血了。”史黛拉一边用手指轻轻抚摸伤口一边困惑不解地说。
托尔摸摸自己的额头也莫明其妙。由于挨了凶狠的一击,他反而没有感觉到本来肯定能够感觉到的疼痛,不过他知道,自己确实被酒瓶狠狠地砸了一下。当时他分明感觉到有血从额头上滴落下来,把他的衬衣领子都浸透了。可是现在,即使他把伤口都摸遍了,手指上也没有沾上一点儿血。
“我们得去找医生看看。”尽管如此,史黛拉还是作了决定。“你得让医生检查一下。”
“我不知道……”托尔流露出很不情愿的表情。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找医生看过病,而他对冒险的兴趣,假使他心里还有冒险兴趣的话,也还隐藏在潜意识的某个阴暗角落里暗自落泪呢。
托尔还从来没有看过医生,因为他从来没有生过重病,重到斯图塔无法在最短时间里护理他恢复健康的病。斯图塔所使用的,是修道院的应有尽有的自备药房中的草药和药酒,药酒的颜色看起来虽然很奇特,但是往往很有效。尽管史黛拉并不隐讳不相信托尔所说的,但她还是毫不松懈地继续扮出微笑的表情。
此刻,在托尔克服了由于今天晚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而引起的最初的恐惧之后,又能够以正常的心态与史黛拉四目相对了。他尽量克制自己,不要太长时间地注视她那对美丽的蓝眼睛,以免自己的下身出现强烈的骚动感,甚至于最后还有可能嘴角流涎而无法控制。
托尔把还没到来的医生想像成一位仪容高雅,银发闪亮,光彩出场的老先生,这种人都会以正派人的心理,同情任何一个牛皮癣患者或者长着两只招风耳的同类,他们除了掌握医疗技术诀窍之外,还具有心理学家与社会工作者的全部品质。或者他是一个戴着口罩颤巍巍而来的容易发脾气的卖肉师傅,手里硕大的药瓶中有毒的绿色液体还在滚滚沸腾,走过来像强盗一般袭击病人,没有洗干净的胖手指在患者的伤口上胡乱抓挠。
实际情形却与托尔的想像完全不同。
片刻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位年轻的长发男士,他走进治疗室的时候,情绪欢快地哼着曲调。他那三天刮一次的胡子,调皮孩子似的笑脸,新潮款式的衬衫,如果不算他身上穿的那件敞开未扣的白大褂,托尔所想像的医生的识别标准,他一条也不占。
“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此人微笑着开口说道。看起来,此男比他俩根本大不了多少。“刚才我处理了一个嘴巴被打坏的伤员。”
由于此话勾起了托尔心里对自己所干的坏事的记忆,在刚刚过去的几分钟里,他竭力把这段记忆从意识中消除掉,他的胃都开始紧张得难受,但是使他的精神备受折磨的,却不仅仅是他的良心不安。他与史黛拉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
“他还在这里吗?”他扭头问医生。
各位,上推荐再次奉上3000字。书扑街扑的的吐血,能不能给个票票,不成收藏一下也行呀!起码留个言让我给你加个精也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