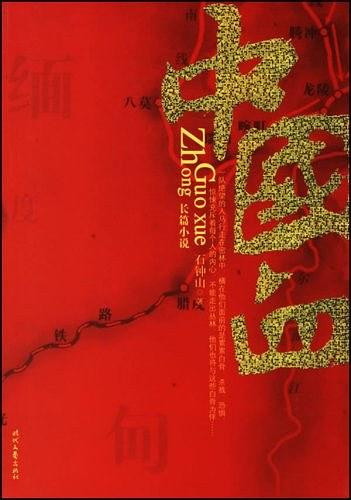东陵677年
富平镇,徐记面铺。
一口棺材突兀的放在街边的面铺旁,过往的几个行人都纷纷回头张望,在这样一个小镇里,将一口棺材突兀的放在路边不是个常见事,毕竟正常人也不会随意的将棺材放在路边。棺材朴实无华,也不像是什么高级的木材,不过说来也是,这么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靠种地做小生意维持的镇子,能有什么人能用的起高级木材。
小男孩学着父亲的模样,拿着擀面杖满街跑,裤脚上全是土,鼻涕挂在嘴边,脸上的面粉扑在脸上像只小花猫。有的时候拿着擀面杖敲一敲棺材板,还会被父亲呵斥一声。
一老一少坐在路边的桌前,老者将依旧热腾腾的面碗放在已经被摩擦地有些光滑的桌面上,碗中只剩一层汤底,汤底虽清淡,却还飘了一层薄薄的油花。
老头子心满意足的砸了砸嘴,长舒了一口气。
“这家面铺三十多年前就在这里,那时还是他老子做,现在这小子接了他爹的手艺,味道没怎么变,可总是差了点滋味,还是功夫没到家啊。”
年轻人却捧着碗将汤底喝了个干净,他打了个嗝,一边发呆,一边回味面汤的滋味。
“你还挺挑嘴,我觉得挺好。”
老人意味深长的笑了一下,道:“吃好了就上路。”
“掌柜的,结账。”
“来咯来咯。”在面案前擀面的中年男子笑着招呼一声,拍了拍手中的面粉,在腰前的围裙上蹭了蹭:“二位客官,两碗面,一碗素的,一碗加肉沫,一共二十五文钱。”
年轻人在怀中摸了摸,摸出二十五个铜钱,放在桌子上。
老板接过钱笑道:“二位客官看上去面生的很,不像是本地人啊,听刚刚老爷子的话,是吃过我父亲做的面了。”
年轻人笑道:“老板你别听这老爷子胡说,他嘴挑事多,我觉得你做的就好得很。”
男人腼腆的笑了一下,说道:“老爷子说的没错,我虽接下了父亲的手艺,到底还是差了一点,功夫不够。”
老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站起来,看上去像是要摔倒了一样,面铺老板下意识的伸了伸手,想要扶一把,但老者并没有摔倒,身边的年轻男子也并未伸手去扶,只是自顾自的将放在手边的一把黑色的剑挂在腰间。
年轻男子站起来活动了一下筋骨,抻了抻胳膊。
面铺老板张了张口,想要说些什么。这一老一少来吃面的时候,就带来了这口棺材,可是当时是从棺材匠家里用驴车拉出来的,放在路边之后,年轻男子就将驴车送回去了。现在倒好,不知道这口棺材要怎么拉走。一口棺材就算用的是最次的木材重量也不轻,现在没了工具拉走,总不能一直放在自己家面铺跟前吧。一直放着,还有谁会来自家吃面。
面铺老板正在犹豫着怎么开这个口,便见到年轻男子走到棺材边,弯下腰,伸出右手,抓住棺材的底部,便一把将一端抬了起来。随后利用巧劲,反手一翻,便将整个棺材扛到肩上。
面铺老板简直要惊呆了,连他那个只知道拿着擀面杖敲敲打打的儿子都吓呆了,一条晶莹的鼻涕顺着鼻孔滴到嘴边。在这个闭塞不通的小镇,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人。
年轻人身形清瘦,却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仿佛身上扛的不是一口棺材,而是一个没什么重量的布袋子。他挥手跟老板示意了一下,便转头跟上老头子颤颤巍巍的脚步,两人的背影向着街口渐行渐远。
有周围的熟人靠过来,瞄了一眼渐渐走远的两人,悄声问道:“这两人不是我们镇子上的,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面铺老板没说话,只是呆愣的摇了摇头,是啊,他们这些地方的人,怎么能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呢。
拓苍山,赤妄峰上。
少年深深呼了一口气,将手中的铲子插在一边,跌坐在草坪上,无奈的看了一眼面前刚刚修整好的坑,叹了口气。
“嗯?富贵儿?怎么停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坑底响起。
少年忍不住翻了个白眼,躺在草坪上,说道:“当然是把那些你觉得碍眼的坑坑洼洼都铲平了才停了。”又小声的嘟囔道:“糙了一辈子了,临了临了,还讲究起来了。”
老人似乎不甘心,又叫嚷起来,枯木般的手指不停的敲着身边的木板:“富贵儿,给为师匀点酒。”
少年似乎在极力忍耐着不耐烦,将腰间的酒壶解下来,扔进坑里,抱怨道:“老头子,都躺到棺材里了还不能老实,你这棺材板可是我费了牛鼻子劲才从山下背上来的,给你挖个坑,你还毛病多的不行,非要在山顶上埋,你这不是故意折腾我吗?还有,你都要死了,能不能别再叫我富贵儿了,我老子给我取了个这么正直的名儿,你倒好,给我取了个狗名儿,一叫就是十几年,现在你要死了,就不能正常叫我吗?”
躺在坑底的老者将酒葫芦从嘴边拿开,挂着水珠的灰白色的胡子颤抖着,满意的砸了砸嘴,嘿嘿笑了起来。
“这不为了好养活嘛。”
这老头子老的像一根已经腐朽了几百年的木头,脸上沟沟壑壑,每一条皱纹深的都能夹死一只苍蝇,一口黄的发黑的牙齿也所剩无几,说气话来也直漏风。
在赵公明的记忆里,这个老头子在他见的第一眼时就已经老的不像样子,那时他还在齐州府中,锦衣华服身边伺候的婢女就有十几个,爹娘叫自己来见这乞丐似的老家伙时,自己还拽了他的胡子。老头子身上永远是破破烂烂,挂着一堆瓶瓶罐罐,颤颤巍巍,拄着一根表面朽的掉渣的拐杖,不过虽然表皮朽成那样,敲到人身上还是很疼的。
这个老头子活了多久,赵公明不知道,不过他推测怎么也得有个一百二三十年了,老的像长过了季节的韭菜,硌牙。
老头子老成这样,一身破破懒懒,嗜酒如命,冬天身上有点钱都让自己打酒去了,喝个酩酊大醉,倒在路边,赵公明还得坐在一边看着,免得让老头子冻死了。这老头子别看老的都缩成一个虾米,站起来还不到赵公明的胸膛高,可就是出奇的重,赵公明怎么抬都抬不起来,只能坐在路边,免得他冻死了没人收尸。
老头子将酒壶里最后一滴酒倒进嘴里,又控了控,实在是没有,终于恋恋不舍的将酒壶抛了出来。
赵公明挤了挤被风迷了的眼睛,说道:“满意了?”
老头子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像是嗓子里卡了痰,最后发出了一声满意的叹息。
赵公明松了口气,双臂枕在脑后,躺在草地上。头顶白云略过,他眼睛有些干涩,合上了眼。
血,满眼都是血。有人在尖叫,冲杀声,兵器相撞的声音不绝于耳,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男人的怒吼,女人的尖叫,粘稠的血液从门缝里溢出来,顺着青石砖缝流到湖里,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死人,男人、女人、孩子。
女人嘶哑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公明,跟着先生快逃!快离开这里!不要回头!不要回头!”
他看不清女人的面孔,内心恐惧至极,忽然,几把雪亮的枪头刺穿了女人的胸膛,血从女人的口中涌了出来,女人张了张口,喉间发出沸水煮开的汩汩声,口中的血水似是要将女人溺死。
“公明...快逃...”
枪头猛地从女人的胸膛拔了出来,女人踉跄了一下,正面摔在地上。他想嘶吼,但恐惧让他张不开嘴,有人拉扯着他离开。
“公明......”
“公明!”
“富贵儿~”
赵公明猛地睁开双眼,鼻腔中的血腥味猛地消失,空气中满是风吹起草屑和泥土的气息。一小块草屑被他吸进鼻孔里,他坐起来,猛地打了喷嚏。
赵公明揉了揉鼻子,看向坑里躺着的老人,耐起性子问道。
“什么事儿?”
老人笑了笑,说道:“富贵儿,我就要死了。”
少年翻了个白眼,又躺了回去。老头子经常说自己要死了,老是挂在嘴边,自己都听得耳朵起茧,虽然赵公明也觉得老头子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了,再不死都要变成老妖怪了,但是老头子虽然老的腰都直不起来,却还是硬朗的很,赵公明甚至有一丝错觉,觉得老头子是不是吃了什么仙丹,说不定自己都不一定能熬过老头子。谁知道这次又要说些什么。
老头子对赵公明的不耐没有生气,只是嘿嘿一笑问道:“乖徒弟,我死了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去?”
赵公明听了,沉默了一下,他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老头子死了以后自己要去做什么,他活的太久了,久的让赵公明以为他不会死,可是人终究会死,肉身总有一天会承受不住岁月的流逝而湮灭。老头死了,这世间可就真的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他想起了那个梦,也许自己活下来,就是为了那个梦。
“去齐州。”他从口中挤出三个字。
这回老头子没有笑,过了许久,终于说道:“算了,终有这一日。你身上挂的玉坠子,是你父亲的东西,去了齐州,若是你还能活着回来,无处落脚,可以试试去嬴州找你父亲的昔年旧友拓跋邵。”
赵公明摸了摸脖子上挂着的玉坠子,这粒湖蓝色的玉坠从自己跟着老头子起就一直戴着,色泽莹润,触手生凉。
老头子说话漏风:“我带了你十三年,该教的都教了,后面的还是要靠你自己,那把刀你就带着吧,师父我身上也没什么钱,就剩十几两,你带上吧,齐州路远,怕是不够,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赵公明皱了皱眉,总觉的这次老头子是认真的,他爬到坑边,看着躺在棺材里的老头子,问道:“今儿个怎么这么认真?不会是真的不行了吧。”
老头子嘿嘿笑道:“凡人皆有寿数,我活了这么久,早都已经活够了,就等着哪日富贵你修为武神,见了真龙,渡我飞升做神仙去。”说着老头子用干柴般的手指解下腰间的一个磨得不像样的布袋,递给赵公明。
“这世间哪有什么神仙真龙,不过是史书世人杜撰罢了,你可是又唬人。”
赵公明嘟囔着接过布袋,掂量了一下,看了看,里面不过几颗细碎的银子和几十个铜板。
老头子听了赵公明的话,意味深长的笑了一下。又将手伸进衣服,摸了半天,从里面的夹层里掏出一颗拇指节大小的珠子。赵公明眼睛亮了起来,纵使他从前也见过许多世间珍宝,却不得不说,难得见成色这样好的料子。
珠子不知是什么料子,没有经过任何多余的雕琢,只是车成圆形,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不像是这个大小应该有的重量,呈现深邃的紫色,通体晶莹剔透,两边用银子包边裹住,触手冰凉,隔着珠子能清楚的看见自己的掌纹。赵公明奇怪这珠子什么来头,这么多年,自己从没见过,老头子都没舍得把这颗珠子当了,他还以为除了自己背的那把刀以外,老头子可以当任何东西呢。
“这颗珠子不是我的。”老头呲着所剩无几的牙笑道:“这是别人的东西,我死以后,你带在身上,一定会有人来问你要这颗珠子,到时候,你还给他就行了。”
“谁会来要啊?”赵公明对着太阳看这颗珠子,珠子在阳光下散射出璀璨的华彩,像是湖面上投下一枚石子荡开粼粼的波光。
老头神秘一笑:“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赵公明将手中的珠子抛到空中再稳稳当当的接住,调侃似的笑道:“呵,不会是你的老情人送你的吧。”
老头露出一抹隐秘的笑容,赵公明觉得脊背发痒,忍不住抖了抖。
“不会被我说中了吧。”
老头摇了摇头,但脸上还颇为自豪道:“老头子我年轻的时候可是有名的俊后生,可讨姑娘们喜欢了,那时候想跟老头子我浪迹天涯的姑娘可多了去了,那一个个长得水灵的......”
老头子越说越飘,表情也逐渐变得迷离了起来,看着倒是挺猥琐。
赵公明仔细端详了那张皱皱巴巴的脸,实在是看不出来哪里跟俊字沾边,他轻蔑的笑了一声:“您可别吹了,就您这张脸,没叫人追着打就不错了。”
老头子并未生气,只是撇了撇嘴,语重心长道:“格局小了,格局小了。”说着又鄙夷的瞥了赵公明一眼,小声嘀咕道:“可不像某些人,这些年纪了,连姑娘的手都没摸过。”
赵公明被噎了一下,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呛声道:“你不说你要死了吗?我看你现在好得很,要是实在没事做,就起来,晚上山上可冷得很。”
老头子咧嘴一笑知道戳到了赵公明的痛处,这个年轻小伙子正为自己的青涩遮掩。
“是啊富贵儿,我要死了。”老头子说话像漏了气,赵公明将脸别到一边,以为又是老头子的把戏。
“从前我教你剑法,你虽顽劣,但也算勤奋,好歹是没白费了我一番苦心。”
老头子笑说:“关山漫漫,云水长长,凡间种种,皆是虚妄,我已将你养大,无愧于赵昶夫妇,且看日后,你如何来见为师吧。”
山顶的风忽然停住了,赵公明抬头看向天,流云依旧,他低下头,看向坑里,犹豫了许久,开口唤了一声。
“师父?”
长久的没有回应,高空中一只白鹤略过,发出一声长唳。赵公明感到心里空了一块什么,他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感觉身上每一处都在漏气。
“这次没胡说啊......”
赵公明起身,怔怔看向棺内,老头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蜷缩着像一只虾米。
他张了张口,似乎再也问不出那句话。
他将棺盖盖上,将挖出的土填回到坑里,将老头子的拐杖深深的插进坟前。
赵公明看向远处,太阳西悬。他在坟前跪下,郑重磕了三个响头。
“老头子,我且东去,此去一别,不知能否再见。若是我能活下来,十年之后,再来此地给您磕头。”
他起身,将剑背在身后,戴上斗笠,下山行去。
东风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