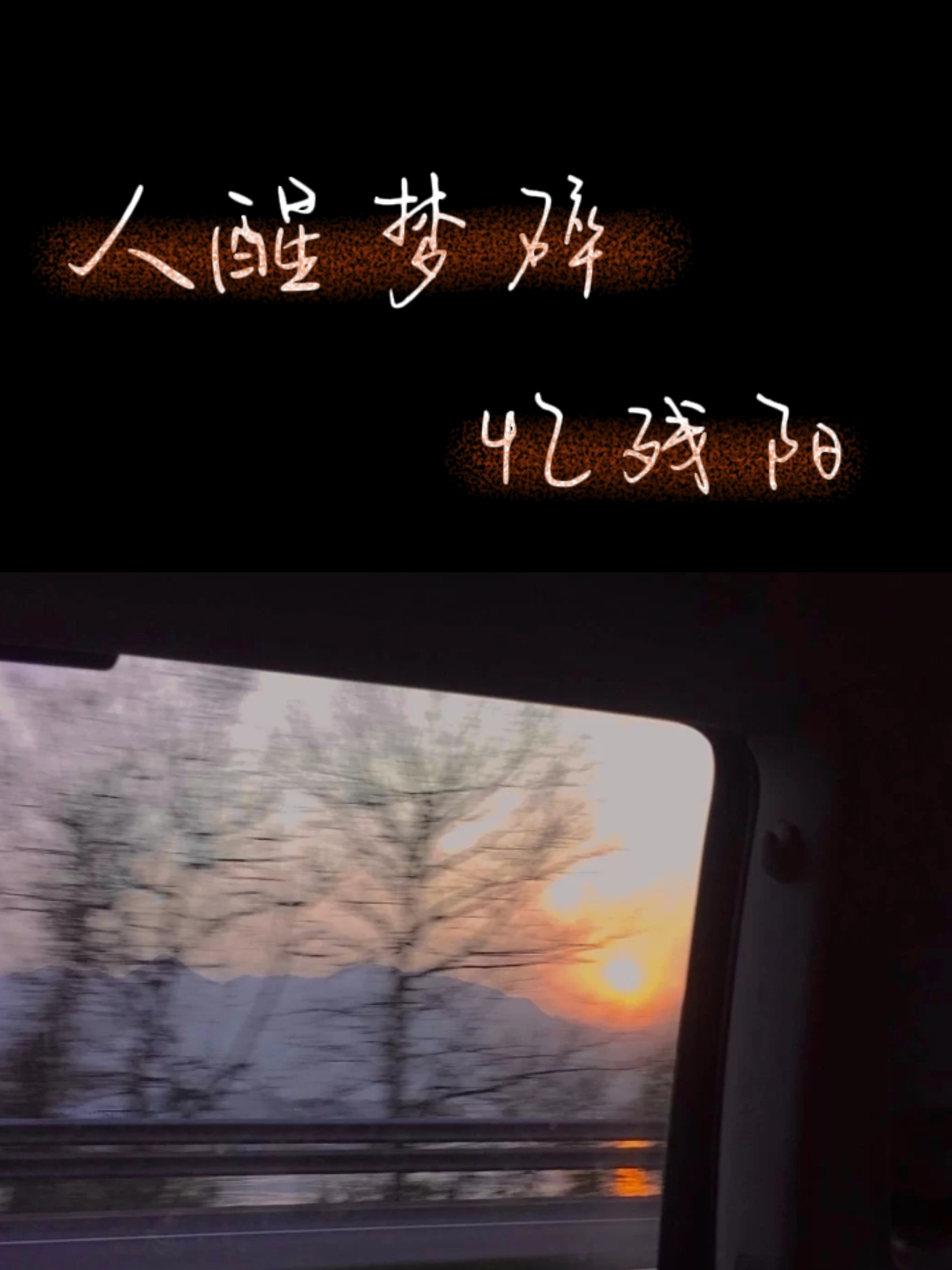河间古镇在外地人眼中,就是一幅生动的水墨画。整齐划一的黑瓦白墙,古朴的灰石路,素衣的街坊们。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感觉到,这世界本不必有太多的颜色,只需要有一处可以安放浮躁的净土。
十岁的柒喜最热衷的娱乐,便是放学后去君子巷里听说书。对她来说,这可比在学校里听老师讲课有意思多了,绝对不会越听越瞌睡。
她从上衣口袋里翻出几个钢镚,买了一小盘花生米。有了消费,自然能从老板手里领到小板凳。坐定的人群中,只见一个瘦小的女娃子抱着小板凳挤来挤去,终是给自己挤出了个靠前头的位置。大人们虽有皱眉却也不会跟个小丫头计较。
“柒喜,你还真在这,快回家看看去吧,你爸被警察抓了。”
柒喜刚要往嘴里送上一颗饱满的花生米,就被邻居家的哥哥拽住胳膊。
花生米掉到地上时她有些恼,当听到后面,爸爸,警察什么的,手里整盘的花生米脱了手,蹦蹦哒哒地散落一地。
跑回家的路上,柒喜的眼泪用袖子怎么也抹不完,妈妈走了,爸爸也要从她身边消失了吗?她暗自发誓,以后再也不听书了,一定听爸爸的话。
柒喜的家门口围着一堆人,呜呜泱泱,叽叽喳喳。不知道谁先看到了柒喜,碰了下身边的人,触发了多米诺效应,大家都安静下来,带着同情的目光看着面前瘦小枯干的小女孩儿。因为瘦,眼睛就显得格外大,因为聪慧就显得眼睛格外亮,也因为害怕和担忧,眼睛里的两汪湖冒得凶,冒得人心里去。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也跟着冒。
“柒喜,你爸已经被带走了,你先跟我回我家去吧。”平时一直没少照顾柒喜的邻居付婶子走过来心疼地搂住她,摸着她的头说。
“我要找我爸,婶子,你带我去找我爸好吗?”柒喜哀求地拽着付婶子的衣服。
“我可怜的喜儿,咱们地方小,有些事想瞒你也瞒不住,你爸犯了错误,被公安带走了。你暂时见不到你爸,乖孩子,先跟婶子回家。”
付婶子知道骗不了,河间巴掌大的地方,出这么大的事儿,用不了半个钟头,便人人都晓得来龙去脉了。她心疼柒喜,亲妈头两年和人私奔了,如今爸又因为杀了人被抓了,这孩子以后可怎么活啊!想到这,她抹了抹泪。
“婶子,我爸犯了什么法?他们凭什么带他走?”柒喜水汪汪的眼睛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正当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告诉她时,旁个看热闹的大孩子喊了一嗓子。
“你爸把人给杀了”。
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杀人就是电视剧里,一个人朝另一个人开了一枪,接着一个人倒下来,死掉了。爸爸又没有枪,没有枪怎么可能杀人呢?柒喜低头想了想,突然再次抬起头对着周遭的人们怒吼起来。
“我爸没有杀人,我爸都没有枪,他买不起枪,去年我想买把玩具枪我爸都说我们家买不起。你们说谎!”
付婶子一把搂住柒喜,带着哭腔说,跟婶子回家,咱等你爸回来。
陶柒喜的爸爸陶晖因为过失杀人被收押等待判决。陶家成了河间茶余饭后的谈资,柒喜每天把自己关在付婶子家的小卧室里。她想回家,可是家没了,她偷听过婶子和别人唠,说柒喜这闺女太可怜了,妈跑了,爸又蹲了大牢,房子又要被卖掉用于赔偿死者家属。孩子连个栖身之所都没了,以后可怎么活。
就在几个好邻居为柒喜的将来担忧时,一个穿着考究,相貌俊秀的年轻男人敲响了付婶子家的门。他说他是陶朗,陶晖的弟弟,陶柒喜的小叔叔。
付婶子一拍脑门记起了这个陶家老二。陶老爷子其实就一个儿子陶晖,陶朗是后来陶老爷子从外省带回来的,说是路上捡来的娃,当年,陶晖二十岁,陶朗十五岁。一些爱打听,爱嚼舌根子的人说,什么地方能捡来这么大的儿子,分明就是私生子。陶老爷子那时候是种茶大户,钱挣了不少,舍得给陶朗花钱,为了能让他上重点学校,花钱走关系,毫不含糊。直到陶朗考上大学以后再没回来,逢年过节也不例外。九年的时光,河间已经遗忘了这么个人。细细打量,确实是当初那个孩子,只是越发英俊挺拔。
“你要把柒喜带北京去?你才20几岁,结婚了没有?你能养活她?”付婶子实在放心不下,眼前的年轻人能照顾好一个十岁的女娃。
“我目前孜然一身,也没有女朋友。在北京有生意,可以给她舒适的生活,供她读书,只要她想,将来出国留学也没问题。”陶朗坚定的目光不容置疑。
“我相信你,可是你这些年为什么到你父亲过世都没回来?”付婶子还是想探探他是不是个重感情的人。
“我当时在国外,不能赶回来。我是陶柒喜唯一的监护人,我想尽快把她带回去,毕竟还要为她做很多安排。”陶朗不喜被过多的询问,干脆站起身来直接要人。
正巧柒喜听到说话声,从小卧室里走出来,因为听了个大概,她大步走到陶朗面前,仰起头信定地说,我跟你走。
她必须走,去北京也好,北极也好,只要离开这里,不再被叫做杀人犯的孩子。
陶朗的心看到这双眼睛时突然失重了一般,他蹲下身直视她的眼睛,找寻了片刻后,释然地一笑。
她太瘦太小了,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要小很多。付婶子心又痛起来,她知道自己不过是个邻居,没权利阻止人家监护人把孩子带走,但是她还是想再确认,要个保证,不然不心安。
“她小叔叔,别嫌我多事,对这孩子我真是疼得很,我想再问问你,你将来也是要成家的,你成家了柒喜咋办?你媳妇能容她?”
“她不成年,我不成家。”
她不成年,我不成家。这句话在多年以后的一天,付婶子见到柒喜时,知道陶朗履行了承诺,不知是欢喜还是痛心,瞬间她明白了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一声唉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