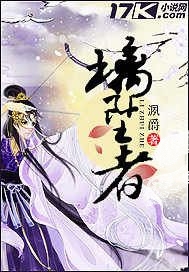楚国在长安的馆驿地处偏僻的西郊,这里既无商贾巨富,也无流民赤贫,于闹市中独辟一处宁静。馆驿外貌是寻常的长安样式,内院却布置着几杆修竹,几株兰花,清雅而不失尊贵。
楚国父子对着刘彻下达的交纳贡金的诏令愁眉苦脸,先是儿子开口了,“父王每次来朝贺都难免被扒一层皮,我们荆楚荒蛮,不像齐国能采盐开采矿山那般富庶。”
“皇上迟迟不召见我们,正在向天下人昭示对我们的不满呢。”这父亲的脸上愁云密布,这皇帝太不好对付了。
“皇帝的特使不是今天来吗?父王尽可探听他的口风。”这儿子凑上来。
“你是不知道这特使是谁呀。”楚王刘道的心情更差了。
门外微风掀起珠帘,吹动了屋内兰芷等香草的气息。身着汉宫华服的女子缓缓走来,在楚王跟前盈盈跪拜,“解忧拜见伯父。”
十年了,她果然长得气度出尘,比起当年的解忧,更有一分宗室女子的贵气。当年的她死了父亲,时常被王宫的眷属借故欺侮,民间上供的珠宝器物送到她屋里已是最下等的,可她是怎样做的?人人都争抢华衣美袍,她却看都不看一眼。
当年的他就心想,这个孩子太傲气了,只怕将来是个厉害人物。刘道本非楚王戊亲生子,宗室对他的继位也颇有微词。而解忧却是刘戊真正的后人,与其留在楚国祸害他们,不如送到长安为质。没想到,为了他这一点私心,却成就了今日的她,如今她真的来祸害楚国了。这算是报应吗?
眼见父亲的失神,楚国太子轻推了他一把,“父王。”
“哦,”楚王咳嗽了一下,“贵使免礼。”如今她都成汉使了。
解忧也不尴尬,在他对面坐下环顾四周,若非刘彻有意的安排,她和这所谓的伯父也不会有机会这般相对。定是刘彻身边哪位智囊给他出的主意,坐观他们楚国宗室内斗呢,解忧心想:千万别让她逮住是谁挑唆的,否则她非要治死他不可。
“自从张骞通了西域,长安人已不大用香草薰室,多半改用西域香料,伯父却丝毫不改楚国习性。”这里熏香袭人,谈笑风生间,却让她隐隐闻出些杀气,多年的习惯已深入骨髓,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住她。
“人老了,一到长安就思念故土。”楚王陪着她笑。长安毕竟在刘彻的眼皮底下,哪里比得上荆楚山高皇帝远的逍遥自在。
“既如此,伯父尽快把那拖欠的十万金贡金献上来,也好早日回到荆楚去。”好一个单刀直入的刘解忧,连过渡都不用就大开杀戒,不愧为刘彻的高徒。
“你!”楚国太子已按耐不住,险些动怒的他被楚王制止。前不久还假扮过这位堂弟,解忧一见他不忍想笑。这一笑更激怒了这位太子,以为解忧有意轻慢他。
楚王哭丧着脸道,“贵使你久居长安,不知道楚国的难处呀,夏季三伏天一半遭了旱灾,水边的又受了洪涝,这一来二去庄稼都不长了,实在吐不出十万金呀。”
解忧最厌恶男子哭诉博同情,一股做戏的姿态,她耐着性子道,“那么伯父能出几万金?”
“最多两万。”楚王见解忧嘴软,立马杀价。
解忧也不含糊,冷笑道,“可是据臣所知,去年山间采摘林中蔬果河中鱼虾收入十分可观,而伯父所说的水灾旱灾根本无足轻重,动不了根本。”
“这绝对是谣言,天大的谣言!”楚王又喋喋不休哭诉起来。
“前方的将士正与匈奴做殊死搏斗,伯父甚为刘氏子孙,理当在此时尽力才是。”解忧咬牙劝诫。到底是骨肉至亲,比不得别家诸侯疏远。若是依着她的性子,保不齐一刀了结了他。
“大将军无往不胜,哪里需要老朽这把老骨头?”楚王推辞着。
“春天过去了,我汉军也不曾遇到匈奴主力,一场小站歼敌两千,陛下的心情不太好呀。”解忧叹口气。
“大将军一味重用匈奴降将。不是本王自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王道。
“看来伯父密切关注着前方的战报,只是不知道后方是否安稳,”解忧不动声色取出一卷帛书,递给楚王,“不知道这卷东西值不值八万金?”
楚王讶然间接过,一打开就吓出一身冷汗,簌的一声收拢帛书,“你从哪里得来的?”
“伯父不必知道从哪儿得来,只需想想,如果这卷密报到了陛下手中,你的王位还能不能保全,我祖父的坟墓还能不能周全?”解忧贴近他关切道。
楚王紧握着帛书的手颤抖着,似在做最后的挣扎,父亲,儿子,孙子,这些人的面容相继出现在他面前,太艰难了!
“好!本王就跟你做这笔交易。”楚王咬牙切齿道。
“伯父明智之极,这笔交易可算大赚。”
楚王看不惯她那得意样儿,“哼!与贵使这样有十分把握的聪明人做交易,能不赔就好了。”
“与伯父这一等一的高手过招,解忧自然要做好十二分准备。”两个人你来我往奉承起来。
楚王心中暴怒到极点,但尚未发作。这间寻常馆驿里,气氛登时古怪起来。
如果他现在动手,有几分把握除掉她?楚王考虑着。他时间不多,解忧已经起身告辞,只有在这里,依旧是他楚国领土一般的地方。一旦出了门,就是她的长安,她的靠山。
他的刀斧手就在门外廊下等待着,他相信解忧也知道。只要他一声令下,他六亲不认的侄女,刘彻的忠心耿耿的臣子就会命丧于此。
杀了她能暂时保住秘密,但难保她没有备份。可这样心思缜密的人,她的备份也不会轻易交给任何人,她有胆量孤身前来,就有把握全身而退。况且,刘彻该有多信任解忧,她若死了,他怎能不追究?
楚王的手停在半空中,终究没有放下。杀了她,就等于与朝廷为敌,杀了她,就没有了后路,杀了她,等于自绝于大汉,杀了她,连祖宗都不会原谅自己。
可算完成了一番重任,解忧走在长安城的大街上却一点也不轻松,前方的战事怎样了?霍去病怎样了?
楚国馆驿里,楚太子一见解忧出了门,摇着发呆的父王道,“父王怎么就让步了?她给你看了什么东西你就怕成这样?”
“儿子呀!她握着的,可是你父王的老命和你下半生的富贵。”楚王拭去额头的汗珠。
“这般厉害?我看看。”说着就去夺他父王手中的帛书。
“别!”楚王受惊吓般收起帛书,“不可看,我们楚国的子孙不可做此大逆不道之事。”
“她连死去祖父的坟茔都不放过,真真世间一等一的恶人,”楚太子感慨着,“如果她是男子,我定要亲手杀了她。”
“如果她是男子,只怕这楚国的王位也轮不到你,”楚王也是心惊肉跳,“不过话说回来,如若她是男子,不等你我动手,当今天子也会杀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