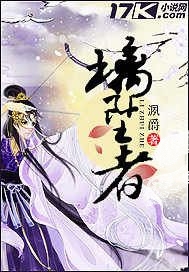刘解忧孱弱的歪在马车里,温热的鲜血逐渐从身体流出,恍惚间带走她不甚清晰的意识。车外是苍凉的荒漠,除却飞沙走石,还有连天的衰草与绝艳的晚霞。
死亡无声逼近,伴随车外马蹄声,她知道他们正俘虏着自己远去。解忧一生不曾服过输,却先后两次沦为胡人俘虏,不可不称之为命运弄人。临近生命尽头,她却毫无恐慌,先前自尽的决心也荡然无存,只剩下枯等。
究竟在等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恍惚间体力不支沉沉睡去。衡玑,数不尽的汉家将士永远留在了那条狭小的山涧上,注定她不会安乐的下半生。
梦中是无尽的喧嚣,震天的擂鼓,汉家的旌旗,巍峨的祁连,还有分辨不清的面孔……
军医看着眼前平躺的女子,她形容枯瘦,眉心紧锁,被撕破的丝帛衣襟上沾满血迹,有她自己的血,也有别人的,新旧血迹融在一起分不清。他的目光最终回到她的左肩,伤口未经任何处理,连日的颠簸也加剧了化脓,逐渐腐烂的皮肉与淤血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异味。这不该是位妙龄女子的身体。
军医的怜悯之心多少左右了他的动作,缓缓先以刀割开她的衣襟,再小心翼翼割开伤口附近的皮肤,箭镞深深扎入身体。昏迷的女子似乎感觉到痛,隐隐**着。
医馆没有犹豫,以铁钳夹箭身,另一手摁住她肩膀,奋力将竹箭拔出。
“嘶……痛……”故人逝去的疼痛与身体的苦楚交错着,生不如死缠绕着她。豆大的汗珠垂下,解忧身子一颤从昏迷中醒来。
榻边的案上摆着一盏昏黄的灯,枯黄的灯光照亮她视线范围内的一切。简陋的军帐,简陋的摆设,肆意横流的鲜血,解忧的血。她猛然意识到身旁站立的陌生汉子正手持利器对着自己。
或许是劫后余生的本能,或许是对生存的渴望,顾不得左肩涌出的鲜血,解忧猛然侧身,一只尚能活动的右手忽然发力摁住汉子的手,“什么人?”
汉子见这半死之人忽然醒来,本已吃了一惊,此刻又被她一瞪,更慌了神,“你,你,你醒了……我,是军医……”
他身材魁梧,举止粗犷,且言语生涩,显然是异族。解忧猛然反应过来,竟大声喝道,“匈奴人!”
军医顷刻间便被解忧制住,手中的铁钳不听使唤咣当一声落地。他从未见过如此凶悍的女子:她目光凶狠怨念而悲愤,似有吃人之意。
想起那些为护驾而死的一百多侍卫,想起倒在血泊中的衡玑,一旦给她力量立即反扑。解忧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了,她声嘶力竭吼着,“匈奴人!不得好死的匈奴人!”
生命危在旦夕,解忧却没有半点恐惧,此时此刻杀一两个胡人也不枉此生。军医拔腿想逃,却被解忧死死拽住动弹不得,只得大声朝帐外呼救。而解忧虽有杀心,却终因伤势过重无从下手。
有军士听到声音闯入,先是一惊,随即上前拉开解忧,高声呵斥道,“他是军医,救你的军医!”
军医被她吓得退开几步,却并未逃出帐子,只在不远处小心观察着。
解忧猛然意识到这里是汉军的军帐,却来不及细问救她的人是谁,指着军医道,“匈奴人!他是匈奴人!我不要匈奴人救我!”
“他是我的军医!”有人闻声闯入大帐,对她怒喝道。
“霍去病?”解忧眼前一亮,先疑心自己看错了,这才意识到自己是真真正正得救了,可她抑制住流泪的冲动,强辩道,“那是杀戮我万千汉人的匈奴人!”
“他是汉军。”霍去病再一次强调。那是归降而来的匈奴军医,对医治箭伤颇有经验。
“不!我不要匈奴人救我!是他们杀了那么多人,杀了衡玑!”解忧声嘶力竭,毫无半点身负重伤的样子。在军士眼里,她竟毫不在乎自己流血的身体和裸露的左肩,披散着头发只顾发狠与将军对峙,活像一只被激怒的母狮子。
“若要活命,只有他可以救你!我没有其他军医派给你。”霍去病明白无误说道,好似扇了她一个耳光。似也在告诉众人,霍去病的帐下没有汉匈之分,只要效力的都是他的士兵。
“哼!你可真大度!”解忧冷冷道,气息却暴露了自己的羸弱。
霍去病没有分辩,只示意军医尽快包扎。
解忧安静下来,发丝无力的遮盖半张脸,虚弱喘着气。军士见她不再发作,便放开了她。那名军医顺势过来为她包扎止血。
在解忧满怀敌意的眼神注视下,那军医战战兢兢完成了包扎的工作。解忧这才察觉自己方才极其失态,侧着身子扯过置于一旁的衣袍披上。
“发生了什么事?衡玑死了?”霍去病拾起她遗落的信息,眼神中并无哀戚,反倒十分疑惑。衡玑,多么不愿提及的字眼,多少夹杂着霍去病曾经的不满。
提起衡玑,解忧泪要涌出,好容易整理思绪平复情绪,怆然道,“陛下驾幸甘泉宫,我和衡玑随侍。岂料匈奴率军偷袭,汉军远在数百里之外,我们既无强援,迫于无奈,只得由我和衡玑领一百多名侍卫引蛇出洞。我们成功引开他们,在落羊涧被他们追击,所有侍卫均被杀害割下头颅。衡玑中箭,她不愿被俘受辱……”
最后几个字含糊不成句,纠缠着她凄凄惨惨的情绪。他无法理解解忧对衡玑的感情与依赖,也无法理解她对此事的内疚与懊悔,如若不是她的大意与轻率,不是她对于感情的怯懦与逃避,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你们引开了匈奴人,陛下安全了。”霍去病冷静推测道,似乎从未将关怀给予眼前这个女子。他在军中并未收到长安任何军令。这事件太过突然,他还来不及悲伤。
解忧点头,这是他们以死相搏唯一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