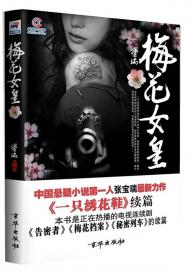公子岩不以为意的嗤笑起来,笑了好一会,方才感叹道:“三娘呀三娘,以前,我总觉得石尉寒是天下第一无趣的人,明明年纪轻轻,做事说话却是一板一眼,一副老古董的模样。枉顾了大好的年华,如今我才发现,原来三娘也是这样的人!”
江子萱并不动怒,完全将公子岩的话语当做对她的赞赏,微微低头,极为诚恳的说道:“多谢公子赞誉!”
公子岩一愣,看着她眼中的认真神色,他再次笑了出来,有别于刚才的嗤笑,现下笑得十分开怀。好似懵懂无知的婴孩般,张大了嘴巴,兀自欢喜。
江子萱看着他,心里暗叹,不怪她当初误以为他是未及弱冠的大男孩,他这幅模样,可不就是天真无邪?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近,即便明知道在他身边就意味着将自己置身浪涛之中。
“呵呵……三娘……呵呵,我收回方才的话,你是天下第一有趣的人!”公子岩说着,一颗乌黑的脑袋又凑到了她的面前,低声问:“你说,这么有趣的你,为何留不住石尉寒呢?”
这话,无异于狠狠刺了江子萱一剑,她双手一握,浑然忘记此时一只手正与公子岩紧紧连在一起,力气大得将指甲戳到了他的手背中。
公子岩吃痛,眸子一冷,却没有自己的手抽出去,道:“三娘,我真是不懂你,既然放不下,为何不去争一争呢?就算有太后下旨,可你和他毕竟有婚约在前,你若是不放手,他石家又能如何?”
江子萱笑了,公子岩的心思他如何不知道,他这是故技重施,用对付谢家的方法对付石家,让她去闹,让江家与石家的矛盾激化,让他们也落下个慕国婚、远世家的骂名。
她想得明白,所以才极早的松了手。只是有些讽刺和心酸而已,以前心里没有石尉寒,从来没有为他考虑过,等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情意,唯一能为他做的便也是成全他和长笙公主了。
公子岩是何等聪明的人?经过这些时日的相处,早已经明白了她的秉性,见她笑得落寞,他冷哼一声,说道:“你倒是为他考虑得周到,只怕他未必领你的情!”
话毕,他方才发现自己话里的酸意,不由一怔,待去看江子萱时,她正侧头凝视被白雪沉沉压住的青松。
他松了一口气,可又有一股子无名的怒火迅速窜了上来,她面对他时,竟然如此的漫不经心!
江子萱浑然未觉公子岩态度的变化,她手捧着一杯温热了的黄酒,借以暖手,而视线漫无目的的扫视周围景色。毫无预料的,石尉寒的背影撞进她的眼中。
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石尉寒独自一人沿着长廊往外走,虽然看不到他的脸,可江子萱却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怒气。而一直陪在他旁边的长笙公主,此刻冷着脸坐在位置上,出奇的安静。
待走到风口时,石尉寒下意识裹了裹身上的狐裘,这个动作,显得他尤为孤单。
眼看着石尉寒消失在长廊的那端,在公子岩欲发作怒气时,江子萱毫无预兆的挣开了公子岩的手,倏忽站了起来,向着长廊方向奔去。
公子岩并未看到石尉寒,只用诧异的目光看着她消失在转角的地方。
她走得急,刚被扫除积雪的石板路十分滑,一个不留神,她嗖的一下滑倒,身体往左前一掼,双手刚好落在花圃之中的枯枝上面。
枯枝刺破了她的皮肉,狠狠插进她的手掌里,立时,火烧火燎的疼痛从手心中传来,疼得她冷抽一口气,再抬头看去,哪里还有石尉寒的影子?
她心下大恸,说不清楚是摔疼了,还是跟丢了石尉寒。
她举起双手一看,手心有殷殷鲜血,几根枯枝还死死插在手掌的皮肉里,样子十分狰狞。
她只觉疲惫异常,也不起来,也不管地上冰凉,一屁股就坐了上去,双眼呆滞的盯着自己的双手。
好一会,她感觉有人走到了自己的面前,顺眼一看,一双厚底的高靴进入眼帘,再抬头,竟然是石尉寒去而又返。
“大郎……”她心里自是高兴,可却不知道能说什么,只是抬着头,痴痴看着他。
石尉寒抿唇与她对视片刻,终于败下阵来,无奈道:“你跟着我做什么?”
“我……”跟着他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江子萱无法回答,她只是看着他消失,着急了,便追了出来。只是如此而已!
她答不出来,石尉寒显然也没有追问下去的意思,斜睨她的手掌,道:“你的手,最好清洗一下,否则伤口若是化脓,只怕有得你疼的。”
“我……我不会。”
“起来!”
她从下而上看他,只能够看到他的下巴和轮廓,至于他的眼睛和神情,对她来说实在是晦暗不明。她甚至不知道,他这般说,是厌恶她,还是出于别的心想!
在她胡思乱想之时,他又冷漠的说道:“回去找公子岩,他可以为你唤来大夫。”
她摇了摇头,脱口道:“大郎久经沙场,可会清洗伤口?若是会,可否劳烦大郎为我清洗?”
她说完,就有些后悔,这样的要求难免无礼!他现下与长笙公主成双成对,她怎么可以生出这样的念头?
她正准备为自己的鲁莽找个台阶,石尉寒出乎意料的弯腰将她搀扶起来,道:“也好,我在离这里不远处有个别院,你先随我去那里吧!”
两个人,心里明明都知道这样的做法极为不对,却都心照不宣的保持了沉默,在赏雪宴会未开始之前,一起离开了襄王府。
襄王府的位置本来已经算是偏僻,靠近北城门,而石尉寒所谓不远处的别院,其实更加偏僻,已经出了城门,在城外的一座小山上面。好在现下天气太冷,城外早已经没有了流民,他们一路上十分顺利。
石尉寒没有用马车,而是与她共骑一匹马,走了很久方才到达。江子萱抬眼看去,这精致的别院,如同他本人一般,毫不虚华却隐隐有贵气透出。院中只有两个不多话、安分守己的老家丁,见到她们并没有多问,这使江子萱紧张的心情得到了缓解。
同时,江子萱心里又生出隐隐的欢乐,这个别院的存在,应该是对他来说极为隐秘的事情,他却肯带她来这里,是不是意味着,在他心里,她到底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猜想,也不过是猜想而已,她没有问出口。
跟着石尉寒进到一间简朴的卧室里,她便老老实实的坐在椅子上,看他驾轻就熟的去取来白布和剪刀,还有一瓶烧酒和一个装着伤药的小瓷瓶。
两人谁都没有开口说话,石尉寒默默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腕,细细查看她手上的伤口。而后,竟然也不打声招呼,就打开了酒瓶子,将烧酒径直倒在她的手上。
“嘶!”,那酒冲到江子萱的伤口,使她本能的倒抽一口冷气,本来就很疼的伤口好似被大火烧到了一般,疼得她只想将手抽回去。
可是,石尉寒的手握得实在是太紧,根本容不得她退缩。
他还是没有说话,眉宇间却带了一丝怜惜,手上的动作也轻了许多,小心翼翼的沿着她的手掌缓缓浇下烧酒。待他将酒瓶子放下后,又拿起白布轻轻按在她的掌心上,将掌上的血水吸干净,露出她手掌的面露,而后才拿了剪刀,开始为她挑出插在手心里的枯枝。
她看着他深邃而专注的眼眸,看着他完美的轮廓及认真的模样,鼻头一酸,眼泪不由自主的就流了下来。
待石尉寒将她的手掌包扎好,抬头一看,发现她满脸的泪痕,一时变得有些无措,好半响才低声问道:“可是我弄疼了你?”
江子萱摇了摇头,不等她说话,他已经掏出了一方锦帕为她擦拭眼泪。
江子萱怔住,木木的看着他,倒忘记了哭泣,也忘记了手掌的疼痛,任由着他为她擦拭,眼睛似有似无的看着他手里的锦帕。
等他擦干她的泪痕,她还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看着锦帕,他有些尴尬,好似拘束的孩童般,嗫嚅道:“我上次……后来……就一直带着锦帕了,没有想到,还真派上了用场。”
闻言,江子萱破涕为笑,原来他特意将锦帕带在身上是为了她。
见她笑,他不由也跟着笑了起来,本来十分刚毅的五官,一下柔和不少,看得她心下砰砰直跳。
笑着笑着,他的目光忽然变得暗沉起来,眼睛似有似无的看向她的唇,身体不由向着她靠近。
江子萱隐约明白他想要做什么,也尚有理智存在,可她忽然不想躲,也不想理会那些令人心烦的现实,就这样呆呆的看着他,看着他的五官在她面前不断的放大,放大……
当他的唇终于碰上 她的唇时,她的心好似被什么东西烫到了一般,烫得她有些难受,又十分贪恋那炙热。
相较于她唇上的冰冷,他温暖许多,轻轻贴着她,什么都不做,已经让她有喟叹之感。
她双眼一直睁着,看着他,看出他的试探和犹豫,她忽然有了向前一步的勇气,生出抛开一切的决心,主动张了嘴,伸舌头舔了舔他的嘴唇。
石尉寒身体微微一颤,刹那,他的眼中生出两簇熊熊火焰,恨不得一口将她吞下肚子去,双手紧紧搂住了她的腰,几欲将她的腰肢掐断,霸道而又不失温柔的亲吻起她来。
江子萱在他怀里,不断软化,软得近乎一滩水,柔柔的贴靠在他刚硬的身躯上面,差点就要不能呼吸,大脑中一片眩晕。
而石尉寒,则是越来越烫,烫得让她心悸。身体随之变得刚硬无比,那样的硬,让她有种想要逃跑却又更想接近的矛盾感觉。
她心里,不是不清楚再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可她将自己那一丝丝的退意全部压制了下去。这一次,大概是她最后靠近他的机会,不管怎么样,她不想与他成为路人,却什么都没有留下。
她这样的想法,实在是有些傻,一边清楚他必然会娶长笙公主,一边又想彻底沦陷这一次。在她看来,未来到底怎么样,似乎已经不重要。
他吻着她,全然没有了理智,有力的大掌不断上移,开始拉扯她的衣服,狐裘上的扣子被他扯掉,他一不做二不休,将她身上的狐裘悄无声息的仍在了地上。
他的额头,溢出大颗大颗的汗滴,呼吸不断沉重,好似在承受极为痛苦的煎熬般。
外面的大雪如同鹅毛般纷纷扬扬的飘在天空中,无声无息给大地再次裹上厚厚的一层。屋子里的火炭烧得很旺,间或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将寒冷完完全全阻隔在了外面,温度热得,似乎令他们两人都无非忍受了。
石尉寒的手,有些乱无章法,只知道要紧紧抓住她,却不想,一下抓住她的手掌,她身体一颤,啊的一声喊了出来。
听到她的惊呼,他方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再看向地上的狐裘,他如同被蛇咬了一口,倏忽放开她,猛然转身欲逃离这里。
江子萱的双手,在她想清楚之前,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一下从后面抱住了他。
他不动了,低头看了看她被白布抱住的双手,眼中有痛苦也有恨意,咬牙切齿的说道:“江三娘,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办?”
他对她的怨恨和不耐,随着这一声问话,清楚无比的传到了江子萱的耳朵,也钻进了她的心里。
她悻悻然松开了自己的手,垂着头,嗫嚅道:“抱歉,是我……蛮横无理了。”
她的心里掀起惊涛骇浪,从他那一声质问中,她终于明白,他真的做了决定远离她,对她恐怕也只剩下了怨恨。而她,却不顾廉耻的缠了上去,这让他感到了无奈。
她想,这就是惩罚,惩罚她以前对他的伤害。如今,无动于衷的那个人,终于换成了他!即便,她想要的,只是回忆而不是未来,也已经令他烦不胜烦,不堪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