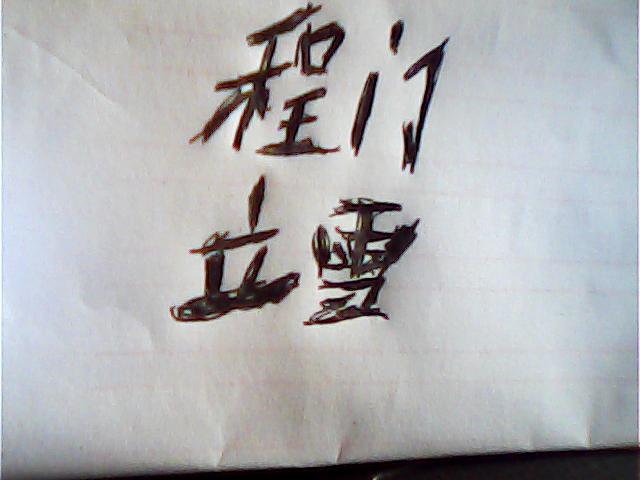旷古的幽风卷携起一缕缕秋的凉意,整个大地渐渐步入萧条景深。
树木还没有落光了叶子,但衰草已经连天。弥弥漫漫、蓬勃浩瀚,恍若昭示着那些离离合合的人世聚散。
轮回兜转、四季交接,如此而已。
云婵的心境,是极平静的。
迎着萧萧寒风,她屈指探手,袖口里指尖贴着青花瓷的感触,带起了那般鲜明的凉。
“自从十三爷去了以后,皇上的生命似也跟着抽空了。”云婵这样想着,眉心却展、面眸寡淡,“他仿佛老却了所有的年华。听宫人们碎碎道着,皇上竟日里除了处理政务外,便一个人对月默看、举杯相邀清风,有些时候往往对着皓月清风一默便是一整夜……这些年来,大家一直都活在没有尽头、无止无穷的漫漫痛苦里,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累了,所有人都累了,不是么?”够了,真的够了,这样昏昏噩噩生不如死的日子,还要继续折磨到什么时候?是时候了,是时候,该结束了,结束这一切了……
她温温如水的目光里霍地沉淀了一道凛然锐利,心口一个紧收,似能拧出鲜红的血色来:“那么,便由我来终结这种痛苦吧!”
汩汩寒风撩拨的宫裙衣袂纷纷飞扬,她抽出了蜷在袖口里的手,掌心处端着一个包裹,外围,是十四爷那方大红绫子图腾汗巾。
她纤纤妙手恍若盛开的兰花,指尖轻点,将那包裹打开,是一个精致的青瓷小瓶。
论道起这小瓶子,原是经年以前先皇在时,她跟九爷调侃时无意间得到的。
那时,她眉飞色舞的开着玩笑,只道想看看九爷那毒药是不是真的。九爷便随手丢给了她。
当初两人谁都没往心上放去,不想到了头,还真真就派上了用场……
这些年来,她一直都把这两样东西带在身边,毒药是无意的、汗巾却是有意的。
焚一炷心香,遥遥祭天。早已不在人世的八爷、九爷、十三爷;还有幽禁中一日一日挨着无边岁月的十爷、十四爷……你们,都还好么?
当年那一场最美丽的初见,潇洒翩翩的十四阿哥便给了她两样东西。金瓜子、以及这方汗巾。
那一把金瓜子一直留在了蘅苑客栈的后墙里,犹如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残瓣一样崩塌零落,是再也没有机会拿回来了。这是她这一生永远遗憾的事情,她又岂能再把这方汗巾弄丢?
这方汗巾,是他唯一留给她的东西了,她最重要的东西了……
是的,没有什么还能再比这汗巾重要,因为没有什么能再比他重要。
时至如今,云婵终于可以毫无怀疑的说她看清了自己的心,真真正正的看清了自己的心!终其一生,原来她唯一爱着的人、一直爱着的人,是十四爷,只有十四爷!
漫天的尘埃与枯叶和风旋转,一层一层萎靡了繁华美丽的紫禁城,埋天葬地的大势头。
素面朝天,她笑颜忽绽。
这一生里最重要的、纠纠葛葛牵牵绊绊了一生的四个男人,四爷、八爷、十三爷、十四爷。
对于四爷,她直到如今都说不清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太过纠葛了、也太过煎熬了。
对于八爷,是一种发自心底的仰慕,或许是一种兄妹之情、和一点点长辈对于小辈的关爱。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情,若论知己,她自知不敢有那份殊荣。八爷的知己,她怕是够不上的。却又分明比兄妹之情更高一重。其实一开始,因为八福晋的缘故,便注定她对八爷不敢再有其它想法,若八爷身边没有这位感情甚笃的爱妻,她又会不会真的爱上他呢?云婵笑笑。
十三爷,则是她的初恋和执念。十三阿哥是第一个出现在她生命里的皇子,自从他将她从掌柜手里救下之后,便仿佛十三的一切都是极好的、极令她欢喜的。那是一种一眼万年的执着情念,以至于日后也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心中所爱的那位良人便是十三。久而久之,便一点一点的认定了去。再久而久之,对十三爷的爱便仿佛蜕变成了一条无需证明的真理;就这般的,从而模糊掉了对身边其他人的真切感觉。把持着这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她似懂非懂了一辈子;到了头,才隐约发现自己守着的不过是一种执念,不是爱。而那个真正爱着的人,却已因当时不懂,生生在此生错过……
对十四爷,是爱,是深爱……当他天天在身边时,并不会明白对他的爱意。只有当那个人离你远去,才可以让你能够得以看清自己的心……可她知道,如果再来一次,她还是学不会珍惜十四,她与十四还是必将错过。因为她的性格如斯。当时不懂、恍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但是没关系,真的没关系。如果三千红尘蒙了眼、障了爱、迷了魂、失了心,便用生命来感悟!
云婵忽觉心下一暖,脉脉暖流甚至跟着浮涌而上、氤氲在了她的软眸里,久违的桃花碧水便开始潋潋流淌。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她突然颔首,一张无限明媚美好的芙蓉净颜染就了和煦生机。她转身行路、莲步折回,着艳紫绣梅枝的华丽宫服,将细眉画到鬓里去,点艳丽的红唇,化最精致的妆……粉面净白、翠眉红唇,怎生得凄美伦常。
然后,她行步出殿,抬手召了宫娥逶迤而去、遣人传话。她淡淡的,又从从容容的,妖娆娇面、含丹盈唇其畔似乎噙着一丝薄笑。那样无波无澜的,她道:“我要见皇上。”
。
风轻轻吹,有枯萎了半个身子的残叶轻轻零落。
静好的书房小间只余下明黄湘帘娓娓晃曳,胤禛已经抬手退了一干内侍。
云婵微微笑起,抬手将一盏鲤鱼雕碧莲的琉璃盏迎着胤禛递过去;胤禛顺势接过,没有多言,仰脖饮尽盏中酒。
一切都是静好如初的,似乎又是一个极平淡的日子。便连云婵忽而扬起的话语,听在耳里都是极随意简单、云淡风轻:“皇上。”她将目光凝在他淡漠无态的面上,浅浅莞尔,“酒里有毒。”
含丹的昙口恍若世上最嗜血阴戾的荼毒,眼前风韵犹盛的女子俨然不再是一个人,已经图腾蜕变成了一个嗜血的邪灵、一个午夜阑珊梦回时降临浊世的女神,一眼过去,便是永无止息的美艳而不祥。
胤禛依旧是极平静的,甚至于说话的口吻听来都没有半点风浪。仿佛只是一个极简洁的发问、极无关痛痒的琐碎调侃:“你就这么恨我?”他似问又近乎叹,因为如是的随意淡泊,反倒冷静的令人心寒。
“对。”云婵临着他的话尾轻声附和,旋而语气陡扬、眉心却展,“我恨你!极其恨你!恨死了你!我恨你入骨,恨不得你死!”她的声音一浪盖着一浪高过去,到了后面几乎在咆哮了。
云婵黛眉紧拧,银牙咬得狠厉无双,铮然抬袖,刷的一指胤禛:“我就是再傻再愚也能明白因果二字。虽然我从来到这个世上之后,便几乎天天都在做错事,但圣祖四十九年旧历新春,我因顾念你的心境而往雍王府去寻你,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最错的一件事,我大错特错!”她周身上下已经开始瑟瑟颤抖,因着心绪叠伏,整个人都在霍然间变得凄厉撕裂、歇斯底里,“我原本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路、可以有虽平淡却美好的生活、可以安稳一世……可是如今呢,我没有亲人、没有爱人、没有朋友通通都没有了!即便我的亲生儿子都不肯认我这个额娘!我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
最后这五个字她言的极慢,一字一顿,却极其铿锵有力,似乎倾尽了毕生所有的、极致的怨忿之能事。
幽幽光影卷起了万般寂寞的旷古冷清,晕成一道绸缎般的织锦,就那么展展的扑洒在胤禛如是清冷绝尘的眼角眉梢。半晌无话,他紧锁的眉头已经泛青,似乎将喧嚣尘世间所有的落寞、所有的寒冷尽匡于蛊中。
迎着这一大片寂寥无边,云婵一张血色全无的面靥突然起了癫狂之态,她仰脖抬首哈哈大笑,犹如一个森森深夜里索命勾魂的怨咒厉鬼。边如此间,她霍地一下伸臂,将雕花小桌上的另一杯酒举起,后仰脖饮尽。
她的动作太突兀,突兀到根本来不及反应、更来不及阻止。一向冷静自持的胤禛也是一震,在她面前他再也做不到不为所动:“云儿……”胤禛抬臂想拦,但那毒酒已经被她饮尽;且在同时,因着药力起了效果,他身子兀地一软,铮然倒在了冰冷的地表。
萎在青砖地面的尘滓霍然间被带起,粘粘连连、飞飞扬扬,像极了一场华丽而庄严的殉葬。
许是这颗心再也支撑不得这个身子,云婵绵软周身再也难有半点气力。亦在一恍惚间,她足髁一萎、曳曳微颤,昙然瘫倒在地,若一朵离了枝头的孤洁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