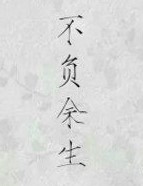是真实么?还是眼前叠生起来的幻象呢?是不是想念太过浓烈、亦或是一个人濒临着死亡的深渊时,便会产生这样至为真切的连贯错觉?这错觉还是那么那么的灵动而光鲜!
云婵莞尔失笑,自己,到底就要死了么?不然又怎会看到如此真切无异的幻影幻象……
原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的人,在蘅苑客栈简单而熟悉的古朴厢房里,她又看到了他。就一如曾经的曾经,那遥远的远不可闻的经年以前,他们两人初次在蘅苑客栈里相见时一样,时今这一眼过去,她依旧会有怦然心动的真切感觉。
那是被他做弄的,她便就这般莫名其妙的跌陷进了他那湾蛊惑心魂的深潭里,就此划不出。
大千世界,任是这般的喜欢做弄人啊!
那是素衣化作缁的十三阿哥。
他着了一件冰青色的锦缎便服,领口袖角攀着深深浅浅的海龙缘图腾,规整且不失通身华贵。他依旧是极俊逸好看的,玉削般的面庞、淡淡的薄唇、如风的长发、素净修长的手指……只是整个人看上去出落的愈发成熟韵味,且偏瘦了一些。怎么都觉眼下的十三爷十分单薄。
也是,都那样久了,他怎会不变?云婵失笑,她自己又有着多少改变呢,只怕是数都数不清明了。
四十七年木兰行围、四十九年春动,他们之间 ,已经隔了两年的光阴。
两年的时光不长,但要看怎么过的。这样的两年光景对于他们来说,诚然也不算太短。也对,有些时候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往往只要一瞬间便够了,更何况是那样一日挨着一日的过的并不好的、且过的那样那样辛苦艰难的整整两年!
缠着新发杨柳清香气息的风儿卷起了无边璀璨,簌簌天光交织在十三阿哥微喜又微敛的面上,带起了几多明灭不定。他就那样站在厢房门边缓步迈进,水波起了涟漪般对着她笑:“我以为你不会在这里。”他笑叹。
云婵曼身轻起,抬指抚了一把耳畔碎丝,面上亦浮出了一缕若有若无的浅浅笑意:“我在。”她的语气有些暗哑,“怎么会不在……”朝思暮想、梦里千寻的那个人儿就站在自己的面前,那么真切那么真切的站在自己面前。可真到了眼下这个时候,心怀里面那些万语千言,似乎全部都凑化成了无声弱息,蛰伏在每一寸骨髓与血液里,她却什么都说不出了。
尘世的美,美在曲曲离歌、万般别绪,美在它的不完美。含恨也好、怨忿如是,终归都是不如意的。
云婵侧了一下面眸,心念铮动,忽而接口苦笑:“十三爷,你可真会挑时候。”依旧是这般不高不低、简单而且突兀。
她这句话没禁住把十三阿哥逗乐。他前几日才蒙了皇父赦免,不多时的调息平气之后,便循着曾经这条熟悉的街道一路走走散散,不想倒进了蘅苑客栈的门。心里也原以为云婵身在八贝勒府邸、亦或在她这个年纪早已嫁做人妇,不想却依旧还是看到了她,就在这里看到了她。真真缘分。
心底下一股莫名情绪只觉浓郁,十三择了个临着窗棱帷幕的位子端身坐下,垂了一下眼睑笑笑:“又是这句话。”
两年之前的那场木兰行围,他从围场那边往帐篷的方向一路走着,远远便瞧见她那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拼命样子。当时的她昂首挺胸、眉梢眼角具挂着可爱的鼓鼓气焰,犹如一只扶摇炸翅的小公鸡。见他迎面过来,她一副皱眉无奈的莫名神情,道出的便是那么一句“十三爷,你倒真会挑时候!”
两年一日日过去了,他却还清晰的记得。
只是当时的他不明白她那句话里的意思,时今的他也依旧不明白她这句话里的意思。或许有一天,他会突然明白;但有些事情,或许当时忽略便一生一世一辈子都忽略掉了,或许他永远都不太会弄得明白了。
这般一场追逐游戏,却是真真做弄的有趣。云婵思绪百结,喟然轻叹幽幽落在心里:“一步之错,生生错过,过错一生……不用太久,只要半月,若十三爷你早半月获赦,我们之间……”念及此,她兀然收绪,即而叹了口气,面上苦笑,“我们之间,又能如何呢!”
是啊,又能如何?
如若一切可以再来,他们之间又能如何?她会对他说什么?她想,她依然不会多有一字、多有半字的言语逾越;她的天性如斯,重来百遍千遍只怕也是一样。
但她若有知,她会的,她会告诉他,一定会告诉他……十三爷,我爱上你了。
我爱上你了……那是早在初次相见之时的一眼执念里,便已经埋了种子,即而渐渐于着坦缓岁月一点一点生根发芽,即便曾经那样用力的去按捺、去忽视、去遗忘过,也依旧还是没有用处。
宁愿做过了后悔,也不要错过了后悔。可这大千世上纷攘百般,却偏生唯独没有卖后悔药的……
静好的春光疏疏洒了一室,那样静默的气氛将周围景深渲染的只觉尴尬不适。十三侧目顾向尤自静默的云婵,握手抵唇低头咳了一声:“怎么,连一盏茶都不愿意给我倒了?”语尽淡淡笑起,他同她开了个小玩笑。
历经近乎两年的圈禁生涯,十三阿哥变了好多。敛却几许倜傥、平添一缕成熟,敛却几分率性、多增若许斟酌;但眼下云婵如此沉声静气的转变,看在眼里还是让他觉得不太舒服。这个彼时那样天真无邪的小小丫头,终是……长大了吧?他这么想着,不觉含笑摇了摇头。
这边云婵闻了十三这句调侃,方转回了斑驳神智,平和着面目冶步趋趋的走过来,抬手将那白瓷小壶里温度刚好的茶汤往锦鲤茶盅倒满,微微一推,递在了十三面前:“时过境迁也不过如此吧!”她抿唇一笑,边不见外的将身落在他对面坐定,旋而抬了抬眼睑,凝着离合神光微微顾他,“记得当初那次塞外行围,我们在草原上坐着烤肉、看风景,看头顶那片似乎离人极低的深蓝色天幕里、点点寒星涣散了夜的经纬……清风撩面,十三爷曾说起过那些蒙古小调。”她顿了顿,软款的唇兮化了一道似飞若扬的美丽弧度,入在眼里,不知为何总也觉得凄美伦常,“奴婢只怕……不会有机会听到十三爷唱歌了吧。”于此抬眸,漠漠的眸子里噙着轻烟笑意。
似乎只是极平淡的家常话语,可不知为何,十三听来只觉心里空落落的。一脉酸涩幽幽荡起,他抬了英挺眉目,便那般凝着深瞳将目光往她身上定格深邃:“怎么会。”他启口朗朗,“为什么非要听那些暧昧香软的蒙古调子?我这儿倒有另外一曲酥醉到了骨子里的,不如唱给你听。”
他的语气略略低微了一些,眉间心上有什么看不真切的东西跟着一闪便划过去了。
云婵侧了一下面眸,依是那般闲闲散散、偏着几分慵懒意味的神态不变却:“是,什么调子呢?”她问的简单。
边说话时,十三已经一整袍角将身起了。
他踱步往央处站定,略微挺胸,扬了一下俊秀眉弯,稍稍清嗓,抬臂展袖做了鹤唳扶摇。就着投渗进了木格子窗的层叠光晕,他嘹歌高起。带着男子特有着的血脉喷张,一曲清音如山涧涌泉、空谷鹰啼。
他唱的是一阕轻松、雪山、红瓦、金顶、蓝天、莲花台间的圣洁藏曲,分分合合、极尽撩拨的软款:
天空洁白仙鹤
请把双翅惜我
不到远处去飞
只到理塘便回
从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的月亮
姑娘美丽的脸庞
浮现在我心上
经幡叠篆、玛尼堆畔,只把你来三生三世盼
……
空灵的曲调杳远而苍茫,仿佛将那天、那地、那山、那水全部都带入到了莽莽苍苍的无稽大荒。仿佛撼动心灵的震慑魂魄,却又尤是入微细致,逼着、抵着渗入到每一丝血气里……只在昙然,云婵兀然涌泪垂颊。
君曾为我歌一曲,我将为君,我将为君歌一生。
若爱成空,是否便会少却诸多牵绊,让整个人都能活的洒脱一点?让爱成空,是不是便能离了忧怖,脚尖轻轻踏着千瓣白粉水莲花、含笑抵达了三千丈红尘的飞升彼岸,自此得了喜乐平安大自在?
可不能够,一切都不能够,只缘我们身在万丈红尘中,注定永生永世的无间轮回便都只能这般不由人的飘飘摆摆。在那些风的、花的、雪的、月的、梦里的荒古旷野里,终是寻不到一个良人,可以救赎自我于陌路的泥沼,自此图腾涅槃……
便这样静好一室,云婵此时的失神流泪惊诧了高歌的十三阿哥。他收声敛气,轻靴阔步跟着向她这边疾走过来:“怎么了?”一如很久以前一样,他压低了眉心急急顾问她。
云婵忙将他对着自己的那道目光错落开去,簇簇抬起衣袖拂面、遮了半张脸孔;旋而暗自薄嗔,笑的幽幽:“没什么,没什么……”只是很快,她复攀住十三阿哥的臂弯,扬起挂着泪的晶面哽咽碎语,“十三爷,若有一朝我死,请葬我于冬季里扬洒起了第一场雪的那个黎明,让我有一个天上人间最干净的身子、让我有一个天上人间最自由的灵魂……”
她言的哽咽啜息、语无伦次,直把十三心底下那团急切火焰点燃的尽致淋漓。
然而云婵只是摇头,只是垂首定睛,谵语般缓缓喃喃的起唇,口里诵着佛号。
生已无望,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愿我,愿我,往生安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清清浊浊、乱乱糟糟,轮回中的梵音,指间转动毫不停歇,无穷般若辛苦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