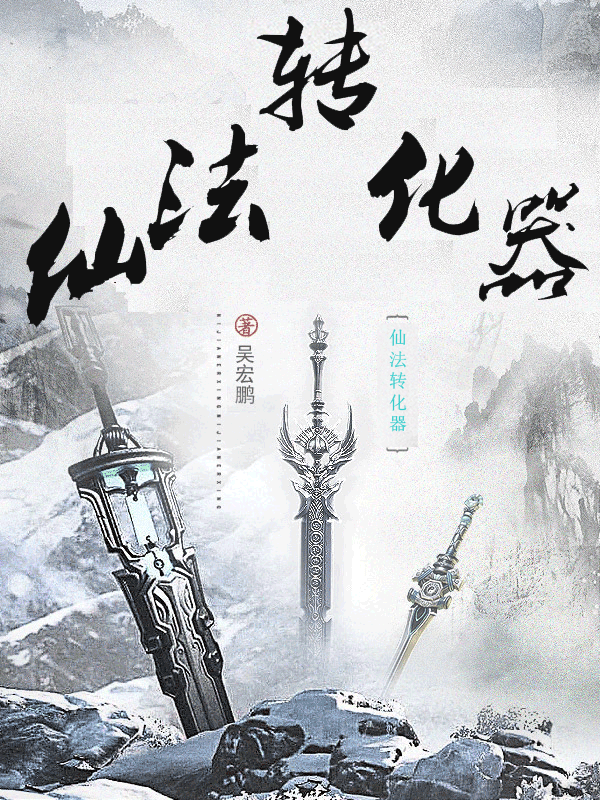长青的气息稳了一些,我依旧大气不敢喘也不敢动,生怕牵扯到她。
“我这里还有些药,可帮她止血……”“你们究竟犯什么病!”
我忍耐不了,破口大骂,不断有血往我大脑里充,昔日所学举止文雅我通通忘却一边。
“给一棒子又拿颗甜枣,你们羌国之人把我们当成什么?”
“最多不过三日,便入你们羌国皇宫,就这么等不及,就这么急着杀吗!”
我声声咆哮。
满天白雪,美景方才还在眼前,现下回顾四周,却是尸横遍野。
那男人立在原地,闷不做声,半响后,男人低沉的声音传来:“芸姐儿,”
这声音幽长,让我恍然儿时在宫中无忧无虑同父皇母后撒娇的时光。
父皇笑的慈和,每每都细细绵绵唤我一声“芸姐儿”。
我忘记做出反应,呆呆一双眼看着眼前人,嘴上不受控制喃喃出声:“父皇。”
男人猛的朝后退了一步,寒风凛冽,吹的我神智清醒。
不,父皇已经死了,死在燕越谋划的宫变中!
我阴冷着一双眼,眼前之人竟知道我乳名,不是羌国的人。
可他们屠了送行的人,此举所图什么?我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快速闪过,抓住那一点破绽后我惊骇的说不出话来。
我抱紧长青不作声,静等对方接下来的举动。
那男人轻叹口气,一字一句缓缓道:“这个丫鬟不该留。”
我握紧拳头,咬牙切齿:“这不归你们说了算,她是本宫的人!”
男人有些无奈,他伸出手朝后摆了摆,在他身后数十人的黑骑顷刻散开,去处理那一地乱尸。
他则重新上前,俯身跪下与我相对而立,他轻言出声:“我给这小丫头看看,许还能活。”
我一脸警惕,长青面上痛苦,嘴上咿呀说着些话,已是神志不清了,我咬牙,将长青轻放在地。
同时袖下将备身用的短刀握在掌心,他若对长青不利,我拼死也要拉他下黄泉!男人伸手在长青几处穴位轻点,又从怀里拿出药粉洒在长青伤口处,我紧盯他的一举一动,耳边忽的传来一阵低语。
“我本不打算留活口,芸姐儿你就这么走,走的干脆些。”
“可看你这么护着这小丫头,又觉得留个人也未尝不可,以后,你身边好歹有个照应的人。”
他语调缓缓:“芸姐儿,之后的事我会替你摆平,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心系百姓系天下,你的死因我会归咎在羌国流寇身上,他们常年受大燕边境压迫,对大燕的人怀恨在心,你沿途所带那批人,不过恰好存有善念。”
“你看边境的大燕百姓,被那些流寇当畜生一般折磨,是羌国的流寇杀了和亲的庆阳,羌国不能将过错怪到大燕身上,你所担心的,也都不会发生。”
男人动作熟练,将长青的伤口包扎好,他忽的抬起头,我不得不直视他那坚毅的双眸。
“好好活着,芸姐儿,活着才能做你想做的。”
这人,竟真是为我而来,即便心下已有猜测,可当话从他口中说出,我还是止不住惊颤。
大燕不可能有人会来救我,大燕也没有这样一支黑骑,这人到底是谁?
天空一道惊雷响起,我吓得从梦中惊醒,又做了那个梦,自那日已经有半月,时不时我还是会梦到那天的场景。
长青背上的伤在慢慢恢复,一连烧了好几天,这两日倒瞧着好些了,偶尔睁开眼能说上两句。
我不记得那天后来的事了,醒来的时候我和长青已经躺在一农夫拖柴火的车上。
那农夫善良,话里满是关怀:“你们两个女娃子,不要乱蹿,若是跟家里闹了矛盾,就快快回家说上两句和解就是。听闻那大燕和亲的庆阳公主,入了羌国边境就被那羌国流寇杀了,死状惨烈哦。”
农夫滋滋咂嘴,满是可惜:“不是老夫吓唬你们小姑娘,那流寇屠了和亲一行人,瞧见大燕长公主和她身边婢女有几分姿色,竟拖着人去两国边境之地,行那龌龊之事,此事传到大燕新皇耳中,正雷霆大怒,两国正在为此事涉交呢!”
我听着这番话,心下竟无半分波澜,想侧身看看长青情况,发觉手上多出一块令牌。
上好的黑木冠成,中间刻有一个“影”字。
我将令牌收好,谢过农夫,带着长青到了现在这所破庙,她不宜舟车劳顿,现下时局不清,我们藏着掖着些,也少些麻烦。
长青醒来时曾问我:“公主,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帮她换着额上的湿布,思量着回答她的话。
“在和亲路途时,你曾要我逃,我看到羌国流寇,觉得这天下百姓又何错之有?既然是死,不如帮百姓一把,至少可以换一段时间的安宁。”
“可是长青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可以活下来,如果我日后有机会重回大燕的土地上,我一定要让当初那群人血债血偿!犯下的因种下的果,天道轮回,一个也逃不过!”
长青伸出手拉着我,她嘴边扯着笑,“公主做什么奴婢都陪着。”
话完她顿了顿,眼中有几分犹豫,嘴唇轻动,但话没有说出口。
我讪笑逗她:“都现在这般情况了,还有什么令你支支吾吾开不了口。”
长青也笑,说:“那汹汹来袭的黑骑,可是公主认识的人?”
我摇头,实话实说:“我在宫中结交之人你是清楚的,从未有过这号人物。”
“那为何……”长青疑虑。
这个问题我也思量许久,得不到答案,索性也不再去想。
“若是有机缘,以后会遇到的。”长青听了我的话,点了点头。
当晚我和长青在破庙的佛祖前结为金兰,今后无论富贵,生死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