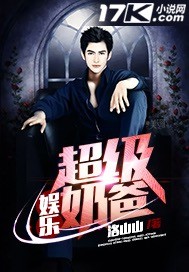这异瞳药医,的确深不可测····
他在破庙中时便给越严商写了信,说了自己仍活着,大可不必派杀手来灭口,这样一来便在离恨天那边保住了自己的命,说不定还会得到合理安排。然而···慎药司离金陵不远,以玄羽的速度早该回来,到现在却迟迟没有回信,江肆隐这才有些担心···
倘若是送信路上出了差错,可就有些不妙了···江肆隐更希望是回信的问题,所以为了试探,他带零彻去地处偏僻的小摊吃早饭,这里人少地荒,不失为杀人动手的好地方,但一路上却连个离恨天杀手影子都没有,就更别说白衣教的人了。
现在看来,形势对江肆隐还是有利的。
江肆隐又吹了声哨···久久等待,玄羽仍未回。无论如何,他现在与离恨天断了联系,出于研药心切,唯一计划便是去金陵城的永昼圣地,亲自寻离恨天尊主讨个说法。
至于零彻逃走这件事···看出零彻逃跑心思,对于江肆隐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毕竟支撑她熬过大半年的执念,怎么可能轻易放弃,江肆隐此时倒也不在乎,他早就想好···与其费这心思防范她逃走,还不如任她将能做的努力与希望全都做尽,等到了离恨天···自己再亲自打破,彻底断了她这份念想!再者,不放这愚忠的杀手逃一次吃吃苦,她怎么会明白有人照顾的好,怎么会彻底依赖自己?
所以,一举两得。
“希望你能在毒发前到达金陵城吧···”
江肆隐望向远方···自言自语道,此刻,他也要启程出发了。
踏上去金陵的那一刻,江肆隐,这本痴心于研药的异瞳药医,开始书写他在这乱世中的故事。
远远的看去…当江肆隐出现时,往往会给人一种安静无争又阴沉阴郁的感觉。
第一次清清楚楚地见到他,是在天空布满落日余晖的原野小道上,他一袭青白长衣,如瀑黑发垂散飘逸,异色的深邃眼眸望向前方平静地走,像个不问世事的隐者。
没人知道他要去金陵向越严商讨要个说法。
江肆隐在天黑之前到达了金陵城,夜市点燃灯火,热闹在这富庶之地弥漫开,他身无分文,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当,唯有左腕上一只解百毒的粗银镯子。
繁华出是非,手脚不干净的混混有的是。江肆隐感受到饥饿疲倦后,显露出右腕的镯子,在这闹市游走一会儿便进了暗无一人的幽深小巷。片刻后他听到脚步声,估计大概有两三个人跟在身后,于是捏碎袖里斑螯花的花蕊,刺鼻的香气充斥整条小巷,紧接着就听到两三个人人身倒地。
这是他的方式,不必焦虑思考,一切水到渠成,一步一行自如合理,永远不用担心在他身上看到惶急的情绪。
搜刮完财物,江肆隐有了住所,他打开客房的窗子,眺望万家灯火,深蓝苍穹,远处一片雾白色的是越氏殿庭——永昼,他拄着下巴,平淡起伏的往事历历在目,在他看来,如今都已如雪泥鸿爪般若隐若现了。
下楼,本想点些吃食,但看了看单子发现即便是小客栈,酒菜也要比外面小摊贵些。另外注意到其他桌的客人中有白衣教的教徒,江肆隐立刻谨慎起身走了出去。
喧嚣热闹的夜晚,形形色色的人们,对于坐在馄饨摊角落里的江肆隐来说还是很具有观赏性的,在这般还算闲暇的时刻,他会用那双充满智慧和疲倦的眼睛默默观察,同时心里细细想着自己的事。比如研药,他也几乎不考虑别的事了,有时候想想离恨天、白衣教、肖若医娘、零彻,但不过都是为了研药,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朝堂、帮派、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错综复杂,也干不着他的事,就算已经被牵连其中,那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好了,遇到天大的事自然可以运筹帷幄的。江肆隐不管是力挽狂澜还是行残忍之事,都从来不会慌乱担忧,这样的他往往给人一种可靠又可怕的感觉,进而使人产生一种消灭他的欲望。
“你干什么?哪来的?”
馄饨摊老板毫不留情地打向一只伸向馄饨碗的手,鄙夷地看向手的主人,是零彻。
江肆隐回头打量了她一眼,和他预料得差不多,浑身脏兮兮的,这个从未混迹过江湖的杀手明显才是真的落魄,她哑巴一般不开口说话,只是用那双带惯了杀气的眼神不知所措地望向老板。
“我请她吃饭,上一份刚煮好的吧。”
江肆隐的语气平静柔和,有种缓和气氛的力量。他对正准备赶人的老板挥了下手,同时看了零彻一眼,示意她过来坐下。
零彻见是江肆隐不禁惊了片刻,而江肆隐仍只是平静的看着她,并不讶异,眼神里似乎还有些罕见的温暖。她还是配合地走过去坐下,像以前一样警惕地望着江肆隐古怪阴郁的异瞳,她很想说些什么,可开不了口,此时的气氛和处境告诉零彻,跟随江肆隐是顺理成章,是命运的安排。
“很饿吧。”
他给零彻拿了双筷子,这副好态度对于此刻恐惧他的零彻来说怎么也像是奇怪又熟悉的折磨。
掀开锅盖,老板用木勺探入咕嘟沸水,舀了五六个晶莹馄饨,染上灶底温暖的烟火,撒上葱花小料,趁着热气儿端上桌。零彻一顿狼吞虎咽,被烫得嘴唇通红。
江肆隐从这副吃相看出她这些日子的坎坷艰辛,他仍继续望向街上的人流,漠然以对。
这人声鼎沸的夜市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此时天空恰如其分地绽放出几朵烟花,洒了繁忙众生一脸的温暖绚亮,零彻很快吃完又要了一份,连汤也喝尽,她慢慢恢复着体力,最后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
和从容善谋的江肆隐不同,零彻过得并不顺,执着于回到离恨天的她,类似于被主人抛弃的狗,愚蠢可怜。她来金陵的一路十分狼狈,既不懂得金钱交易也不擅与人交流,只是靠着多年锻炼出的体力与善人施舍的食物撑到了金陵,这样的她没有被人当作傻子已经算是幸运,不过零彻思想的麻木让她无法意识到自己经历的委屈心酸,也算是为她的人生减轻了一层痛苦。
小摊角落里的两人安静无言,仿佛这一刻就应该等着时光悠然流逝。
吃饱后零彻的微褐色双眼有了神采,她小心注视着江肆隐,这个此时此刻优雅沉郁的人,这个曾对自己施刑的人,这个能让自己吃饱喝足的人。以前她除了依赖江肆隐,更多时候会痛苦,恐惧,甚至反击,但实际上她并不对江肆隐感到怨恨,要知道她经历过离恨天的残忍遗弃后能仍旧保持绝对的忠诚,所以很难想出零彻会有怨恨之类复杂的情感。与向来处变不惊的江肆隐相比,两人也算是有共通之处。
“回客栈休息。”江肆隐站起身付了钱,零彻跟在他身后,理所应当成为一个待命者。
“明天,我们去永昼,见离恨天的尊主越严商。”
回到客栈,白衣教的人变多了,他们喝酒摇骰,大呼小叫。以前在金陵很难看到白衣教的人大胆聚集,他们现在甚至敢挑衅离恨天,气焰嚣张。江肆隐绕着他们走,他心知白衣教与官府勾结,否则官府不会无故捣毁慎药司。
“老子赢了!老子赢了!给钱!快给钱!”一个白衣教徒将骰子摔打到地上,他眼神发直,对其他人伸出手尖声讨要。
“去你大爷的!敢赢老子的钱!”另一个强壮的白衣教徒咬牙切齿之际将他一拳打倒在地,指关节沾了血,围观众人猴子般拍手叫好。
“你,你···咳!你他妈有本事去干离恨天那帮杂种杀手!”倒地的白衣教徒艰难爬起,吐了口血沫嘲讽地笑了。
“那晚徐师姐身边那个杀手,不是把你吓尿了?”说罢是一阵狂妄的讥笑声。
打人的白衣教徒顿感羞恼,伸手揪住那人的衣领两人开始扭打,在一片混乱中撞碎不少东西,引得掌柜心疼直叫,哀嚎、辱骂、破碎,客栈里瞬间变得闹哄哄。
楼上的江肆隐眼帘一垂,他已思忖完毕,侧过头在零彻的耳边说了些什么,便回了房间。零彻则下楼隐入客栈后院,等待这场混乱平息。
夜深,月转朱窗,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从窗子里扔进江肆隐的房间。两声闷响,干净利落,江肆隐扫了他们一眼,确认是那两个闹事的白衣教徒。
轻跃进来的零彻把窗子关上,站在一旁。
“想活命,问什么你们答什么。”江肆隐吹了声怪异的哨子,片刻,大概五六只毒蝎蜈蚣就从各处爬出,听话地守到两个白衣教徒的眼耳口鼻处,蓄势待发。
“你们白衣教的人,与离恨天的杀手可有来往?”
地上的两人纹丝不动,惊恐不堪,脑中早已空白一片,血与汗水混杂在一起成股流下。
“放心,如实答完,你们就可以走了。”
“没,没有···”其中一个弱弱地说道,这可能是因为恐惧而随便吐出来的一个词。而那些毒虫则前进了一步。他立刻惶急地改口:
“有有有!我想起来了,我们师姐有!”
“告诉我你们师姐和那个杀手身份。”
“我们师姐是徐瑰颖,白··白衣教的关门弟子,繁温楼的头牌。那个杀手我不,不知道,真不知道!连面都没见过!”
“好。”江肆隐偏过头看向另一个白衣教徒,同时毒虫离那表现良好的教徒远了些。
“该你了。”
另一个白衣教徒见此慌忙积极道:
“杀手!是个男的!还有,还有见过他的教徒都被他杀了!”
很明显他还想说点什么但无奈他已一无所知了,结巴的样子像是恨不得自己背叛得再彻底一些。
江肆隐听罢,零彻无声地俯下身,待他坐直身子吹了声哨,贪婪的毒虫齐齐钻入二人窍中凶狠噬咬,来不及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二人的脖子便被零彻扭断,毒虫们全身带着肮脏黏腻的血肉从黑红色的洞窍中胡乱爬出,不一会便消失在了房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