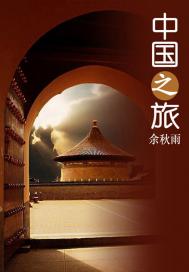简俊将她送到东程的楼下,她转身时没有犹豫,路是自己选的,总得顽强的走下去。
公司里的人都下班了,但门都大开着,倒似为了专门迎她一般,她走到记忆中的总裁办公室,门关开着,骆轶轩拿了杯红酒坐在沙发上,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外国人,骆轶轩注意到纪灵站在门口,忙站起来把她拉进来,“史密斯,这是纪小姐。”
史密斯有一头金黄的头发和一双蓝色的眼睛,随便一流转就是笑意,纪灵与他握手,他赞叹道:“纪小姐真漂亮。”
纪灵道他是恭维话,也不甚在意,微笑着道谢。
他很快就借口有事离开,偌大的办公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今天上午的那一幕极自然的窜入脑海,纪灵不由得想起了那张报纸,她和简俊还专门分析过那张照片的角度,倒是挺唯美,于是不知为什么,她笑了一笑。
他坐在离她不远,她的笑意辐射到了他的周围,他笑着问:“有什么好笑的事?”
她勾勾嘴,“我在想,今天报纸上的照片骆总有亲自把关吧,居然把我照得那么美。”
他笑了一下,“你认为报纸上报道的事是我授意的?”
她看了他一眼,坦然道,“我想不到会有其他人。”
他低低的笑了一声,既不辩解也不承认,起身拉起她,“走吧。”
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今天开的是敞蓬车,他开得又急,气流相撞得厉害,纪灵的长发在风中飞舞。她想开口,却发现嘴刚一张里面全是风,便放弃了。她不是没有坐过这样快的车,方子北骑机车的时候,也是用最快的速度前行,那时年少,只觉刺激与快活。
车离开市区,驶入一条水泥长道,速度渐渐慢下来,他瞥了她一眼,“害怕?”
她摇头,“不怕。”
他闻言,马上踩动油门,纪灵虽有安全带,却还是被吓了一跳,气愤地想找他麻烦,却发现他笑容满面,夏夜月亮的清辉照在他脸上,竟让她有不忍打搅的想法。
她终是开口,车在沿途一个闹市停下,他拉她下车,七拐八拐拐进一条小巷,他牵着她的手往前走,小巷里月光照不到,也没有路灯,他用手机上的灯光照着路,路上沆沆洼洼,她踩着高跟鞋,好几次险些摔倒。
走了有七八分钟,他们停在一个红漆大木门前,木门用很大的锁锁住,他把手机递给纪灵,“照着。”
她听他的话照着门锁,他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开门。这道门似是好多年没有开过,吱呀呀的发出响声,他推到能容纳两个人的空间,回头拉着她进屋。
首先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口大缸,一棵很大的不知名的树,还有一张石桌子,桌子旁边的凳子已经倒了,他没有停顿,推开了屋门。
是一间卧室,中间有一张红漆木床,他轻车熟路地摸到床边,拿出蜡烛和火柴,点亮后,屋子有了黄黄的光。他朝她微笑,“这里十多年没人住了,所有没有电。”他把床边柜子上的布拉开,开始找东西。
少顷,他搬出一个女人手饰盒大的木盒子,颜色暗沉,上面有精致的雕花,骆轶轩挥手招她近看,捂着盒子笑得眉眼弯弯,看得出他心情相当的好,他说:“你猜这里面是什么?”
纪灵认真打量那盒子,“你妈妈的东西?”
他摇头,似是志得意满的小孩子。
盒子也用一把锁住锁住,但他随手一扭,锁就应声开启,他笑道:“小时候总觉得这是我秘密,要用锁锁起来不让别人知道,现在才明白,其实儿时的那些所谓秘密,在大人眼里完全不值一提。他们只是懒得猜穿你。”
他这话也许无心,听在纪灵耳里却如被雷轰。是了,他带她来,就是提醒她不要玩小花样,我都知道,只是我不屑于去猜穿你。
他打开盒子,里面整齐摆放着十来个泥雕塑,有人有物也有动植物,他拿出其中一个小人,小人盘腿坐着,双目微闭,似庙里见到的菩萨坐姿,头发挽成一个髻,面目慈祥。他微笑看着她,“这是我妈妈,她每天总有一个小时用来静坐,至今我都未见过她那样安静的人,她能整天不发一言,一个人看书写字画图,她也是我见过的最优雅的女人。”
他又拿起一个小动物,“这是我第一次作雕塑的作品,做完后自己都认不出做的是什么,却没有舍得扔。”他抬起头,眼睛都是笑意,“年少的时候有很多理想,却从未想过会入黑社会,也没有想过会成为铜臭满身的商人。我的父母都是文化人,周末的时候,父亲在院里修花剪草,母亲就坐在石凳上,翻书阅读。”
他盖上盒子,将手插进西裤口袋,“小时候最想做艺术家,作画雕塑篆刻。”
他的眼神全是笑意,纪灵也似被感染,胸腔里有着轻微的疼意。她突然很想从后面搂住他的背,将头埋在他的背上,感受他欢乐又忧伤的回忆。然而,她只是微笑看着他,她很多年没有这样笑过,发自内心并非灿烂如阳光的笑,只是清清浅浅却有着复杂感情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