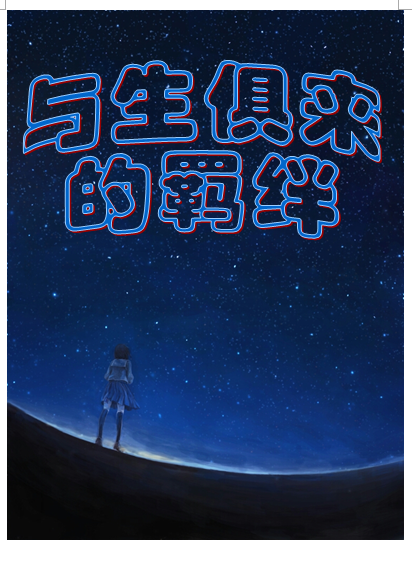纪灵微笑看着眼前的菜,菜色不多,三个。但看得出很花心思。有胡萝卜的雕花作装饰,三个菜的颜色搭配都很漂亮。
“如果不是看过你坐在办公室的样子,几乎以为你是厨师。你学过吗?”纪灵微笑着问他。
骆轶轩摆好筷子,拿了一瓶桂花酒,给纪灵倒了一小杯,“母亲喜欢洗手作羹,没事就跟着学了两招。”他举起杯子,“这个桂花酒是专门从桂林买来的,据说窖藏了二十几年,你尝尝。”
纪灵小小的啜了一口,觉得并不难喝,有淡淡的甜味,不由微笑。
这样的气氛很好,两个人。而天边的晚霞正要消失。红色的霞光照在纪灵脸上,平添了几分醉意。
可能是气氛太好,令纪灵完全不能抵抗;也可是酒太好,她一杯接着一杯,却不知这种酒的后劲最大,等她终于发觉自己有些晕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院子亮着两个红灯笼。
光晕重重散开来,打在青石板上,她突然看着骆轶轩忽明忽暗的脸,笑了。
她摇摇摆摆的站起身来,一把掌打在他脸上,嘴里喃喃道:“方子北,你是懦夫......”
头像被撕裂般痛。
纪灵只觉得全身都是酸的,她从床上坐起来,觉得床也硬也不少。再睁开眼,她吓了一跳,床是雕花的,而床的外侧的,还睡着一个人。
回忆慢慢地回复脑海。
她拍了拍头,为自己的失策。
天还没有大亮,只有从窗口照进来的一点点余光。他的脸对着她,身体并不与她相亲,只是就这样睡着,也觉得分外暧昧。
她打量着他,在微光的清晨里,他的轮廓依然清晰,连柔和的地方都透着棱角,呼吸清浅而悠长,睡得正沉。她笑了笑,想起自己昨晚的失态,也不知他怎么把自己架进房里……
她怔了一下,去看自己的衣服。衣服已经换成了丝质的长袍睡衣,与他相对,他的浅蓝,她的粉红。她握住薄被的手紧了又紧,才止住自己想去掐死他的欲望。她看着窗口的微光良久,觉得眼睛累了,才又重新躺下。
怎么办,能怎么办?
然而身体并无异样。这方面的经验她又那样少。此时也只是睁眼瞧着。
窗口的光越来越大,她侧身时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每一个毛细孔,他的呼吸打在她的脸侧,柔和的。与此相对,他的下巴上长出一点点青色的胡渣,她感到有些怪异——方子北是不太长胡渣的。
她伸出手,在上面轻轻的流离着,有一点刺手,然而这种感觉也极奇妙。她不敢动作太大,怕惊醒他,只是静静地瞧着。越瞧越觉得这个男人上天实在太顾怜,即便是这样不修边幅地躺在这里,依旧风流倜傥。
一丝温暖从心里泛起,她扭了扭身子,窗外的日光已经照进来,柔柔的打在床中央,照在丝质的薄被上,她将手放在日光上面,衬得她的手有如白玉,泛着暖光。
又玩了一会儿,回身去看他时,他不知何时已睁开了眼,也不说话,只微笑望着她。见她吃惊的瞧他,他从被子里伸出手,握住她还放在阳光下的那只手。
“还好么?”他的另一只手抚上她的额,他笑她,“你酒量原来这么差。”
她打开他的手,“你有意灌醉我,我能不醉么?”
他大笑起来,伸手发誓,“天地良心。我还买了一个蛋糕等着十二点时庆祝,哪知你只顾着发酒疯,抓也抓不住,弄到一二点才好不容易将你弄睡着了。”他带笑的眼睛直视着她,“你还是少喝酒为妙,不然被人占了便宜也不知道。”
她正纠结于此事,他却偏来提醒她。
她也不说话,只看着他,眼里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他握着她的手忽然着力,把她拉到胸前,纪灵还没来是及反应,他的唇已压上了她的。
突然不想挣扎。想想,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她伸出另一只手,搭上他的肩。
其实这样谁都快乐,也不用费心地防着谁。
这样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