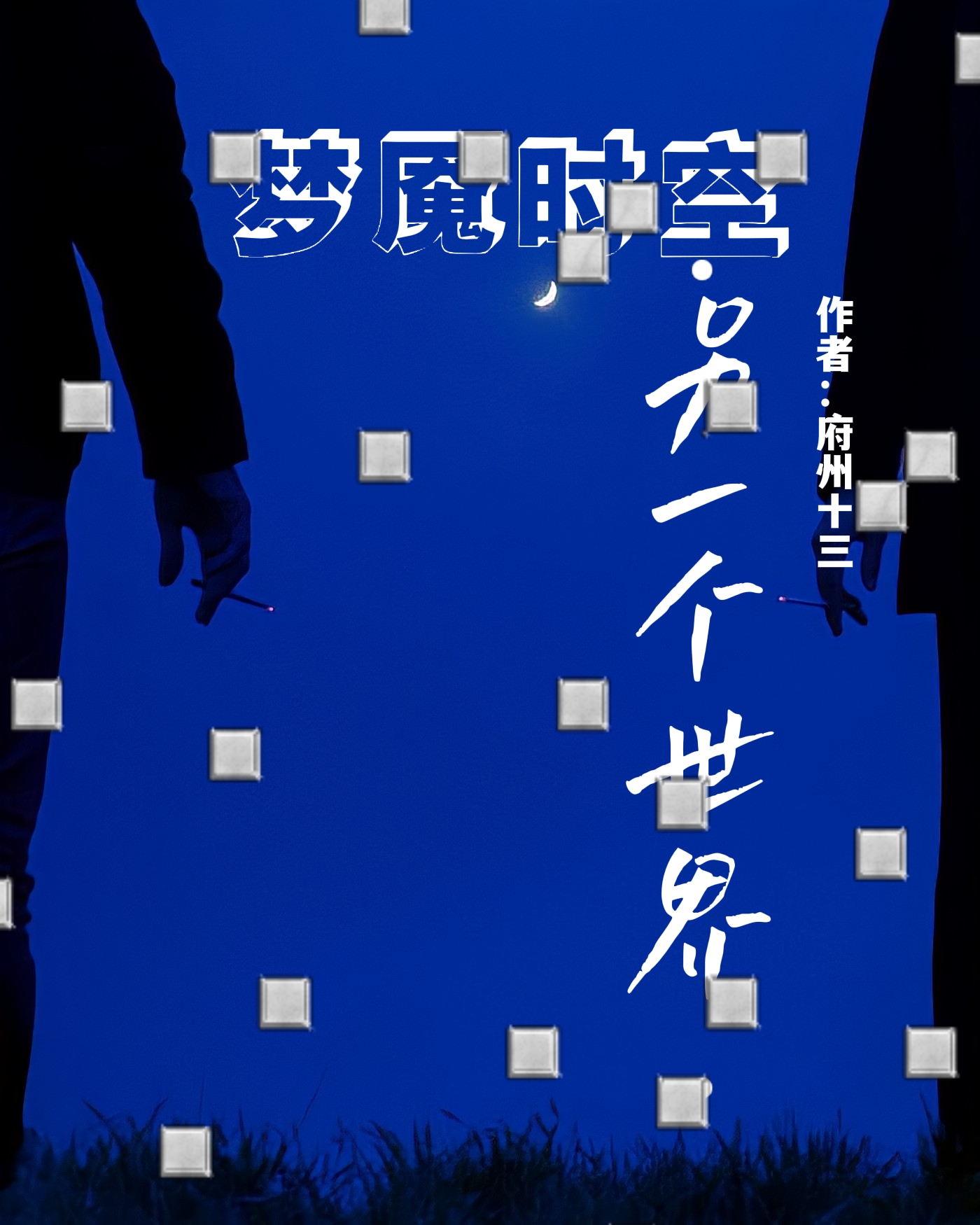把辫子松开,一头黑发如瀑布般垂下,上面稍沾染了白日的尘土,静姝拿着木梳细细的梳洗。月奴在一旁为自己铺床,半跪在地上,做得甚是仔细。
月奴虽说还是奴籍,可是已经是阿史那默认赐予自己的丫鬟,平日里跟着自己进出,再也没有回过那红帐。静姝想着,自己做了圣女的最大好处,就是带着她脱离了苦海。
这个小丫头,天真单纯的紧,平日跟在自己身边,竟然对于阿史那的把戏没有看出半分,还对自己的那些所谓神迹崇拜不已。
“圣女,你找了金牌,可就真是我们族里的大救星了,月奴跟着你也沾了光,走在外边可神气了。”她低着头絮絮叨叨的样子煞是可爱,静姝情不自禁的笑了出来。
听见静姝笑,月奴太起头,“我真的没说假话,”样子又认真几分,“好多人对着我特别客气。”
静姝笑意更深,“我又没说不是真的。”
说到这,月奴突然像想起什么东西起来,起身跑到帐子外面,不一会儿抱着一个陶罐进来立在静姝面前,神情有些扭捏,罐子里飘出淡淡的奶香。
“怎么了?”静姝先开口。
“这……”月奴身子晃晃,静姝听见罐子里的叮咚声,“今天白天我哥哥来找我。”
哥哥?就是那个把你卖掉的哥哥?静姝忍住没说,却看这月奴对于一个几年前卖掉自己从此不闻不问的哥哥没有半分怨恨。
“哥哥让我拿这罐羊奶来孝敬圣女。”
“有什么事吗?”对于卖掉自己亲妹子的哥哥,静姝没有半分好感,这突然的出现怕是没有叙旧这么简单。
“哥哥说……哥哥说我的小侄子两个月了,一直没起名字,想来求圣女向神明请示,给赐个吉利的名字。”
“你见过你那个小侄子吗?”
月奴摇头,不出静姝的预料。这样的哥哥又有何脸面来求妹子帮忙。
“你希望我给他起名字吗?”
“当然了。”月奴神情又激动起来,“能得到神的赐名是何等荣耀的事,说不定以后有了大出息,成为族里的武士,就不必再过这样的生活。”
静姝看着月奴的样子,不忍拂了她的意,想着不过是个名字,她既然相信那就信吧。
静姝偏头沉思,不一会儿,口中念道,“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舟,泛泛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
静姝抬头,笑笑,“取名‘寿’字如何?”
“寿?”月奴挠挠脑袋,不懂。
“寿乃长命之意,在中原,是吉字。”
“这样啊……”月奴不好意思的笑笑,感觉总是有些怪异,“既然圣女说是吉祥之意,那我明日一早就和哥哥说去。”
看着她高兴的样子,静姝反倒有些落寞。她是独女,没有兄弟姐妹,如果她有一个哥哥,也许也会和月奴一样,即便被伤害的遍体鳞伤,在一个小小的示好之后也会摇晃着尾巴欢天喜地的贴过去。这就是情。
可惜这世上惜情之人并不多。
她没有告诉月奴,她刚刚低声念得,是《诗经》中《邶风.二子乘舟》篇,讲得是姜宣的两个儿子寿与朔的故事。
宽厚仁德的寿,为了同父异母的哥哥赴死,死在了不明真相狼子野心的亲弟弟手里。
悲哀的寿,同样悲哀的朔。悲哀的姜宣。
她没有给月奴讲述这个带着春秋晚风的悲剧,却给她的侄子取名寿,希望那个还抱在怀中的孩子,怀着一颗慈悲之心,对同胞有着一份怜悯之情。
夜渐深,静姝躺下,看月奴吹熄灯,消失在黑暗里。
闭上眼,听空气里细微的声音渐渐消失,却无眠。
不知过了多久。
黑夜中,静姝睁开眼,四周的物体只有朦胧的轮廓。极静,空气里只有月奴平稳匀净的呼吸声,这样的声音却让人感觉真实而幸福,她突然想起玉奴的话,“你相信誓言吗?”
在黑暗中摸索着起身,小心的绕过睡在门口的月奴,帘布一开,清辉一地,月华如练,再抬头,才发现今夜竟是满月。
拖着及地的皮衣,静姝顺光而行,在这草原初冬,今夜却是罕见无风。随意走到一处乱石处,静姝停下脚步,抬头看那月亮,似乎又近了几分。
她想起还在洛阳时,只有中秋才会看见如此无缺的月亮,她总会早早的做好枣泥馅儿的圆饼,摆上切成莲花状的西瓜,还有擦洗干净的苹果和葡萄,同父亲在亭中赏月。那时,即便只有两人,她也觉得幸福异常,靠在父亲的肩头,听他讲他与母亲的故事。
现在,是连父亲也去了。
静姝低下头,从怀中摸出那求佛公子送与自己的竹笛,低低的吹奏起来。
父亲临终前面目含笑,他拉着自己的手说,“静儿,你这一生,我是托付于苏将军一家,苏将军与我是生死之交,他为人忠肝义胆,儿子们也各个人中龙凤,你嫁过去我放心。”
静姝也试图含笑,却忍不住眼泪流下了,滴落在父亲的手背上。
“静儿,你是知道的,你母亲等我等的太久,我不忍她在等下去,这一天终是被我盼到了。”
父亲说的绝不仅仅是安慰,他与母亲阴阳相隔十六年,如若不是为了将自己拉扯成人,怕是父亲早早的就随母亲去了。
这就是她最早对于爱情的印象,缠绵,温情,又绝望。
这样的爱情。
叹息一声,断了笛声,瞭望远方,什么都没有,却又好似什么都有。
母亲对她来说,已经完全模糊了样子,可是关于母亲的每一个细节她都清楚异常。
“静儿,你已有你的母亲八分的容貌,她就是你这样的眉眼,只是嘴唇稍厚。”父亲总是顺着她的容貌看着母亲。
“静儿,你的性子也与你的母亲相似,总是远远坐在那里,淡淡微笑。”他看着远处的椅子,好似母亲就坐在那里。
“静儿,你的手艺是同谁学的?你母亲知道肯定欣慰,因为她手艺一直不好,苦恼了好久。”父亲说笑着,看着的仍是母亲。
她所有关于母亲的记忆,都是由父亲一点一滴拼凑,父亲心中藏了十多年的影子,又重新在她的心中延续。
再叹息一声,又一曲低低鸣奏。
这轻且低的笛声柔柔的飘荡,阿史那在帐中,借着昏暗的油灯光读书。今夜他没有读那些汉家兵法,倒是随手捡了一本诗集看着。
他一个字一个字费力的拆解,却仍不明其中意义,那些他不知道的唐朝诗人,那些他不理解的悲春伤秋,如若在平日,一定被他随手翻翻就丢之一边。可是今夜,和着这哀怨的笛声,竟然鬼使神差般不忍放下,即便是囫囵吞枣,也一遍遍的在心中默读。
夜,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