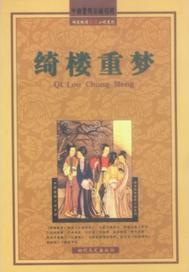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一首描写雨后初晴行人狼狈赶路的词,风声呼啸过后骤雨铺头盖脸打来,让人猝不及防,同理世间不幸事十之六七都是不期而遇,就似这未知天气,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芸芸众生各自命运,人生大路各不相同,成大器之人披肝沥胆,尝尽千般苦,终于换来功成名就,命贱之人苦熬活受,最终到死都是屁民一个,咽气之时喘息良久,终不能安然瞑目。闲来驻足闹市之中望眼看去,南来北往纷纭而去,皆是为了前途和命运奔波,再多的挫折病痛忍了又忍,谁都不肯割舍了这条生命,为的什么?只为雨过天晴,苦过痛过之后能得享福禄寿喜,子孙满堂,欢笑中落个团圆结局。
且说到那时风已停,雨已过,天气放晴,广阔大地任诸位行走,该有多好。
康熙二十年初春,恰逢农历节气惊蛰,京畿道南方一带,湿漉未干的田间小道上急匆匆走来个挎着包袱的浓眉青年男子,中等身材,略显魁梧,脑门之上头皮剃的锃亮,一条黑粗的辫子绕在脖颈之中,眼神中略有几分坚忍和俏皮,青蓝色长袍之上沾染了些尘土,一只手拖着一名十多岁小女孩,因为行走多时脚痛腿麻小女孩不停哭闹,怀中抱着一个刚满月的婴孩,婴儿在他怀中睡的很熟,轻微的呼吸声都能听得见。
仨人远道而来,看起来风尘仆仆,面带不堪倦容,渐渐累的行走不动,到一处名叫亭候头的地方,小女孩实在倦怠,青年男子拖行她不过,低头耳语几句,松开手,将怀中孩儿交到她手中,疲惫男子从怀中掏出一壶酒,猛喝了数口,然后从手腕处的包袱里取出一块黄金般的丝绸布垫在身下,二人在其上就地坐下,这块绸料一看便不是寻常人家之物,明黄黄夺目,金灿灿晃眼,拥有此物者,非王即候,非寻常富贵人家能拥有。
雨过天晴,屋檐上滴水略停,躲在茅草亭屋中避雨的乡间人纷纷走入田地中,抢着农时劳作,此时男女欢笑,儿童间在田埂上嬉笑打闹之声不绝于耳,俩人在窄路上鱼贯而行,打扮甚是惹路人好奇,多半停下猜测男子的来历,三三两两农人站起身,在田间手搭凉棚好奇看着他们。
此处离要去的地方不足百里,晁开霁的二叔晁俊德并没有如约前来接应自己,心中不免有些忐忑。抬眼望去,地洼之中高粱棵棵旱死,左右林子多是刚刚能藏人的荆棘,土地贫瘠,此地民风狡赖,无信不义气,害人夺命而不能破,几乎家家都有亡命之徒,故而能藏住不速之客,想到此,晁开霁反倒觉得松了一口气,江湖之中人不能不讲义气,只要提到二叔的名号,未必不能趟过去。匿在草苇之中,他仨人在背风处小山包下歇息够了,站起身来爬上极目远眺,从这里极目远眺,雨后天空如洗,沿途景色如新,空气新鲜呼吸一口令人心生喜悦,冬雪化尽,即将是春的来临,贫瘠大地上一块块的白碱还能看清楚,附近庄野一片宁静,鸡鸣狗吠之声此起彼伏,大树高若巨烛,即将吐蕊报春,只因寒冷未净,春芽刚开始萌生,未能染绿。
默不作声重新蹲下,青年男子表情略带得意之色,从怀里另一侧拿出几块干粮,小女孩接过咬了一口,被青年男子搂在怀中,他低头想亲昵,硌着怀中婴儿哭泣起来,声音颇大,俩人怕惊动了旁人,急忙收好明晃晃绸布,往远处的杏树林当中走去。
光秃秃连绵的杏树林枝桠层层交错,一股北风从田野上吹过,寒气透人衣,俩人觉得身上冷,更是加快了脚步赶路。
此二人来历甚是奇怪,急匆匆行路的男子姓晁,名叫晁开霁,眉目清秀,身材长硕,是个看一眼就让人喜欢的年轻人,只是稍稍举止轻佻,与人对视常常目光游移不定,他心生倦怠才想起与女孩调笑。随行女孩杨明艳随主人姓杨,幼年不明来历到了杨家,她长相不出众,不惹人注目,怀中婴儿是传说中的朱三太子之后,主人家命名杨宏复。
春寒料峭之际三人同行,去晁家庄投奔他二叔晁俊德,千里之行,如此重要的朱三太子之后怎么没有其他人护送?且听细细道来。
看官有所不知,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造反,杨起隆在京城冒用朱三太子起事,历时七年,响应者百十万众,与清廷作对救断明于未续,争斗绵延千里,最终不敌清兵围剿在陕西凤翔府伏法,不久一家老小都被绑缚刑场开刀问斩,只剩下怀中孩子幸免于难,在杨家当护卫的晁开霁和奴婢杨明艳保护之下,侥幸逃脱,二人抱着婴儿躲在巷后石板下的污水沟内,躲过一劫。
隐秘在京城胡同的杨宅已然破溃,守卫杨起隆宅院的反清复明义士被杀的七零八落,血流成河,多分散逃去不知去向。
晁开霁的女知己暴露身份引走官兵,他带着杨明艳护送小主子离开是非地京城,投奔到乡下暂时躲避,期待能换小主子平安活命,他年他月再图复明大业,一展抱负,大展宏图,尤未可知。
晁开霁的二叔晁俊德年过四十,在乡下无所事事,年轻时好舞刀弄棒耍拳脚,寻些武功秘籍照着练,农闲时候纠集些乡下流氓少年,效仿朱洪武年少骑驴骑牛两帮打作一团,为便于练习武艺,在家中设了一处场院,摆着刀枪剑戟,石斧石锁,平时练功防身,因他不拘小节事必较真,引得江湖之中无数诬赖之流慕名而知,切磋一二。
性情罅隙的他,同时略微有些乖张,拘泥于细枝末节,故而有不少乡里人为了鸡毛蒜皮小事与他结怨,小小乡间补事的差挣不了几块钱,全靠着家人勤耕几亩地支撑粗茶淡饭。
晁开霁在杏树林中急走了几十步,突然听见几声布谷鸟叫声的天地会暗号,知道附近藏有同党,遂按照暗号回应了几声。
既然都是明末之人,便不再有丝毫的迟疑,一名白发苍苍老女人从杏林中突然走出,威风站定自报家门,拱手向上苍一表,朗郎大声自称锄水婆婆,是前朝断臂公主的徒孙,自从庵堂被清军剿灭,她被迫还俗嫁人,住在不远的合璧镇,生活清贫倒也终日和乐,此杏树林当中有一简陋居所,靠贩卖甜杏生活。
晁开霁同样还以大明稽首共拜之礼,“既然是明朝公主的弟子,我就明人不说暗语,我怀中抱的乃是朱三太子之后,人生路陌路过此地,请给与方便,待他日功成名便一同共享荣华富贵,若有半句虚言,当死于掌下。”
锄水婆婆听言两眼放光喜出望外,“哎呀,我久违的小主人你安好否!”说完扔了手中拐杖,上前顶礼膜拜,托抱出孩儿,恐有惊吓,忍泪含悲细细打量,瞧他的眉眼,老泪数行不觉滴在婴儿脸上。
“老奴知错,不该这许久才来迎驾,这泪儿此刻不该轻弹,让我主蒙羞。”说罢,拿手猛掴自己的老脸,直至牙龈出血,滴滴鲜血从嘴角流到衣襟之上。
“滴水婆婆快些住手,莫要惊扰了主人家。”晁开霁急忙拦住她再次下手,并挥掌打伤自己一臂,鲜血喑红了衣袖,杨明艳随即双膝跪地,泪水止不住掉落一地,双手牵扯住两人的衣袖,“两位贤士不要如此自虐,咱敌人是清兵不是自家人,不能自相残杀”。
听见此言恳切,滴水婆婆收了眼泪,再次说道,“眉目中间隐藏帝王之气,几十年间,听闻天子余脉被诛杀殆尽,无一幸免,痛不敢言,如今我朱家有后了,此刻就在老奴怀中,犹如重任重新担在肩上,老奴身死何报万一,再也舍不得让殿下离开我半步。”
晁开霁突然想起此乃杨起隆之后,便略显尴尬,犹豫片刻,决定将实情以告,遂上前抱起孩子,低声说话。
“此乃京城起义的杨氏之后,虽然名为三太子,但相差甚远,不能一概而论。”
“既然已在城中称帝,便是我汉人的皇帝,为我汉人起事,与那鞑子为敌,有何不同哉?我之前听闻三太子起事,欢心不已,与义士奔走相告,而今君主虽已殉国,我年事已高,能做的不多了,只是藏身在杏林陋室中,祈求君主的灵魂早日升入万佛天堂。”
晁开霁见她不细追问,眉开眼笑叩谢,“你有这份报国之志,何愁大明不兴。”
锄水婆婆再观看婴儿,再行跪拜之礼,“如今看见怀中太子,确实坚定了我的信心,你们这是去往何处?”
晁开霁替小主子遮上挡风沙的面罩,自言自语却坚定,“我要带着杨姑娘投奔我二叔晁俊德,暂时安顿下来,我相信他有更好的办法。”
锄水婆婆熟悉晁俊德,知道他人品事迹不端,便出言阻拦,“此时不可,清兵从我这杏林中路过刚走不远,见你们形色匆忙,故而现身打暗号给你们提醒。”
晁开霁指示杨明艳还礼,“多谢前辈提醒,还请前辈指教一二。”
锄水婆婆看了看姑娘,夸赞她美艳,日后定然大富大贵,不可言喻,“你们一行人目标大,我一个老婆子也已曝露,会连累太子的安全,且怀中孩子在吃奶,没有奶妈照顾怎么能活下去。清兵搜查的严谨,晁家二叔是个光棍汉,素不喜男女纠葛,突然与女人勾搭,多出一双儿女恐遭人非议,反而容易招致杀身之祸,事缓则圆,不如找个刚生育的乳母寄宿。”
晁开霁一听,觉得是个万全之策,欣喜不已,“前辈话说的虽好,可去哪里找这样的乳母?”
锄水婆婆向前跨了一步,“英雄不要着急,有我在此,你们先这杏林小屋内小住,我出去帮你们打探情况。”
晁开霁打算带着杨明艳投奔他二叔,听了锄水婆婆劝告,暂且改了主意,留在杏林小屋之内。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锄水婆婆梳洗打扮干净,拄着拐杖一溜小跑出了树林,去合璧镇给孩子寻找合适的乳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