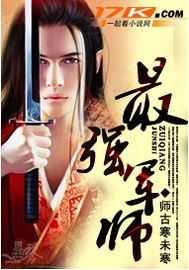阮卿躲在窗下,身子不住地颤抖,不知是因为受了冤屈气愤,还是因为害怕。她不敢挪动半步,不敢发出一点声响,甚至不敢大口呼吸。她睁大眼睛凝神听着屋里的动静,只盼定儒能说一句:“不,卿儿不会的,我不信。”可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阮卿等了半晌,屋里只是沉默,定儒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良久,余师爷那低沉沙哑的声音传了出来:“女子之祸,甚于虎狼,七爷是伐纣的周武,可不是贪恋美色的商纣啊!”只听定儒答道:“师爷说得很是。”阮卿闻言,心中一阵气苦,眼泪便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她恼恨余师爷这般诬蔑她,恨不能破窗而入一颗冰玲珑打进这恶毒书生的膻中,可是一听得定儒这话,她全身便立刻没有了半分力气,恨也不成,怒也不成,只是哭。
她自思对定儒一片痴心,天地可鉴,对上官箫不过兄妹情份,更何况她恨上官寥入骨,怎肯做上官箫的耳目来算计定儒?可是定儒却不信她,疑她,甚至将她看成了祸害。这巨大的委屈悲伤憋在心口,闷得她胸膛似要炸开一般。她独自在议事厅的窗下呆坐到中夜,定儒和余师爷早已走了,胸口又开始闷痛,可她明明记得气海穴上那颗冰玲珑已被女妖化解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房间,又是怎么挨到天明,只觉得白日黑夜并无区别,万物入口皆是苦味。
又过几日,庄里渐渐开始热闹了起来,丫环仆人们忙着打扫整理各处厢房庭院,花厅中不时有客进出来往,道喜声不绝于耳。只有阮卿一个人呆坐着,她想见定儒,面陈自己的清白,但却找不到他,料想是他故意避开了。这几日她连眼泪都已哭不出来了,哀哀地想着:他总要处置我的,就算是将我当奸细杀了,他也该给我个了断。
屋外有人敲门,阮卿以为是定儒,忙起身开门,当看清来人之后,她的脸色立刻从希望变成失望,从失望转为愤怒,冷哼了一声,扭头回坐到窗前。门口站着的是余师爷,他缓步进屋,愣愣地盯着阮卿的背影凝望了半晌,眼神似伤痛又似温柔。
阮卿头也不回,冷冷地道:“怎么,冤枉了我还不够,想亲手杀了我么?”余师爷一愣,才想到那夜与定儒的谈话被她偷听了,忙道:“不,我怎么会杀你?”阮卿冷笑道:“你害得我这样,还不如杀了我。”余师爷沉默良久,说道:“我带你去一个地方。”阮卿道:“我要见他。”余师爷叹了口气,道:“你还不死心?”阮卿眉心一凝,倏地抽出鱼肠剑,转过身来,怒目道:“这么说,是你故意要我死心?”余师爷缓缓点头,阮卿觉得一阵眩晕,眼中似要喷出火来,她手臂一伸,鱼肠剑锐利的刀锋已抵在余师爷的咽喉。阮卿喝道:“带我去见他,替我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