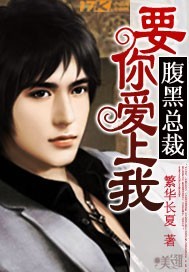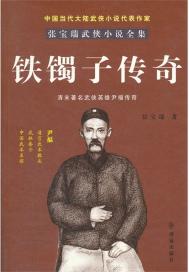“阿曼莎妈妈要死了……她要死了……”顾歆舒喃喃着说出一个名字,整个人便软瘫下来,像一滩烂泥一样糊到闫涛蔚身上。
刚才往回走的时候,顾歆舒接到一个电话,是富伊莎孤儿院现任院长打过来的。阿曼莎修女终究没有敌得过疾病的折磨,就要去了。问她最后的心愿是什么,她只说没有。然而她的眼睛总是那么执著地望着桌上那盆干花。那是一盆康乃馨,顾歆舒送给她的康乃馨。那天顾歆舒走后,孤儿院里一个手工工艺颇为出色的孩子把这束花枝做成了可以永久保存的干花。从此,它们就在阿曼莎修女的床头长久的摆放着,而那张小而破旧的桌子成了再珍贵的礼物也替代不了的摆放位置。
在顾歆舒那一代的孩子中,阿曼莎修女最疼爱的不一定是顾歆舒,但最担心最牵挂最心疼的一定是她。她太了解这个孩子了,执着而胆怯,坚强而脆弱,善良而决绝……所有相互矛盾的词汇她统统沾上了。她正在走着的是一条错误的路。然而这世上又有多少人是在走正确的路呢?顾歆舒不会明白,她也点拨不了。上帝也没能帮助她,他选择了打盹,于是手指间抓着的悲惨丝丝缕缕漏下来,全都落到顾歆舒身上。
院长明白阿曼莎修女的心思,偷偷给她打电话,希望她能过去一趟。
闫涛蔚二话不说,把她塞上车,就要往孤儿院赶。
顾歆舒仿佛是失了知觉的木偶,不声不响,毫无反应地任凭他拉着她一路小跑,帮她打开车门,系好安全带……直到车子启动了,她才忽然惊醒过来,立刻扯掉安全带,也不管车子已经开始进入行驶状态,推开车门就往下跳。
“顾歆舒!你疯了!”闫涛蔚赶紧停车,冲到她身边。她在地上缩成一团,还一点一点往后挪,直到背部抵上盛鼎山庄的黑色沉铁外栏,再也无路可退。
闫涛蔚不动声色地看着她,预备好控制她随时可能失控的情绪。这几天实在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然而她始终静默地坐着,空洞的眼神黯淡无光,连他的影像也反射不出来了。
“为什么啊?为什么是今天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么多事情要一下子发生?我快要死了吗?所以所有的事情怕来不及,统统跳出来了?这几天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她这么长时间不说话,闫涛蔚几乎担心她要憋坏了,说不定又像那天一样,就这么“死”过去了。然而她忽然低喃出声,一句接一句地问。她的眼睛依旧空洞得怕人,不知道是在问谁。也许是在问自己,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陈述。
她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竟然就没完了。
“何政鸣,你是疯了吧?你敢说你还正常?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何家讯,你真的爱我吗?丢下我的人是你,充好人回来拣我的人也是你。你吃定我了是不是?你怎么不娶我呀?嗯,对,是我不待见你。但是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温婉,你真可怜,可怜的竟然需要我的同情……那我呢?你怎么这么自私,你为什么不会想一想我呢?……纪晓阳,别跑,你还怕我骂你么?嘿嘿……我不会骂你,你多聪明啊,卖了我还让我帮你数钱。你又回来招惹我是要干什么呀?你要做什么?歆怡是我的命根子,你是要离间我们!——你妄想!啊——阿曼莎妈妈,你是在生气吗?你在怪我没有学会宽恕?那你回来啊,你陪着我,我都听你的!阿曼莎妈妈,你别走,真的,我要死了……你把我一起带走吧,我要跟你一起……妈妈……”
闫涛蔚感到脊背一阵发寒,走近她一些,只担心她脑子不要出现什么毛病才好。
她的眼睛忽然重新变得有神起来,不,不止有神,简直是狂乱。她的一双眼睛里交错而杂乱无章地变换着各种神色和光亮,碰撞间激光迸溅。忽而又平息一下下,然后以更加激烈的方式掀起滔天巨浪。她的眼睛像是长了牙齿,凶狠地眨巴着,仿佛就要咬上来。
然而这双眼睛却是她浑身上下唯一活动的地方了。
她的眼睛这样灵活而狂躁地闪动着,她的脸却平静而苍白,语速均匀而缓慢,嘴巴张合的动作都很轻微。她软塌塌地靠着高大的铁栅栏,像一块沾满水的沉重的海绵,动弹不得。
就好像,身子是她的,而灵魂,是另一个人的。
“顾歆舒,你醒一醒!阿曼莎修女还在等着你见她最后一面!最后一面你懂么?你要是错过了,那是一辈子的事!你给我起来!”闫涛蔚决定不能再放任她这样下去。她必须正常起来,振作起来。他知道他的话现在根本占不了一点分量。他要带她去见阿曼莎,不管是拽的拉的绑架的,他要她去见她。那个阿曼莎修女……也许能救她。哪怕只能说上一句话,他坚信她能把顾歆舒喊醒。
顾歆舒怔了怔,仿佛已经清醒过来,挣扎着往栅栏里挤,双手死死攥住栏杆,不管不顾地哭叫:“我不去!我不去!阿曼莎妈妈会死,她会死啊!”然而她瞪大的眼眶干涩得紧,一点眼泪也见不着。
闫涛蔚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心情,恶狠狠地掰下她因为用力过猛而扭曲得显得瘦骨嶙峋的手指,一根一根,毫不留情。他把她夹在胳膊下面,不管她的拳打脚踢,像搬运货物一样把她扔上车。
闫涛蔚简直是用捆的,把安全带死死绑到顾歆舒身上。顾歆舒仍旧拼命挣扎,一伸手摸到插在锁孔里的车钥匙,不假思索地拔出来就往他身上戳。这一戳刚好戳在闫涛蔚的额头。他吃痛,忍不住低吼一声,捉住她乱挥的手,夺下钥匙来扔到一边,扬手就甩了她一巴掌。
“你以为你不去她就不会死了?你以为她能等你多久?顾歆舒你多自私啊?你让一个老人家一口气吞吞噎噎、断断续续,你让一个将死的人还悬着一颗心七上八下、不得安稳。你觉得这是好心?你觉得这是在为她续命?你是做了好人了,别人怎么办?她本来可以一了百了,超脱痛苦了,你却还让她在疾病的折磨下苟延残喘。你是不疼,你当然不会疼。你是在关心别人么?你是在保护你自己!你怕见到最后一个爱你的人离你而去,你接受不了所以选择逃避!顾歆舒你真够自私的,哈?你把一个要死的人折磨成这样,还顺带稍上一个大活人。我流血了,我疼!你有感觉么?你醒了没有!”闫涛蔚火冒三丈地捂着额头,痛痛快快地训斥了她一通,然后不打算再搭理她,重新把钥匙插进锁孔,启动车子。
车子里安静得怕人,只能听到细微的咔嗒声。
闫涛蔚把车后座的纸巾盒拿过来,抽了几张纸巾胡乱擦了擦额头沁出的些微血迹,然后心烦意乱地把纸巾团了,扔出车窗去。
卑微的纸巾在风中轻飘而无助,瞬间就被风刮到遥远的后方去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闫涛蔚忽然听见车厢里有簌簌嗤嗤的声响。他转过头去,发现顾歆舒终于流下眼泪来。他长长舒一口气,眉宇间的严峻肃穆缓了缓。她肯哭出来,肯哭出来就好了!他把纸巾盒放到她面前,良久之后看她一眼,却发现她快被自己的眼泪淹了。她仍然保持着最先的姿势,两只手软绵绵地垂在半空,一动也没有动过。他叹口气,抽出纸巾来帮她擦眼泪,一直擦一直擦。
他忽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
顾歆舒骂了那么多人,说了那么多人,谁都搬出来了,唯独没有他,没有闫涛蔚。不管是爱也好,恨也好,悲也好,怒也好,甚至是绝望,都没有关于他的只字片语。
在她心里,闫涛蔚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吧?
车子驶进孤儿院大门的时候,顾歆舒突然一下子活过来,坐端正了,自个儿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
“总得让妈妈放心。”她轻声细语地说,不知是对他说,还是对自己说。但是他在她轮廓精致的眼眸里依稀看到一贯的平静淡漠。
顾歆舒同阿曼莎见最后一面的时候,闫涛蔚正在车上往外拨电话。
那边一接起来就是怒不可遏的样子。
闫涛蔚哼哼了几声,笑道:“你以为我愿意么?对我没有好处的事我会做么?不过,我很失望啊,本以为有商机——起码能找到块铺路石,结果……还是老兄你面子不够大么!到场的嘉宾中竟然没几个能在圈子里搅风搅浪的角儿。”
“什么叫搅风搅浪?你混黑社会还是找打手来了?闫涛蔚我告诉你,惹火我对你没好处!”那边没好气地吼道。
闫涛蔚剑眉微按,长而厚的睫毛沉沉地压住眼睑,遮挡住眸子里陡然雪亮犀利起来的光芒。
“差不多了吧?谁也别在谁面前耍横。该闹得闹完了,该得的得到了,我们——该出手了吧?”他的声音带着摄人的威严和冰冷。
那边静默了片刻,无声。
“我给你的时间够长了。”闫涛蔚嘲讽地翘起嘴角,“其实做我的下属,也没那么糟糕。你说呢——何总裁?”
何家讯手里正捏着一只酒杯,听到这里,不由得把杯子攥得更紧,直到骨节泛白发青,手背的皮肤绷得紧紧的,显出皮肤下的青筋来。
“快了。再给我几天。还有,请你离歆舒远一点!”何家讯摔了手机,又把手里捏着的酒杯狠狠砸到墙壁上。
闫涛蔚从耳边取下手机,在手里掂了掂,仿佛把玩着什么新奇的玩意儿,深邃的眸子里神情高深莫测。
他一抬头,看见顾歆舒已经从屋子里出来了,连忙开车迎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