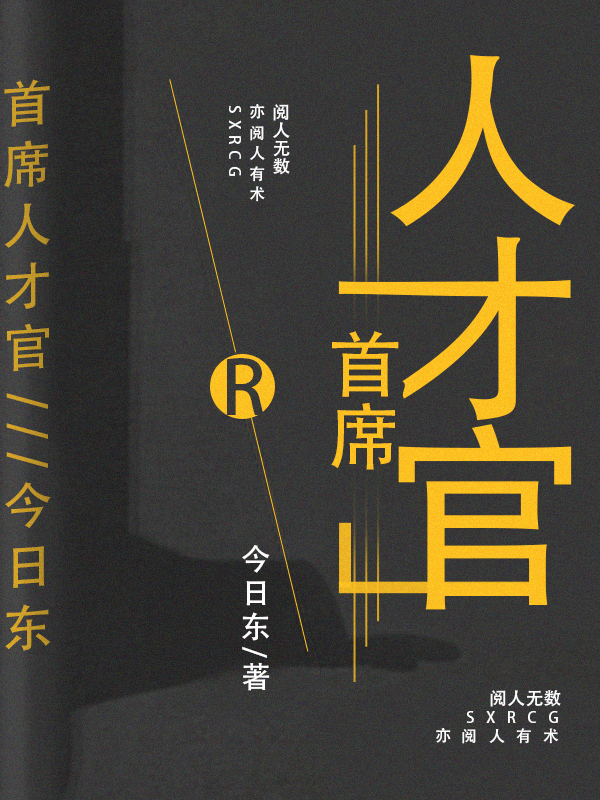在这一刻她对宜敏不由得起了轻薄之意,这世间究竟有多少友谊会最终走到这一步:在女人与女人之间,维系她们彼此的不再是感情,而是相互的争竞之心。老公,工作,房子,小孩,家产。倾心相与的交往只能在同阶层内节制有礼的进行,就象是工作中等级与人际关系的另一种延伸,只接交对自己有用的人,做对自己有利却无伤大雅的事。芳晴定下这个原则,侧开脸,坐在餐桌上听苏楷絮絮的发着牢骚。那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妙论,很慷慨,很激昂,是于事无补废话连天的那一种。她有些絮烦,于是低低说:“我去添汤。”一侧身,却恰好听见苏楷说的最后一句:“我们没有精神上的联系,没有共同的人文背景。我们更象是玩伴。”这恰好是她与宜敏之间现状的最佳写照,但孙宜敏显然不这么想。在一阵沉默之后,芳晴站在灶前听宜敏问道:
“他是谁?”
芳晴几乎笑起来。他是谁?当然是男人。不是好男人就是坏男人。一个女人一生中所能遇到的无非是这两种:他肯给钱,他不肯给钱。那些爱不爱的倒在其次,钱都落在手上了还怕什么?锅里的汤噗啦噗啦的响着,苏楷双目微合倒在餐桌上似乎盹过去。这是装的,一个昨晚还在打电话想借他人之力飞上青云的人绝不会这么轻易倒下。芳晴有意无视宜敏眼中的悲伤,低声说:“我送小苏走。”
“就住这里好了。房子这么宽,又不是住不下。况且苏楷还醉着。”
她们俩合力把苏楷扶到卧室睡下。
可只得一张床,怎么睡?
“有人等你?”宜敏问。
芳晴几乎疑心是有人知道了什么。可不待她发怒,宜敏就又说:“能等我们的人唯有父母,芳晴,你不知道,我这次回家有多难受,多受刺激。这么些年,我都只顾着自个儿,顾着我自己的心,自己的想法,竟不知道父母过的是这么困窘的日子。连吃饱穿暖都谈不上,更别提老有养病有医。他们能指望的也唯有我,我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改变自己迎合这个社会。芳晴,你不知我有多羡慕你,你至少还有一套房子可以给父母改善生活,可我呢。我竟什么都没有,连友谊,”宜敏说到这里迟疑着抬起头问道:“我们的友谊还在吧?”
其实早已失去了,友谊,连同看待世事的纯真,早就在年华中远去。留下这一地狼藉,和妄图在混乱中收获些许微利的决心。这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窥伺,企图和妒忌,这样的局面,与其说是男人造成的,倒不如说是源于自我对困窘的不甘心。人总得挣扎着才能向上改变自己,而身边的所有物就成了出逃生天的最佳助力。少有人会在身陷泥沼时还能仔细衡量助力的道德与否。正所谓成王败寇,一朝权力在手,自有言词如黄冕加身般将自己护得滴水不漏。这样的事,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芳晴只是奇怪,孙宜敏难道当真是有百分把握钓得金龟,所以竟提前将自己道德的高度提升到“一切为了父母。”其实何尝是为了父母,莫非寡妇再嫁也是不愿让家人在夜里为自己忧心?只是守不得吧,那日日的寂寞,如鸠毒在手般灼热,双眼望去,这世间没有一样是不勾人的:男子,金钱,权势,享受。喔,她竟忘了,宜敏是自山沟里重生,但凡经历过这番困苦的,应比她万芳晴这傻傻的一直在原地踏步的蠢人更富有决心与冲劲。她想到这里,不由得重重点头。友谊?好啊,她倒真想看看孙宜敏是如何在“道德的高点”上抛弃所有束缚勇获新生,成为这现实世界中成功的淘金者。应该很难吧,芳晴想,毕竟宜敏已经老了,在这个城市里无根无基。并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兴趣陪人唱出“情与欲”的大戏。男人们都现实得很,包括杨志。更何况她还不想将他还给宜敏,即使是在友谊的名目下,她也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干干净净的如白莲花般自泥沼中抽身,还转脸一笑。当自己是谁呢?啊,孙宜敏,究竟当自己是谁?
见芳晴点头,宜敏不由得一脸宽慰。“芳晴。”宜敏把手伸过去握住她的,沁凉,带着微颤的寒意。仿如孤岛重生,可有这样心态的也只是宜敏而已。小孙如今孤落无依,在城市里如一只流落折翅的雁。不靠人,行吗?要知道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见的,孙宜敏当初一意孤行要为了理想而奋斗,如今时过境迁,要为了面包而多付出代价亦是理所当然。还日本呢,人哪里会凭轻飘飘二个字便能飞抵彼岸。
“宜敏,要现实一点。”
见小孙低低的应了一声,露出深深受教的表情,芳晴不由得心中一恸。当年倒没有人肯对她说这些呢,无论如何,她都得自己爬自己摸,自己跌倒自己站立。就象现在,她分明已无力去均衡所谓爱情,友谊与现实之间的比例与份量,却仍然为了不失落任何一杯羹而坐在这里。在这里,竟分不清为什么要在这里。或许她早就应该与宜敏一刀两断,以免于将来处于两难。迟早有一日,应是终有一日,她在宜敏与杨志之间串演的角色会被曝光,届时何以自处?不知怎么,她隐约的觉得畏惧。那不是源于道德的约束,更不是因为良心的谴责。就象是小时候被人发现在墙上乱涂“XX是坏人”而衍生的愧悔:幼稚,无聊。竟不会用更成熟得体的举动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与愿望。这是她人生中被缺授的一课。母亲。芳晴在心里哀哀的喊,她这才恍然想起,为着生存,为着父母口中的一套房子,她已经很久没有与他们联络,也不愿意与他们联络了。除非功成名就,除非有足够的金钱可以保障一切感情不会受到世俗的伤害。芳晴在枕上辗转,她与宜敏在客厅搭地铺,天热,汗水一滴滴沁在凉席上。席子显然是旧的,让芳晴心里有异样的灼热。
“那个日本,到底是什么人呢?”芳晴艰难的问。
宜敏爽落的开口说:“一个客户,我用他来哄人的。”
芳晴一惊,倒把半边身子从席上撑起来:“哄谁啊?”
“想嫁的人。”宜敏声音平平的应道,她双手合十,规规矩矩放在胸前,象一个忏悔的姿势。可要做的事,在说的话,没半分悔意羞惭。“那人有女朋友的,可怎么办,总得搏一搏。”
“你倒真胆大。”
宜敏的眼睛一下子睁开,清清泠泠的与她的声音一般玲珑圆转:“芳晴,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想做的事,前人皆已做过。我们想达成的愿望,也正是后人心中的目标。正所谓前有虎狼后有追兵,以这个年龄夹在中间的,却又不止我们一两个。一个位置你若不占上去,自有人拼了命的去扑。稍有差池,错的便不止一点半步,而是数年半生。芳晴,”宜敏把头侧向她,象个孩子似的扑在芳晴胸前。宜敏的声音小而又小,呜咽着似一种胆怯的哭腔:“不管男人怎么样,我们总归是我们。”这最末的七个字诡异的在夜空中的游荡,芳晴似闻非闻,只是伸了手去理宜敏发上的绒毛,这样细又这样软,象一个人的心肠,总在不经意间撩摆动荡。
“明天我要去相亲。公司组织的,大把金龟呢。”宜敏说。
“好啊,给我,喔,是我们也找一个。”芳晴抬头看见苏楷摇摇晃晃的走过来。醒了?她讽刺的想,其实一直都是清楚的,只看在什么时候出手吧。有道是三个女人一台戏,长夜漫漫,她们究何是金龟及相应的缚龟方式做了详细的研究及论证。意见不一,各有花头。芳晴话最少,于是站出来做了结案陈词:“明天是周日,我和小苏都在开心乐园里等,宜敏就负责揸些活物过来。正所谓蛇有蛇路,鼠有鼠招,各人看各人的本事吧。”她说是样说,其实心里如何肯去,没的辱没了自己的身份。万芳晴轻轻咬着唇齿,坐在席上,看宜敏与苏楷嘻闹。心中的悲悯让她眼里的泪慢慢滑下来,芳晴拉了她俩的手说:“不管男人怎么们,我们总归是我们。”
当她们这样说的时候,都希望别人能比自己对这句话更认真。所以总是在说过之后,小心的觑着对方脸上的神气。都不再是孩子了,还有什么妆彩不能随手扮成。芳晴苏楷和宜敏在这黎明前的光辉里相互搭了手哭成一片,就象是秋日荒野上盛放的野火,在燃过之后,反而有了更深的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