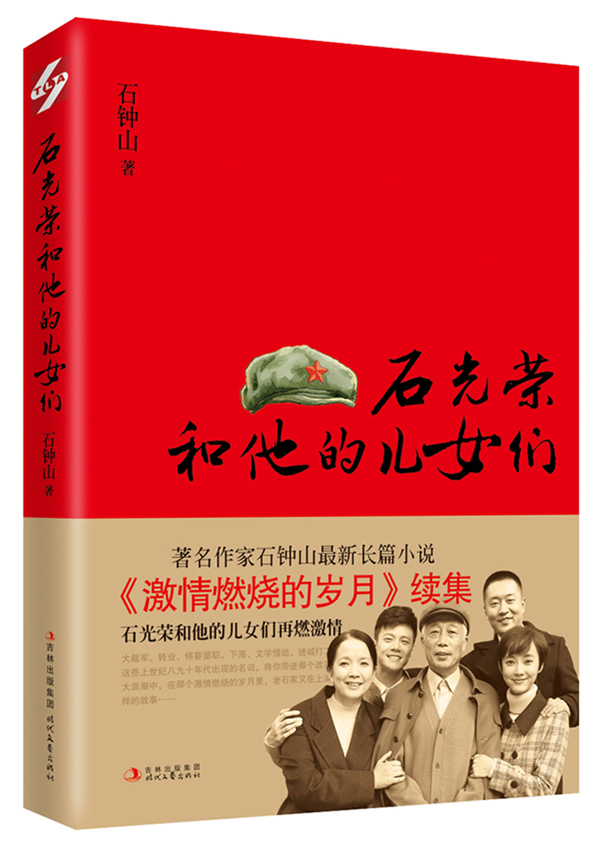她那时并不认识小林,她的注意力,整晚都集中在相亲对象的身上。平心而论,这是芳晴历年来所见到的最好的目标了:斯文大方。当然从气质与收入上讲,绝不能与她相对而坐正与人谈笑的那一个子弟相比,芳晴注意到那人衣着高雅,一扬手便有美酒食物流水价的送上来。说不羡慕是不可能的,但她这两年学乖了,很知道做人当不可逾份没分寸:这只是没道行的人才有的想法吧。过了很久,当芳晴看完了那场真人SHOW,这才领悟过来自己曾经经历了什么:友谊,爱情。这都是后话。此时芳晴正涨红了脸,一双眼闪烁不定的望向小林这一方。刚才是她鲁莽,走路太急,竟不留心扫去了林铭山桌上的一只杯子。“我来赔。”她低声对侍应说。“哪能让小姐付帐。”那桌人中间有人轻佻的应了一句。他们探头探脑的看着芳晴身后,艳遇是不能了,索性哄堂大笑。原来不过如此,芳晴轻咬着下唇,那个被她羡慕的水晶琉璃世界所有的,竟只是一群纨绔。和大部份人一样,她在心思被轻泄之后以良家子的骄矜来掩饰与伪装自己,与她相亲的那个人坐在酒吧的一角仿佛暗夜未闻。那人看着芳晴挺直腰板向自己走近,装得太过了,当那人惊诧的脸色一点一点在芳晴眼前分明,她不由自主佝偻下去。在这个繁忙的都市,一个人的自尊心从来都不是以自爱自立大度若虹,却是以另一种方式来呈现的:那是另一个,或另一群人的臣服。如果做不到后者------世人将之称为事业的成功。那么,总归会有爱情的名目来满足一个人的私欲。而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婚姻。不过是三餐一宿,她轻叹着,手不由自主抖起来。一支烟叼在芳晴唇边,这是都会里最不引人注目的一角,檐下檐上,有沉重的石块和精致的雕梁。夜雨,细细碎碎的落下来,有什么自她心里正缓慢的移挪一点一点空出去。她不觉得痛,只觉得发虚。把背抵在墙上,撑了十秒,这才缓过劲。这是不被人知晓的一幕,与她相亲的人,在半小时之前,已用隆重的礼节相互告别过了。在下一次登场之前,她(他)定会打扮如仪,照剧本上演。这是为什么呢?天知道她想要的,不过是汲一点点温暖而已。夜已经深了,似一只巨兽,冷冷的在如繁星盛锦般绽放的浮华里窥伺着每一个人。芳晴只感觉到弱,小,疲劳,及厌倦。在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家里走去的时候,她开始厌恶起这出孝子贤孙的戏码。而这也正是一个普通人被现实逼无去处之后最终的落脚地,因为恐惧现实社会会带给他们的肉体上真实的伤害,他(她)会选择以家庭为单位,试图从相爱的人身上寻找光明与突破。
她当然不知道这不过是虚妄不实的幻想,当我们所处的世界不能赋予一个普通人以正直坦率自由等品性,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不过是滋生所有上述品性的反面的温床。这样的时代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却从未象此刻那样令人惴惴不安。有什么已经被断掉,被遗失。而那失落的一部份正是教授人如何看待生与死,喜与悲。这样的感情,一个普通人的感情,绝非所谓远大的理想,宏伟的目标就能轻易的左右与安排。或许人会因为自身精神的软弱在某种授意与暗示下做出某些超乎于常理的选择,但这样的选择绝不能长久,因为它违背人性。但人性究竟是什么?无非是善的挣扎与恶的倾轧。在善恶之间,得制定规章努力约束与克制自己。这便是制度,如此而已。那些被浪费的牺牲,付出的生命,不过只是为此而已。
然而她想不了这么远,虽然命运有一天终将会把芳晴带到那里去。关于这个,她并不愿想,当然也谈不上相信。她所要的无非是一份好工作,一所好房子,一个好男人,家庭幸福,合家欢乐。这是正当的意愿,却只能在某种环境下派生滋长,诚如皮与毛。这个比喻在芳晴脑里模糊的闪过,和往常一样,她将之归类到不可理喻那一类。这世界塌下来自有高人顶着,在上个世纪中期,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流行过与之类似的说法。在这个说法背后,是惨痛的呼号与悲伤的**。
而那,是离她很远的历史。
有时想想,历史之于现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轶事?是玩笑?是秽淫?是掌故?还是什么别的,能让人明智理性的感悟?借助于历史,人能学会反省,并明了自身在现在以及将来的位置,这些课本上不会有,在分数里也不能体现。历史,在某些人眼里,是嚼过即扔的口香糖。谁会想到一颗糖会跳起来报复?关于这个,芳晴不信,万树德也不信。虽然他经历的时光远远超过女儿。但是,在他的人生经验里,历史也就是个任人打扮涂抹的**。很粗俗是吧?但一个人的行动指向不过是来自于他(她)的人生经历,他(她)经历了什么,自然将来也就会做出些什么,类似于条件反射。当芳晴一进屋,见到的就是父亲焦燥不安的那一幕。已经有好长时间,通过主动或是被动的手段,她没有看到这种场景了。乍一见了,未免生出些厌烦。已是夜阑人静时分,她不欲多事,只淡淡的点了个头。“你去相亲了?”万树德劈头就问。
怎么?芳晴冷笑着下意识脱口而出:“你还想省装修费?”
如果父亲的脸在瞬间变得惨白,并为之而失语气恼,或许芳晴还会有些微的欠疚之心。但没有,都没有。万树德神色如常,只是脸上略带点讪讪之意,象她日常见过的那些不得不将自己送上门来敷衍讨好的供应商,别开头,尽量想不起正面冲突,私底下或许就会换一张脸切齿咬牙的诅咒。象是喝醉了酒的人突然被一根针刺醒,芳晴万没料到父女之间有一天或许会走到这一步,也许会更远,远到有一天终不能相见。她隐约感觉这就是两代人之间历史的宿命,无关乎金钱,只因他们的人生是被放置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譬如黑与白,明与暗。聚光灯噗的一声打下来,连过渡都没有,背景一换,在同一个舞台上,所有的演员立时三刻,就得上演一出新版的暗恋桃花源。可怜谁是春花,谁是云之凡,谁是老袁,谁又是江滨柳。错乱的角色,如流水般悔落无情的人生。这便是两代人的宿命,在历史中的位置。如果可以失忆就好了,在芳晴身边,不是没有这样的人。那是九零后,卡啦卡啦象一张新刮刮的钞票,可以毫无忌惮的挥霍出去。
万芳晴叹了口气,努力把脸色放正了,温言说道:“有什么事吗?”
李明彩的眼泪被这一句话堪堪逼了出来,她嗫嚅着说:“是楼下的张叔说看见你和一个男人走在一起。我们也是担心,希望你找个好人家。”
都是老生常谈,她这两年历练久了,颇能应付些则个。万芳晴三言两语打发母亲睡下,但万树德不肯,“我再坐坐。”他说。这就是邀约的表示。芳晴如何肯上当。反正也不是客户,她索性别开脸视若不见的溜进帐中。夜这样深,她疲累的倦意沉沉的睡去。没有梦,更没有在光华满天满怀期待中醒来。那样的喜悦以及对生的渴慕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的她,无非是仟仟万万人中力图求生的那一个。不傻,却也不见得精明。站在青冬色的天井中央,满溢在她心中的是尽在吾彀中的悲哀。在冥冥中,芳晴仿佛听见有一个人在对自己讲:你能去哪里,又要去哪里?只在这里罢。这便是她在纵横历史经纬中的一个点,是她的宿命。而天又这样子寒,芳晴站在门角,重重的打个喷嚏,而后出门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