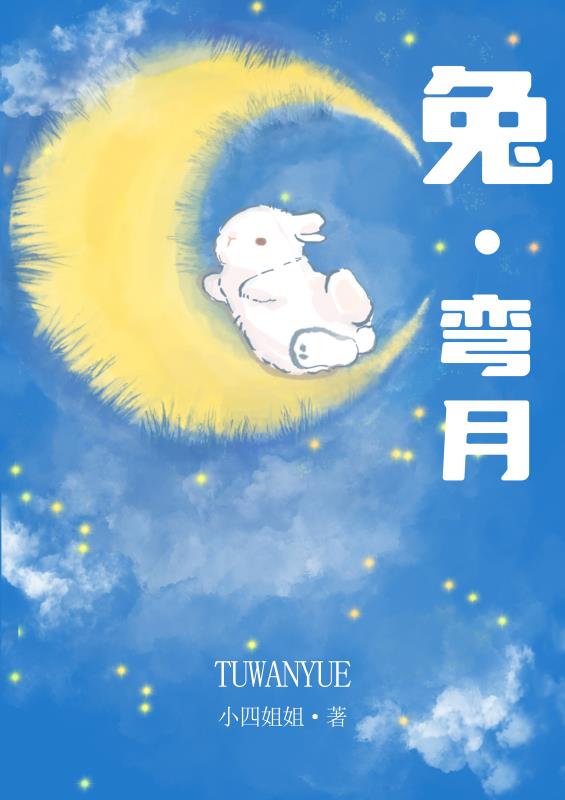(一)
还是春天,风却已经热的人喘不上气。
黑布搭起来的棚子外火光有一人高,白纸做的红脸腮的童男童女伫立两边,和纸马一同守着黑漆杂木的棺椁。几个保安神情不满的在旁观看,却都沉默不语。没人会找死人的晦气,哪怕这个死人生前无比讨人厌。
我收回目光,不再看那跳动的火苗,大概送下去几百亿了吧?三叔再贪得无厌也该够花了吧?可回头看到棺材前的黑白照片,上面那人正冷笑着盯住我,目光随着我的移动而移动。我哆嗦着,生硬的咽下口水,心里想着还该再烧几千亿。
不多,永远都不够多。
三叔生前是个开杂货店的,死于砒霜中毒,谋杀。
三叔脾气不好,得罪过不少人,但都是小矛盾,没什么深仇大恨。会是谁想要三叔的命呢?警方很想知道,所有人都想,只有我不想,因为下毒的人就是我。
三叔是我的父亲,养父,我是个孤儿,七岁前一直四处流浪,后来饿晕在三叔的杂货店门口,三叔见我可怜就收留了我。
那时三叔家里还有个女孩子,很瘦,呆在挂着干净白布门帘的里屋,头发是白的,眼睛是红红的,见不得光。
我还记得那天的情景,我躺在三叔的床上,一个白的吓人的女孩慢慢走过来,她的眼睛红的像在流血,怯怯的问三叔:我可以摸摸他吗?这么说时,她温暖的小手已落在我的脸上,仿佛化开了千年的坚冰,那一丁点暖意直渗进我的灵魂。她会是一个好姐姐,我相信。三叔大声的叫她回屋,我看见她眼中的失望和惊恐,低垂的灯罩被碰的摇晃,杂乱的光影中我的姐姐紧紧抱着黑色布偶跑回里屋了。
在流浪时,我见过许多千奇百怪的人和恶毒的事,都是冷的,只有她是温暖的,在恶浪涛天中给我生存下去的勇气。
我总梦到这情景,三十年来每一个有梦的夜晚。
三叔说那是梦,他一个老光棍家里哪来的什么女孩?还是白头发的,可笑的紧。
现在三叔死了,自以为把所有秘密都带到了下面,可我早就知道了,我确曾有过一个姐姐,在我到三叔家的那天夜里,她死了。我记得十岁时,偷偷把三叔压在箱子底的死亡证明翻出来看到,上面写的死因是器官衰竭。匆忙中只来得及看清死因和年龄,姓名都忘记了看。那时脑海里全是带着愤恨的疑惑,前一刻还想摸摸我的病孩子,下一刻怎么就会器官衰竭?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我只见过姐姐一面,可我觉得应该替她报仇,所以我给三叔的杯里下了毒。
(二)
来祭奠三叔的人很少,都是邻居,或常来买东西的熟客。大家都冷着脸,上过三柱香就走人,一个个急匆匆恨不得转身就从这个晦气的地方消失。
我很奇怪,既然这么不情愿,为什么还要来?
黑布棚外保安走了,火光也低了下去,只剩余几点火星隐在纸灰间。
风开始变得冷了,我枯坐在棺椁前,眼睛却不敢看照片里的人。我总觉得他在看我,甚至棺材里都有声响,像有具尸体急着复活爬出来,可能还要吸干我的血。
远处有汽车驶过的嗓音,夜色很黑,几乎看不到行人。
我知道棺椁里什么都没有,警察说三叔是死于中毒,属于刑事案件,尸体需要解剖化验。只是我一再坚持,他们才让默许我搭起这个灵堂祭奠。
早知道警方根本就没有怀疑过我,就不作这场秀了。我不是什么孝子,也没把三叔的杂货店看的很重,更没给三叔上过什么巨额保险,三叔的死对我来说只是没了责骂的声源。邻居们都知道我们父子关系不很好,毕竟二十几年来我就没叫过他一声父亲,要么是喂,要么是三叔。
为什么是三叔?而不是叔叔或者二叔?
因为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姐姐就是这么叫他的,这是个秘密,我想三叔也是知道的。所以,每当我叫他三叔时,他脸上的肌肉就会跳动,目光移开,不敢看我的眼睛。
今天是停灵的最后一个晚上,过了今晚,我会把三叔的杂货店转手,然后离开这个城市。
很多年前我就想离开了,继续我的流浪生涯。可每当想起姐姐温暖的手,心里就会无法停止的痛,就会想起三叔喝斥姐姐的声音,那么恶毒。因此我选择留下,我想亲眼看着他死,实在等不到那天的话,就亲自动手。
三叔身体并不好,但我的更糟糕,肾坏了,已经快没钱做透析了,更没钱换肾。时间不多,所以我选择亲自动手。
夜里十二点了,四下寂静无声,最适合回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
(三)
黑布棚里突然有刺耳的异响,是棺材的方向。我惊恐的站起后退,然后才看到一只白猫比我更惊恐的窜到黑布棚的边缘,拼命的从缝隙钻了出去。这个时候有一阵风刮过,灵堂的灯灭了,只剩下黑镜框前的蜡烛,照片里的三叔狰狞的看着我冷笑。棺材里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是有个人在不甘心的敲打棺材盖。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知道一定是保安把电闸拉了,但这个时候无论如何都无法平息心跳。难道真的是三叔回来了?可他的尸体还在医院,大概明天才会有解剖结果。
那棺材里的,是什么?
我想逃离这个地方,但腿却动不了,甚至转身都做不到。
“刘雅,我来了,你回去休息会吧!”
大伯的声音突然在背后响起,我几乎是跳着转过身,让大伯吃了一惊。
“刘雅,你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差?是不是又该做透析了?”
大伯宽厚的手掌扶住我的肩膀,硬生生把我按在椅子上。我指着不停发出声响的棺材,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大伯惊疑不定,慢慢走过去,然后松了口气,把一幢倒在地上的纸别墅扶起,棺材里的声音立即消失了。
“看你这胆子小的,是风把你爸的别墅刮倒了。”
大伯手里拎着只太空杯,我盯着看了半天,才确定,是我第一次给三叔下毒用过的杯。
三叔脾气不好,但并不表示没有心机,我猜他早看出我想毒死他了,所以才能躲过两次下毒。
我记得那是个夏天里最热的星期天,三叔要出去进货,我乘他不注意,在三叔新买的太空杯里下了砒霜。但下午三叔平安的回来了,问起那只太空杯,三叔说送给大伯了。我还担心错杀了大伯,但等了很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大伯,您怎么来啦?您的身体也不好,现在虽然是春天,但晚上还很冷,快回去吧,我一个人能行。”
大伯挤出一个笑,随即叹了口气。
“回去也睡不着,不如咱们爷俩说会话吧!”
我不是一个聊天的好对象,更不是一个好听众。我在心底想,但大伯却没一点要走的意思。
“你爸从不让我跟你说,我曾过继给他一个女儿,叫乐乐。按年龄排,是你的姐姐。”
我心头狂跳,身体禁不住颤抖,天旋地转。
(四)
“乐乐一岁的时候就过继给你爸了,这孩子命苦,很小时起就发现得了白化病,后来又得了肺病,见不得光吹不得风,身子很弱。后来你来的那个晚上,乐乐细菌感染突发并发症走了。你爸一直不让我们和你说,照片都不让摆出来,其实我和你婶都挺恨你,觉得是你克死了乐乐。只有你爸他总说,乐乐喜欢你,说你来了,她就可以放心走了,你爸就会不孤单了。乐乐临死时是这么说来着,所以这些年,我和你婶才没逼着你爸赶你走。”
大伯的声音像从天边飘来,我弯了腰,把头埋在两腿间,咬着手指喘不上气。没有哭声,泪水却源源不断的流淌。
原来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只有我不知道。
原来全世界的人都在保护我,只有我在莫名其妙的怀恨在心。
怎么会这样?我不停责问自己:怎么会这样?
我的姐姐叫乐乐,她希望我和三叔都能快乐的生活,可我都干了些什么?
“我知道你难过,很后悔。”
大伯的手落在我肩头,他的叹息那么沉重。
“大伯,我……我给我爸……是我给我爸……”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
大伯阻止我继续说下去,他轻拍我的后背,让我的呼吸能均匀些。
“你那年考上清华大学,但家里没钱供,所以只去了三流大学,你爸为这事后悔了整整十年。他总跟我说该早点把店卖了,这样你就能上清华,这样后来你谈女朋友时,女方家就不会因为你文凭不是清华而看不起你,也就不会吹了。”
我一下子想起曾经爱过的那个女人,她的一顰一笑都重新出现在眼前,还有分手时的绝情,心里痛的更利害了。
这个世界是现实的,不会因为你是弱者而多出一点怜悯。
“大伯,是我给我爸……”
“听我说,孩子,这些话大伯憋很久了,让我说吧!”
大伯掏出手绢递过来,我颤抖着接过,却擦不净脸上的泪水。
“后来你得了肾病,你爸急的跟什么似的。实话跟你说吧,为了给你治病,杂货店早抵押出去了,你做透析的钱都是我和你婶出的。你爸不让说,怕你心理有负担,病就不好治了。为了借钱,你爸的脾气越来越坏,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遍了。可他有什么办法?他就剩下你这么个养子,他不想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我不知什么时候跪在了父亲的照片前,大伯仍在继续说着我所不知道的真相。
灵堂里刮起风,蜡烛的光亮闪烁不定,照片里的那人仿佛在无声的叹息。
“我知道是你下的毒,你爸也知道。你第一次下毒前,你爸就发现你不知从什么地方弄了些砒霜,你爸以为你是想要自杀,所以整天提心吊胆。后来你在他杯里下了毒,你爸灰心了很久,他以为你给他上了保险,想骗保,这样你就有钱换肾了。可后来一查,你根本就没给他上过保险,你爸和我说:这孩子是想和他一起走。”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变凉,可心底却仍有一团温暖,温暖的中心却是阵阵剧痛。
“你爸为了给你治病,想到一个赚钱的方法,他给自己上了巨款保险,一年前就上了,直到现在才动手。我知道你这几天一直在奇怪,为什么下毒的那几天没事,都过了快一个月突然就中毒走了,其实是他自己下的毒……”
我不知道大伯什么时候离开灵堂的,我抱着父亲的照片哭的晕死过去。
我弄错了很多事,而且没法补救,谁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五)
第二天,灵堂撤了,父亲的遗体还在医院。
大伯告诉我保险公司的人今天会来,要我准备好,别露破绽,要不然父亲就白死了。
我呆在家里,整理原准备丢弃的父亲的遗物,才发现原来父亲过的那么苦,而我却毫不知情。眼睛哭肿了,头一直发晕。邻居冷着脸送来吃的,安慰的话也夹杂着刺,她们是知道父亲的不易,只有我知道的太晚了。
中午的时候,保险公司的人还没来,却有两名警察登门。
他们说父亲体内没有发现砒霜,但症状的确是砒霜中毒,大概是新型毒药。又问父亲生前最后一个月都与什么人口角过,案子可能会拖一段时间,如果能回忆起什么线索尽快找警方联系。
我听不到警察同志的声音,看不见他们的脸,脑海里一片空白,许多画面在眼前闪过,是父亲出事的那天的画面。我看见父亲偷偷进入我的房间,然后拎着水杯去了杂货店,我回到房间查看原来藏砒霜的地方,果然被动过了,我冷笑着走到窗前,看着父亲走远的背影,他不知道,第二次下毒未果后,我就把剩下的砒霜全部倒进了河里,藏砒霜的盒子里装的是感冒药粉末。
充满邪恶的行为,为什么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
我下的那份毒药,即使没有毒,依旧会致命。
我终于放声大哭出声来,让两位警察满脸错愕,这个时候保险公司的人也来了,但我仍当着他们的面把所有事情都一一讲了出来。
我不在意我的生命,可我希望死去时能得到安宁。
大伯来晚了,他责怪我辜负了父亲的遗愿,可我不后悔,那是我该得的报应。
谋杀未遂,虽然父亲的死与我无关,但仍判了两年徒刑。至于巨额保险,我根本不敢想,可在大伯的争取下,这桩难判定的保险还是做出了理赔。
我会等到合适的肾源吗?不知道,我只希望剩下的每一天都过的开心,替只见过一面的乐乐姐,和让我心痛的父亲好好活下去,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