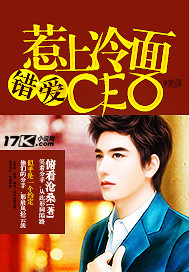天已向晚,罗心倚身在床沿,心绪飘荡。这时敲门声响起,她问道:“谁呀?”夏光的声音回答:“罗姑娘,睡了吗?天色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我就不进去打扰了。”说完转身离去。罗心想道:“这夏光倒有自知之明,分明想来见我,但恐深夜不便,就又改变主意了。原来他并不如我以前想象的那么环,至少我没有听说她的太恶劣的行迹呢。”
夜凉如水,初春的夜晚天犹寒冻,罗心躺在床上,被褥毛毯都是上品真料,想见得是夏家对她格外爱护。她只觉一阵暖流涌上心头,沉沉睡去。天亮的时候醒转,侍女已先一步送来热乎乎的洗脸水,见她起床,连忙走近来叠被整床,勤快得很。罗心笑笑,问:“小菊,你每天都是这么早起床么?”小菊边干活边笑道:“是呀,小姐,你昨晚睡得可好?”罗心道:“好得很,哦,平时夏老爷和夏公子待人怎么样?”小菊似乎想了一会,说:“当然很好啦,依奴婢看,夏少爷对罗小姐您可是一片真心。”罗心啐道:“你这小妮子,乱嚼什么舌根?”小菊嘻嘻地笑,忽然又问:“小姐您觉得我家少爷怎样?”这话怀有征询试探的意味,罗心当然明白,就道:“他只是我的救命恩人,当然是好人了。”这话似乎答非所问,小菊也没再问,待罗心洗漱完毕,才将洗脸盆端出。
不一会,夏旷添一派慈和地走进来,和昨日见面时的那副嗔怒的脸容完全不一样,才一见面就说:“罗姑娘,你今天气色好多了,过的还习惯吗?”
罗心这回见到夏旷添,虽然没有十分热络的表情,但也不再表现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色了。闻言点点头道:“多谢老将军救命之恩,小女子沉齿难忘。”夏旷添摇摇手,“罗姑娘,千万别说客气话,平顺王爷在世时我是相当仰慕尊敬的,老夫年纪不浅,人生经历也不短,历过艰难困苦方知为人不易,能够帮贤侄女那是快慰的事。哦,现今不方便称呼贤侄女一声‘落晴郡主’,侄女不会介意吧?”罗心黯然道:“夏老将军只管叫我罗心,那什么落晴郡主是个累赘的名号,不叫也罢。”夏旷添颔首道:“那么,老夫就有僭了,姑娘若是赏脸,不凡叫我一声伯父,以后大家相处,融洽如同一家,我会视你如同己出以慰王爷在天之灵。”罗心一阵感动,点头应了。
早饭在大厅里团聚,罗心被请上**,左边是夏夫人,右边是夏光,坐对面的是夏旷添,似乎已没有明显的主客之别了。夏光今天特别的高兴,没忘时不时为罗心夹菜添饭,弄得一旁的侍女插不上手。夏夫人嘻地笑道:“瞧光儿这孩子,最近几天精神儿多健。”罗心脸一红,低低地道:“伯母说笑了。”她决定不以郡主的身份现世,再说这劳什子的郡主委实不伦不类,所以说话待人较先时客气礼貌。夏旷添老脸安慰,心怀一畅,就忍不住多喝了几杯酒,一脸平易近人的气度,顿让罗心生出无限好感。夏光听母亲说话,也回话道:“娘您别说笑,罗姑娘来到我们家,我这个做哥哥的能不关心照顾?娘您若叫表姐表妹们来家做客,我照样是这样子的。”两句话说得不亢不卑,一家子听得其乐融融。
饭后,夏旷添当着罗心的面亲自叫来两位亲信家仆,责成火速赶往天山求取灵药,千嘱万嘱,务必尽快将“千年何首乌”弄回来。实则,他的友人早年确曾得过一棵,历经沧桑年月,这时是否还有存留并不可知,碰运气的可能性相当大。饶是如此,罗心也感动非常。
又过了数日,罗心一直呆在夏府,平日除了女眷们活动的后花园附近,别的地方她一步也不敢多走,真像是一个听话的姑娘。其实,她的心思里不知残留多少的苦楚,难道一辈子终老此地么?但是……李萧儒已经成家,她一时心灰意冷,外面的花花世界已不足以唤醒或者活跃她的心灵了。这段日子以来,夏家俨然良善之家,每个人都把她当成了亲人一般,连平日里冷峻的夏老爷子,一见了罗心的面也掩不住慈和关爱的情怀,真的视同自己的孩子一般,相反地,有时会当着罗心的面训责儿子的不是,教夏光好不难堪。
这一日夏旷添在书房伏案阅卷,罗心孝心十足地为他送上一盏热茶。夏老将军老怀大慰,忍不住颔首连连称许,说道:“贤侄女,你身上的毒伤还会发作吗?”罗心回答说:“暂时不会了,张御医送的药可真灵,只要每三天服用一颗,就可暂时稳住毒势发作。”夏旷添皱眉道:“唉,这毒伤还真是让人担心,能及早断根那才好。张御医医术高超为人忠良,伯父甚是敬重,今早已经派家丁前去邀请,过会儿可能就会为你看病来了。稍后你还得多多劝醒,千万不要让张御医露了这里的口风。”罗心点头道:“这个自然,张御医为人持重,伯父你放心好了。”夏旷添又沉吟道:“明日伯父要随同皇上亲征沙场,家里的事就有劳贤侄女协同照看了。”罗心欣然应道:“伯父千万不要见外,侄女会好好帮着照看府上的。”夏旷添捋须长笑说:“这就好,这就好。这阵子天山若来灵药,那就真的让人开怀了。到时伯父不在家中,你尽可遵同张御医的良方小心服用,将毒物连根拔除才好哪。”罗心感动得说不出话,心想这老人家对我真好,这几日来他们并没有逼我嫁做夏家儿媳妇,大概顺其自然看开了吧。骨子里,她并不愿意委身下嫁夏光。
下午,张秋衡果然就应邀而来,小心地为罗心把脉看病,留下药物,另告知平顺王爷的后事皇上已经派人秘密料理,罗心闻言,禁不住感怀流泪一番。张秋衡不敢多留,事毕匆匆而去。第二天,夏旷添全副将军装打扮,苍老的身躯和面庞被铠甲衬托,雄赳赳气昂昂好一副威武形象,准备离府出征了。夏光受皇上器重,委以二路少将军职,只等一路大军冲杀疆土,这二路军再整装进发。
家人饯别宴上,罗心身在其中。罗心实是唯一的外人,连日来受夏家看重,从未将她当外人看待,大家依依话别,只望亲人前途珍重,早日驱逐蒙古余孽将捷报飞传。宴后夏光和夏夫人送夏老将军直出府外,罗心不便出府,只得默默望着一行人背影消失,心里掩不住万般祝愿和人去心愁的凄凄感。
她回向自己的厢房,从后花园穿过,一双彩蝶翩跹嘻戏双宿双飞吸引了她的眼球。“能够做这样的一只蝴蝶多好!”罗心天真地想,“现在,我的人生已经暗然失色了,将来如何肯定比不上这双蝴蝶,它们自由而恋春依春,春来喜气洋洋,我可能也感受到这份春意了,但是心中为何还那么冷呢?”她顿了一下思绪,想起李萧儒,心儿忍不住抽痛了一下。“这会儿,李大哥大概跟云妹妹双宿双飞了!”她想着,眸中的失落感越来越重。
实则,此时的孙锦云真可说是气恨失望交集而至。那天从外面游山玩水回来,她确实美美地睡了一觉做了一个好梦,梦醒时天亮了,洗漱完毕去找李萧儒,好半天没人应声开门,就急忙推门而入,见到那封告别信,气得抖手撕成碎片。她本来是一个刁蛮的小丫头,只因连日来遇着家庭变故,才收敛起旧态,人仿佛也变了样,这回受到刺激,就不由得恨起李萧儒来。李萧儒在信上说得简单明了,说是大事未了,迫不得已不告而别,望孙锦云孙夫人原谅。孙锦云撕了信,恨恨地道:“这个呆头鹅,亏我对他一片真心,居然这么样对我,连要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孙夫人闻声赶来,只暗怪自己昨晚太过鲁莽,撮婚不成反逼走李萧儒。她以为李萧儒是因她昨晚的一番话而不告离去呢。当即好好地安慰了孙锦云一通,说缘分莫强求,是你的总是你的,云儿你何必太认真?孙锦云可不依,哪里听得进话?暗中决定非得当面问罪李萧儒不可,当时打定主意,气呼呼地回到自己的闺房,饭也不想吃了。孙夫人又心疼又难过,只想让她自个儿去静一静,待到实在忍不住,亲自进房劝女儿吃饭时,才知道闺房中早已人去楼空。
这番经过罗心哪里知道?她还以为李萧儒和孙锦云永结连理了呢。当日夏旷添父子说得活灵活现,而孙锦云对李萧儒生情这事又不假,李萧儒受她一顿不得已的狠心之言排挤,当然有可能接受云妹妹的一腔爱意了。不由得罗心不信。罗心昨日也曾向张秋衡打听过消息,也顺带问了张大娘的下落,张秋衡平日深居宫中,只知道女儿觅地另居,其他诸如李萧儒动向,确实不知情了。
整天闷在夏将军府的后院里,心情实在是糟。罗心感觉度日如年,这一天北京城下起了第一场春雪,一时兴起,她便要出门观雪。下雪天头戴避雪遮风帽,女子另加丝巾蒙面是很平常的事,罗心也想这么着,料想绝对没有人能认得她。夏光拗不过,再说内心深处也确实存在要与佳人雪中漫步的遐想,便答应了。二人整装停当,并肩行出夏府。
这是半月来罗心第一次外出。感觉里,外面的空气仿佛比夏府里的空气还要流通顺畅,由于是元宵日,人人为着今晚的花灯炮竹节目做准备,街上真个是人流继踵。雪不大,轻盈盈飘虚虚的,从天际如鹅絮般散落下来,让人联想起九天仙女在天上撒花,花儿变成飘雪,落入凡尘,也落入每个人的心中,在那里浮升感叹。不一会雪停了,人似乎更多,罗心走得累了。夏旷添心细,坚持要找地方休息,又不便到大客店里落脚,就寻了一处幽静的林荫地,双双并肩坐在石凳上歇脚。
春风吹得罗心细腻白嫩的脸蛋现出潮红,衬着娇美的琼鼻水眸,浑身散发出一股醉人的香息。夏光偶一回目,瞧得眼都快直了,心说:“老天,罗姑娘真是天女下凡呢,这般楚楚动人的模样,真是好迷人,若能受到佳人垂青,便是要我少活十年也值了。”心里想着,手不知不觉地伸出来,要抚上罗心搁在石凳边沿的玉手。罗心没察觉,她的眼中被另一幕景象惊呆住了。
远处,林荫的那一头,李萧儒缓缓然地沿路向这边走来。蓦地,孙锦云的身影打斜里出现在李萧儒身边,像是又惊又喜又十分动情,小拳头儿想捶在他的身上,落下时却改捶为抱,将整个身子伏在他的身上。李萧儒没有拒绝,两人像是十分感动,抱得紧紧的。
罗心眼见如此,虽然相隔太远听不到对方说话,瞧这情形也够了然的了。她不知,李萧儒本是逃婚而来,孙锦云随后出走,为的是找他问罪,两人这一见面,孙锦云气也消了,忍不住动情地抱住李萧儒大哭,将满腔的委屈尽吐无遗。李萧儒见这个云妹如此痴情,一时不便拒绝,任她抱着,两人偎依在一处。
也合该有事,无巧不巧正被罗心撞见,日前夏旷添父子为了留住罗心,而编了李萧儒成家的谎言,如今不正是最好的见证吗?罗心脸蒙纱巾又身在远处,李萧儒当然认不出来,而她可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一痛,又感到莫名的委屈,遂站起身来,大声地又像是堵气地说:“走吧,我们回去!”
夏光正陶醉在佳人的绝色风采之中呢,手刚刚伸及罗心的纤手想要忘情地抚摩,不料罗心突然起身说话,还以为被罗心看破企图,心一跳脸发红,也就不敢说一句话,随在罗心身后走回夏府。其实他本无明显地亵渎美人的意思,刚刚是心中朦胧的不知觉行为,幸亏罗心没留意。这时夏光眼中只有一个罗心,当然不会看到远处的李萧儒和孙锦云相拥相抱的情形,否则他不知会不会乐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