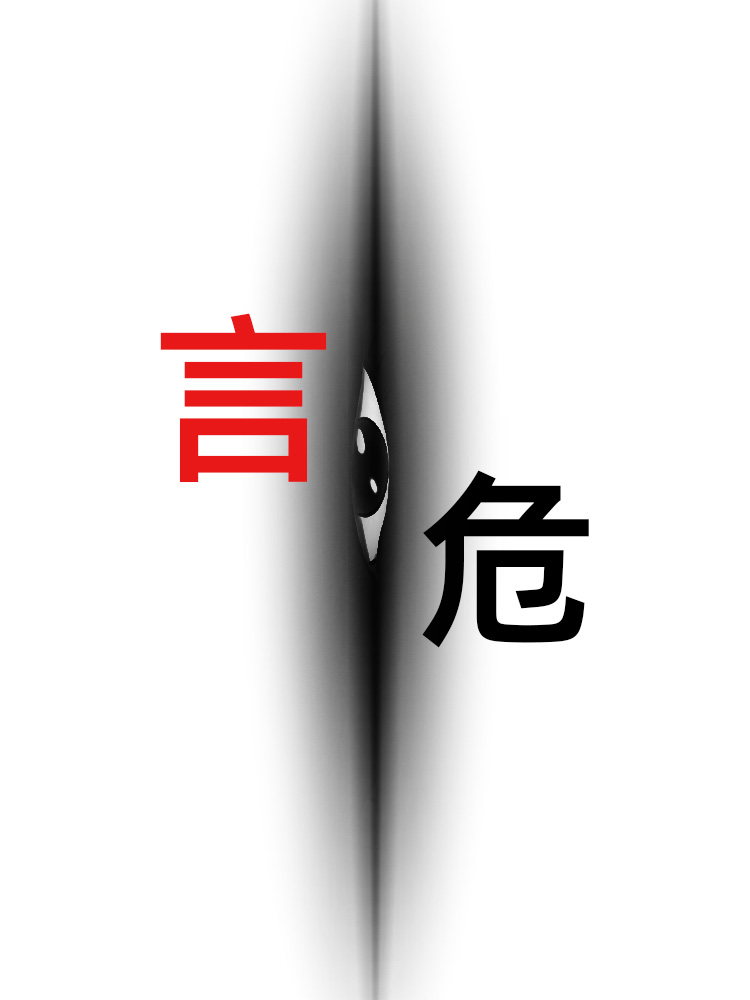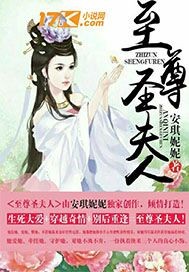引子
老罗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捏的生疼,慌忙说到“记住,千万不能在井下睡觉。否则……”说完便垫着右脚走了。 ”
你知道什么是绝对的黑暗吗?你知道绝对的安静什么感觉吗?你体会过在绝对安静和绝对黑暗的环境里睡觉的感觉吗?
伸手不见五指就是形容夜里最黑的词了,可当眼睛能适应黑暗以后还是能看得清手指的轮廓。而绝对黑暗犹如被包裹在厚重的墙壁里,孤独和恐惧犹如恶魔一样笼罩着你。就连时间都似乎被刻意调慢了一般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犹如置身另一个时空。
我出生于西南边陲的一个小镇,高中毕业以后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南下进厂,在厂里认识了同一条流水线上的老乡朱逸。因为都是老乡,而且我们也在同一个宿舍。渐渐的熟悉了,每天7.00上班,晚上10下班,有时候甚至会加班到12.00。工资由于是组长打等级,没发工资之前,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工资,在工厂里每天超过12小时候的工作真正让我体会了社会底层的艰辛,加上江南的夏天真的很闷热,车间里就连风扇也没有,特别是中午,喝一口水都能立马化成汗凶猛的往外流淌,闷热和困倦会一同席卷而来,就算是热的后背湿透,车间里坐着也能睡着。那一段日子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也许是每天下班之后我们能喝着两瓶啤酒就着一桶泡面坐在工厂里大树下享受一刻自由时光的美好,又或许是对领工资时的憧憬。但是一切都被两个月后发工资时的工资所改变了。由于工资是由组长打等级,我和朱逸都是D等,所以我们的工资都是一千多。而组长他老婆和他们湖北的老乡则都是五六千,最低的也是四千多。拿着薄薄十几张钞票,想着苦了这么久,才这么点钱,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夹在里面的硬币也因为手抖而掉了出来。
那天下午是我们第一次矿工,我坐在工厂门口的路边。朱逸则是一把脱下厂服,撕成两半就丢在了路边的树上。骂了一句:艹,这样还不如去挖煤,至少不会不会像这样被人耍。随后他给我说“小秋,回去我带你挖煤,绝对比这个工资高,而且我姐夫现在是包工头队的队长了。”我想了一晚上,还是不确定要不要挖煤。但是肯定是要辞职的,
第二天我们去辞职,组长说,辞职要提前一个月申请,否则便没有工工资。朱逸听他这么说,立马跳起来给了他脸上一拳,朱逸和我比我大两岁,虽然看起来不怎么壮实,但那一拳让组长立马口鼻冒出血来,组长的三个老乡见状也就立马冲了上来,我自然也加入了这场战斗。直到组长老婆过来把组长带去医院,才结束这场战斗。气也出了,人也打了,当晚我们便鼻青脸肿的连夜坐上了回西南的火车。我也算是被动的跟着他来到了矿上。自此便有了这一系列的诡异经历。
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又转了三趟车以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小镇,小镇在一个山腰上,十月的天气小镇依旧大雾弥漫,车灯连前方的路都看不清,副驾驶伸出头去指挥我们才勉强到达镇上,到镇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二点了。吃了一碗面之后,我们在路边等着朱军的姐夫过来接我们。夜里两点终于到达了矿上,依旧是大雾弥漫,东南西北是一点都分不清,朱军姐夫给我们安排了住的地方以后随便聊了两句就各自睡了,我从来不认床,倒头便睡。
第二天一早,朱军的姐夫开完会就来叫我们去吃早餐,所以便起床了。我才发现昨晚睡得被子都黑乎乎的,门边墙壁上有个小圆镜子,我照了照,发现脖颈处全是黑灰。可能是被子上的煤灰吧。十月的天气这里依旧能感觉到冷,好在墙角处有个电炉丝在烧着,源源不断的提供着热量。电炉丝的边上还挂着几件工作服。墙壁四周都是黑灰色的。我们住在三楼,出来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阳台上的玻璃没有一扇是完好的,穿过走廊走到另一头的楼梯下楼坐上朱军姐夫的面包车缓缓的往镇上开。穿过一个大铁门便出了矿。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个体态虽胖但却不臃肿反而有气质的圆脸平头中年男子,熊老板介绍说这是刘老板,他是干掘进的包工头。朱逸的姐夫姓熊,大家都叫他熊老板。40出头,头顶发量不多,走路沉稳有力,脸上虽然没多少肉,但人非常的精神,昨夜初次见面,就感觉人是靠得住的那种。话不多,但谈吐不凡。
一路都是上坡,路在山腰上,犹如一条盘旋于山上的大蛇。可见当初修路的艰辛。今天天气很好,应该是个晴天。远处的天空清晰的透出了些许太阳的光线,我打开车窗,使劲的吸了两口香甜的空气。没走多远便是一路的下坡,不多久便来到了镇上,小镇是沿着盘山公路修建的,两边都是房屋,紧挨着路边。街道中部一侧一条水泥路转进去有一块开阔的场地,应该可以停五六十辆车吧。这片停车场的尽头是一栋三层的政府办公大楼。停好车之后在转进来的路口一家早餐店吃的蹄花粉,每人加了一个蹄花,蹄花很糯肥而不腻,特别筋道。我们也是边吃边聊。朱军的姐夫也没问我们为什么突然过来。直接开口说道“既然来了就好好赚点钱,你们可以学机修工,学会了轻松工资高,我们现在的机修工都是开9000的工资。但是也危险,有很多机修工的这个指头都是少一节的(他用食指比了比),想不想学嘛?”朱逸一脸不屑“怕哪样哦,我要学。”我没有说话。他可能看出来我不想学。随后说到,“还有个工作也挺轻松,听到铃声的时候按一下开关就好了,250一班,就是时间有点长,12小时。也有点远,差不多是井下最深的地方了”说完看了看我。我听到工作这么轻松,而且还工资还这么高于是想也没想便答应了下来。
回到矿上之后,熊老板说“你们才来,休息两天等体检了就可以上班了。”我和朱军都满口答应着。趁此机会我们正好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熊老板听到我们想熟悉矿上的环境以后,在一楼的小卖部拿了一包烟,请看门的老罗带我们转转,他便忙去了。老罗50来岁,身材高大,穿个有点像军服的军绿色大衣,头发蓬松。走起路来右脚有点不太能伸直,走一步右脚向外提一脚。他身后跟着一条大黑狗,比普通摩托车小一点,身上的毛发就像老罗一样,蓬松而油腻。他走到哪里,狗就跟到哪里,他停,狗就坐下。拿到烟后他很开心,由于朱逸不抽烟,他散了一支给我,我们边聊边慢慢走着。
我向大门口望去,一条散满煤沫的十来米宽的水泥路延伸了二三十米连接路边的盘山公路,一边是去镇上,一边是去县城里,煤矿坐落在一个半山腰,整体呈阶梯式,大门口路一边是高于路面厚三四十公分的大铁块,正好够一个四桥车停放,老罗介绍说,那是煤车出去时候称重的,叫地磅。大门右边是一栋三层小楼,老罗介绍说一楼是磅房,也就是煤车出去过完磅开票的地方。二三楼便是宿舍。和这栋楼相隔二十来米的地方是一栋L型比较干净也是最大的一栋楼。这里是矿上办公楼,监控室以及矿上核心人员的宿舍。背后便是盘山公路,由于地处不平,三层的楼只比后面的路高出一点点。二者相连的中间是由铁皮盖起来的地面机修所。楼下便是一个一亩地左右的空旷场地,停了三四辆车。铁门左边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一楼是变电所。再往下便是我们昨晚睡觉的三层楼房。一楼有家小卖部,熊老板住在三楼中间的一间。
我们这栋楼下有个三四百平左右的空地,对面是一栋二层楼房。一楼一边是食堂一边是澡堂,澡堂要从二楼才能下去。二楼一边是开班前会的会议室会议室在食堂的楼上,中间是充灯房,每个灯都有编号,上班之前过来领,下班又交过来充电。另一边是下到澡堂的路。由于西南地处不平,这栋楼比我们住的这栋矮的多,二楼居然还没有这边一楼高。两栋楼呈八字型,开口向路边。食堂也是在靠路的这一边。澡堂的旁边退向外四五米是一个低矮的瓦盖起来的公厕,大概十几个蹲位呈一字型排列。食堂这栋楼的旁边是一栋三层的员工宿舍,和这栋楼间隔五六米,与这栋楼呈垂直形状。外面和出矿的路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空地。宿舍的右边爬几级台阶是一栋二层民房。周围盖满了租给工人们的小砖瓦房。
路一直延伸到一栋三层的豪华别墅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罗总的豪宅。路的右边都是堆放煤的场地。各种皮带运输机和筛煤机哗啦啦的响动着。办公楼的右边往下三十级台阶左右是一栋一层的库房。库房对面也是堆放煤的场地,边上就是围墙了。库房对面有个一层的小房子,大概五六间,在地面筛选煤的工人一般在里面休息,这类工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女工。这小栋房子和库房也是呈八字形,可能是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吧。只能这样建,中间往外退五六米离这上面高三四米的地方是处理污水的一小层房屋。这些所有的建筑围成一个圈,中间都是堆放煤的场地。
就这样边走老罗边给我介绍,由于半路的时候朱逸被他姐姐叫走了,所以我跟着老罗走完了这一圈,又回到了小卖部门口。我买了瓶水递到老罗的手中,他也不打开,笑着说“挖煤苦的很,你们这小身板怕是干不起诶。”我给老罗散了支烟,“熊老板是我那朋友的姐夫,他学机修,我在井下按一个开关,就是时间长点,好像是井下最深的那里。”我刚说完,老罗猛地吸了一口烟,右脚突然不自觉的又向外提了提。可能是走累了吧。他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烟随着他说话全吐到我的脸上,“你确定是最深处的那台?”我随口说道“我也不知道,可能吧。怎么了?”这时候,路边尘土飞扬,一声急刹车。朱逸正好和他姐姐开车回来了,他们买了新的被褥。我要去帮忙搬被褥了。正要移动脚步,老罗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捏的生疼,慌忙说到“记住,千万不能在井下睡觉。否则,你有可能就出不来了。”说完便垫着右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