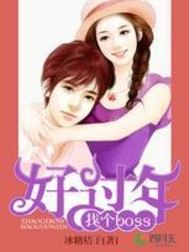悲剧的开端,只是一件日常琐事。
那天晚上,月色极好,公孙策就如往常一样梦游过展昭的窗前。展昭也如往常一样,无视公孙策慢慢飘远的背影,在灯下算账,克扣各人的零用钱。当公孙策第二次经过他窗前的时候,他已经合上了账本,打算在睡前巡视一下菜地。
地里的蔬菜瓜果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几片嫩叶东倒西歪毫无生气,惨白月光下更显得可怜。展昭蹲在地里叹了口气,虽然他致力于种植业,但总是不怎么顺利。有时候,展昭不得不怀疑自己也许没有种菜的天分。
就在他长吁短叹的当口,一个黑影踩过墙头,从展昭的头顶跃过,落下一个轻巧的黑影。他还来不及反应出任何疑问,已经本能地拔腿追了上去。敢拿开封府当过道,他不知道这里是谁地头么!两人在瓦片上飞步,九转八弯。前面的黑衣人眼见要就要被展昭追上了,回身丢下一颗火药丸,火药在展昭脚边炸了开来,他急急退了两步,眼前一片白雾,伸手不见五指。
“就这么让他跑了,真不值。”展昭咬着牙道。
“我也觉得不值。”白玉堂的声音从下面一路飘了上来。
“你又怎么了?”
“让你踩了半天我觉得很不值。”白玉堂说得咬牙切齿的。
低头,难怪地上软趴趴的,原来是老鼠肚子。展昭赶紧挪开脚。
“你追谁呢?”
“我要知道还追个什么劲儿。”
白玉堂在一旁掀鼻孔:“好好,你有理。”往下一翻身,稳稳落地,“我睡去了。”
这件夜半小事,很快地过去,除了白玉堂还谨记着肚子上的一对脚印,就没有人再记得那个晚上了。
今春又到了每年的科考之期,各地学子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一时间八卦之风更盛于前。《景祐杂报》特地开辟科考专栏,每日不间断贴身报道考生动态,热门人选专访。礼部司科考之职,这些天更是忙得脚底朝天,彻夜加班,一个个累的面青唇白,被舆论戏称为“考期瘟疫症”,一沾即死。
那天包拯下朝回来,就苦着一张脸脚步沉重,比平日更加浓墨重彩的姿态,像个为民请命又被奸臣陷害的好官。从进门到在饭桌边坐下,一路叹不完的气。包拯面色浓重地拣了根油条塞进嘴里咬着。香脆有劲,软硬适中,端的是一根好油条。于是哭丧着脸又多咬了几口。
“老包你能不能别用这个脸色吃油条。”白玉堂说,跟中毒了似的,害得他都没食欲了。
“唉……满腹心事,更与何人说。”放下油条,皱着脸喝口粥。
白玉堂咂了下嘴,继续没食欲。
“又怎么了你?”展昭问,在他的记忆里,包拯鲜少有这样的情况。一般上朝是他带着人玩儿,偶尔被人玩儿一次,他也是意气风发地要把人再玩儿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要有科考。”包拯感慨。
“没有科考,你怎么当官?”白玉堂不屑之,最烦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
“要当官,总有办法。”包拯摸摸下巴。
虽然人人都有好奇心,但是没人想问他有什么办法,那绝对是旁门左道,鬼哭神嚎,欺师灭祖,还是不知道为好。
“对了,展昭你是怎么当的官?”白玉堂又问,他忽然想起这个问题,是他们一直在回避的。其实有些事,不是好不好,只是习不习惯。
“我?我是由老包举荐的。没考过。”展昭回想起当时,他还没有看透包拯邪恶的本质,只觉得这个人胸有一腔热血,必能为国为民,脑子一昏就跟了他那么多年,将他整个人生都扭曲了。算了吧,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不好。
“那公孙呢?”
“我考过啊。”
“居然没考中?!”这让白玉堂很意外,以公孙的学识和见识,怎么都该是三甲材料吧。
“啊,那是,”公孙策脸上有些尴尬,“我在考场里睡着了。你不知道那地方,又静,又没人喊我起来。我就足足睡了三天。”
“……公孙你这种个性真难得。”
“闭嘴吧,白玉堂。”包拯出声阻止他。白玉堂破天荒地没再说下去。考场失意对任何一个读书人来说都是不大不小的打击,以公孙策的个性,他虽然不放在心上,也不代表他就不介意。再加上,他明明就不输给任何人。这样离开,到底意难平。
展昭看看各人脸色,于是岔开话题:“老包,朝上怎么了?”
包拯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口粗气,从怀里掏出一封公函,一块金箭令牌:“我是今科主考官。”摆出一个难看的苦笑。
那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病树前头万木春啊。倒霉人遇着倒霉事,包拯的脸色可不得就跟中了毒似的么。
原本今科主考一早已经定了礼部尚书,谁知道这些天手忙脚乱的,把个老头累病了,如今卧床不起,再让他当主考好像有虐待老弱之嫌,恐怕不用等考试过去就要办白事了。于是赵祯临时急召,要遴选新考官。
“来吧来吧,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各位爱卿就赶紧的吧。”
此言一出,底下一片“李大人合适,我推举李大人。”“不敢不敢,还是刘大人才高八斗,最合适。”“要这么说的,林大人是翰林更合适。”“还是蓝大人合适。”以此类推,直到每个人都被提名了一次。文武百官果然非常友爱,这叫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赵祯摇头,心说,我早知道你们这群人,就是吃饱了饭不想干活。还好我已有妙计。你们有张良计,朕有过墙梯。
“我朝人才辈出,朕很欣慰啊。所以朕早就知道会出现这样礼让谦逊的场面,早有准备。”说完挥挥手,一旁林公公捧了个大木盒子站了出来。赵祯点头示意,“来,抓阄吧。”
“太儿戏了吧。”有人出声,其他人颔首附和。
赵祯微笑着摆摆手:“不儿戏不儿戏。治乱世不拘礼法么。”
朝上众臣心说这是哪门子的乱世……别说乱世了,治世也没见你拘礼法,乱世那还了得了。
……没的说,只能排着队一个个伸手进去掏,心中祈祷千万别抓着我,回去就给菩萨进贡。包拯百无聊赖地插在队伍中央,做主考他没兴趣,这活又累(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得管)又不得好(没高中的考生还会在背后唾骂你),以前还能收几个门生,现在赵祯圣旨一出,全成了天子门生,他尽收囊中,而主考是半点没落下。所以没人想干,一般是派给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子。一来人老了就没心气了,二来本着敬老的原则也不会有人过分难为他们。比方说有事的时候,只要来句“你看看我这一把年纪了,你好意思来麻烦我么。要是我就这么累死了,我找谁说理去?又有谁来替我照顾我家那群妻妾子女老老小小,巴拉巴拉……”于是就以太极之势化去种种麻烦。
朝中老臣一年少过一年,今年仅剩礼部尚书和庞太师了。其实朝廷里唯一想干这事的大概就是庞太师了,但是赵祯总是很无意地把他漏了过去。尚书大人一倒下,庞籍立刻站了出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赵祯选择了抓阄。
队伍过半,终于轮到包拯了。包拯撩着袖子伸手在木盒里搅了搅,捻了一张出来。皱皱一团纸片,刚一展开,包拯就愣了。“娘喂。”他无声地呼喊了句。忽然间,飞光片羽,沧海桑田。一片白云载着他延着长江,度过都江堰,青山城。他要去塞外,牧马放羊,还要养一群骆驼,每天举着细细的皮鞭抽打在它们身上。
这是阴谋!这是欺天骗世之大阴谋!
林公公接过纸片,嘴里说:“包大人。恭喜你。”眼睛里在说:包大人,多多保重。
抬头看看赵祯眉开眼笑跟只狐狸似的,满朝文武由衷地对着他道贺,三呼佛号。这里就像一个劫后余生的庆典,每个人都在欢唱,大家都那么高兴。只是……只是他包拯怎么那么想哭呢。
公孙策拍拍包拯的肩,道:“别难过。我们会帮你的。”
“再说吧。”包拯挥挥手,落寞地离开。他的背影忽然变得像一只大漠里孤单的骆驼,随着响铃迈动步伐,不紧不慢,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是踩着脚下柔软的沙地,让风来带领着他走向四面八方的黄沙万里。
羌笛何需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展昭心里一凛,挥手拍掉萦绕在头顶的诗句。
“我去巡街了。”展昭放下筷子提剑起身。脚刚迈过门槛,就听白玉堂在后面口齿不清地喊:“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一回头,就见白玉堂塞了一嘴的油条抽打自己的胸口。
“去什么去。你不去就太平了。你这不平白增加我工作量么。”
“切,德性。我就爱跟着,你管得着我么。”白玉堂麻利地抹嘴,叫,“老李,收拾收拾吧。”
“哎,来了。”老李矮小的身子不知从哪里蹿了出来,开始收碗抹桌子。
展昭看他一眼,心中大为快慰,他也终于感受到当大爷的感觉了。
两个人走到门口,展昭一阵眼晕,真是出门不利,他好像看到在石狮子上趴着个人。
“你怎么了?”他上前摸摸脉门,没死。于是把人翻了过来。一张苍白的中年脸留这两撇山羊胡子,长相非常和谐有礼,绝对不站在群众百姓的对立面,换句话也就是说丢人堆里绝对找不见。
“哟。”白玉堂一挑眉毛,有点惊讶。
“你朋友?”展昭也惊讶,白老鼠真是相交满天下,群居动物。
“你朋友!”白玉堂顶了一句,“是五里坡上的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