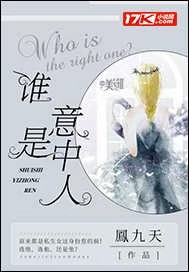祁父看她一眼,有些动摇了,他禁不住问道:“你真的醒悟了?”
“……”
都用上醒悟这个词了,说明她以前是真的不可饶恕。
祁优悠点点头,又说了一通,就差伸出三指发誓。
本来今天那通电话,祁父就有些信她,这会儿又听她的一番说辞,心里更信了几分。
他一时有种欣慰的热泪盈眶的感觉,他举起一旁的酒杯,里面斟了红酒,他对着祁优悠,语气颇为的感慨,“浪子回头金不换,回头是岸,来,干一杯。”
“……”
祁优悠看着一旁的酒杯,举也不是,不举也不是。
“她回头,爸你怕不是又被她骗了。”
祁父还没喝下那口酒,门口忽然响起一道响亮的声音,满含讥讽。
祁优悠把目光投过去,一道婀娜的身影缓缓走近,俏丽的面容也渐渐露出。
是祁钥盈,她的妹妹。
上辈子她总是和她作对,再加上廖慕思的挑唆,这个妹妹什么都要和她抢。
但有了上辈子的经历,祁优悠对她,倒没什么恨,反而多出几分同情。
不过现在对方还是讨厌极了她。
“薄大哥那么好她都看不上,简直就是不识好歹。”祁钥盈在一旁坐下,看向祁优悠的眼神,带三分讥讽,四分不屑,“整天抛头露面的,真是丢尽我们祁家的脸。”
要是上辈子,因为陈明的事,此时的她对这话一定无法反驳,但这辈子,她对这样的说辞多少有点反感,不想忍,也不用忍。
“妹妹说的哪里的话,我怎么就丢祁家的脸了?我进娱乐圈,自己挣钱,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和你有什么关系吗?再说,抛头露面怎么了,你想抛头露面人家还不给你这个机会呢。”
“你!”
祁钥盈站起来,指着她,美眸怒瞪。
“我什么我。”祁优悠不甘示弱,继续说,“我有说错吗?妹妹。”
她一叫这两个字,祁钥盈就觉得瘆得慌,她天生反感,又拿她无法,一时气愤,甩手离席。
她阴阳怪气的来,怒气腾腾的走。
祁父看得也有些气,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扔,“你们两个是要气死我!”
关她什么事?
祁优悠不禁皱眉,她没怼回去,还是出言安慰了几句。
可祁父仍旧冷着脸,一脸的你别跟我说你和她一眼都不是什么好货。
看得让人不自觉就生气,她也没待多久,吃了几嘴就以家里有事为借口离开了。
一场好好的晚餐就这么不欢而散。
祁父看着餐桌,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
祁优悠走出门去,在马路边乱转悠,她心情不好,但也知道,要想挽回祁父对她的印象不能图一时之快,得慢慢来,从长计议。
但面对这样的指责,就是有些委屈。
祁优悠走的有些累,找了个地方蹲下,她打开手机看了眼,已经晚上八点了,她思绪又飘回家中,想到这个时候薄季同差不多应该在吃她做的饭。
鬼使神差的,她拨过去他的号码。
“喂?”
只响了一声就没接通,祁优悠本来没有想打的意思,刚想挂掉,但听见对方轻柔的嗓音,忽然又没了挂掉的念头。
她抱着手机,不说话。
“祁优悠?”
电话那端,薄季同应该是又看了眼来电显示,有些狐疑地出声。
听见他叫自己的名字,祁优悠忽然觉得有些破防,好像她在心房铸造的所有防备在一瞬间被击溃,她缓了缓,忍住哽咽的冲动,轻轻嗯了声。
薄季同觉得她有些奇怪,他声音放得低,又轻又温柔,“有谁欺负你了吗?”
轻柔的嗓音透过听筒传出,夜晚的风有些凉,声音混杂在风里传入耳。
她额前有碎发在风中胡乱的飞,祁优悠握着手机,眼圈有些红,她半推半就带着撒娇的意味哽咽起来,“薄季同。”
“嗯。”
“我走不动了,你来接我。”
这情意,半分真,半分假。
薄季同有些惊讶她对自己撒娇,同时又觉得心疼,于是便问,“你在哪儿?”
“在我家。”祁优悠答。
他赶来的时候,祁优悠蹲在路边,手里握着一根不知道哪里找到的草,在地上写写画画,小小的一只,蹲在地上,摇头晃脑的。
薄季同觉得心头有一处软了下去,好像被什么给触到一般,软成一滩。
他真是中了毒了。
薄季同走过去,一把将她抱起,“回家了。”
祁优悠本来还要挣扎,但扭头看见是薄季同的脸,又安静下来,她双手圈住他的脖子,脑袋乖巧地贴在他胸膛。
很乖很乖的点点头,“嗯。”
薄季同笑了下,抬脚往车里走。
他真是中了毒,再也戒不掉。
路上,祁优悠一直往薄季同身上靠,薄季同顾忌到前面有人,便推了推她,低声道:“坐好。”
“我不。”祁优悠摇摇头,要往他怀里钻,“我就要躺着。”
薄季同拿她没法,最后还是妥协了,他往车门那边靠了靠,敞开怀抱让她躺。
祁优悠露出得逞的笑,她握住他的手放在脸侧,侧过头亲了亲。
“薄季同。”她说,“你真好。”
薄季同微怔。
她又说,“你是对我最重要最重要的人了。”
薄季同回过神,很轻很轻地嗯了声,又捏了捏她的脸,动作轻柔。
他唇角上扬,微微笑了。
助理兼司机房岩透过后视镜看见老板这一笑,不由咋舌,果真是老板娘厉害,他跟这么久,还真没见过几次老板笑。
唯一的那么几次,都是有关祁优悠的。
连好几百亿的项目谈成他都没见过老板这么笑。
此时此刻,不由再叹一句。
老板娘威武。
路程有些远,也许是房岩车开得平稳,又或许是忙了一天她真的有些累了,不知不觉中祁优悠就躺在薄季同怀里睡着了。
等到了目的地,薄季同不忍心叫醒她,就把人抱进屋里,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后,他才离开,去浴室洗了个澡。
祁优悠在床上躺着,眉头却越皱越紧。
她又梦见了,许多的血,从她身下渗出,是廖慕思在放声嘲笑,她说,你真失败,连你的孩子都保不住。
祁优悠,你就是个笨蛋,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蛇,好多的蛇,五颜六色,冰凉的触感让她头皮发麻。
“薄季同……”
“薄季同……”
她抓的被褥发皱,眉头紧锁。
薄季同从浴室走出来,就听见她一直在叫他的名字,他走过去,却看见祁优悠额头出了一层薄薄的汗。
他握着她手心,感受到汗意,薄季同也皱了眉,他小心擦拭掉她额角的汗,然后在她身侧躺下,抱住她。
轻声说,“我在。”
“薄季同。”她又唤他。
“嗯,我在。”
祁优悠没喊一声,他都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