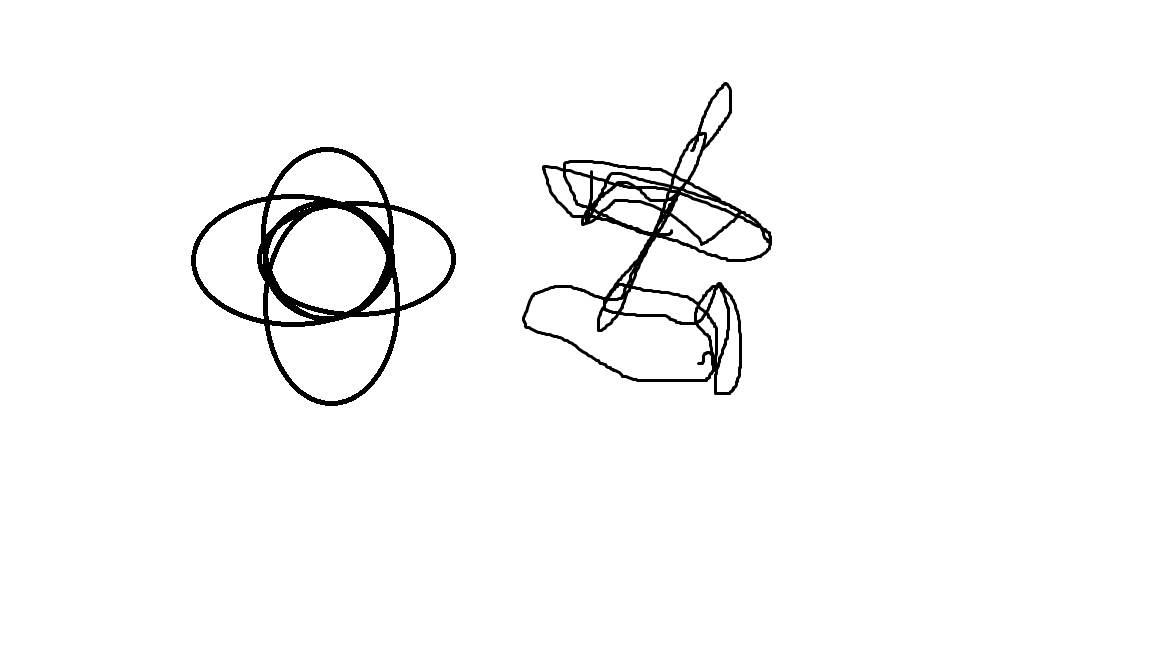那些空气中飞旋的细细碎碎的尘土,在烛光的掩映下,变成与光同质的生物,这个世界虚像丛生,似乎连原本冰冷的东西,都能够靠着一些光亮伪装成温暖的样子,可谁都知道它原本是怎样的。
把白梓轩扶至床上躺好,刚要离开,却被他从后面拉上了衣袖,感受到那股力道,我恍然回过头去,看到他脸上满是无奈的苦笑。
“你曾经说过,在你心中,白梓轩是位‘有将帅之才的王者’,可你知道我每每想起这句话,都觉得多么可笑吗……”
那时我还不知碧落变故,只道他是酒后发泄,于是回身对他道:“殿下此话何意?”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手仍然拉着我的衣袖不放,我转个身,让自己面向他。当他告诉我,就在明日,他便要前往那遥远的北疆之时,我才稍稍动容,没有料到,那道清相国,竟然连自己的女婿都狠心舍弃。不过想来,朝堂之上拥护六皇子者虽多,但更多却是畏惧相国权威之辈。如此看来,这应是白梓轩命定的劫数,难怪他如此颓然,十年磨一剑,在紧要关头,却遭遇这样当头一棒。
“这尘世一切,均属虚无的梦境罢了。”他对着虚空叹口气,“慕容雪时,直到今天你仍认为我有帝王之才吗?在我看来,自己不过是刀俎之肉而已。”
“是这样吗……”我接过他的话,眼睫低垂。“昀端呢,我家师父昀端如何肯冷眼看着殿下如此这般?”
“昀端师父只说,顺其自然。”他道。
“那便是了。”我微微露出笑意,“既然师父都这样说了,那么便无事。”
白梓轩对于我的话先是不解,后来眼神却冰冷下来。
“连你都在嘲弄我吗……”
我轻轻坐到他身边,没有回应他的话,而是这样道:“你知道吗。北方雪国的高山之上,生有雪莲,每10年才有一次花期,若它能经得起风雪的考验,便会开出洁白美丽之花,那花朵绽放之时的香气可以拯救一个垂死之人,可仔细想来,有哪个人会恰好在它的花期遇见它的盛放?现实中,若一人垂死,定不会寄希望于一朵十年才开的花,而若真有人有幸遇见它的盛放,那个人又如何恰好需要它的拯救?或许那是一个健康之人,可你能说,他遇见那朵花,留下的只能是虚无吗?”
那两年里我读了很多书,自信已经比鸳鸯懂得了更多的词,也自信能将想要表达的东西说得很文艺,我说完这些,看到白梓轩陷在绵远的沉默里。我想他是个聪明的人,应该知道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造物之神并不会给我们存在的意义,也不会在创造我们的同时便创造好一个答案,那样一个绝对而真实的答案是不存在的,可我们能因为知道这点便不去追寻吗?”我的语调平稳。
“人一直在追逐一个绝对的答案,可那答案归根到底是虚空的,那么,殿下,你还要去追逐吗?”
“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一些想不明白之事如此费神,如果殿下只是想知道一个答案,那么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经历的不不是虚妄的梦境,你仍需要往前走,你只需相信雪时现在说的这些就够了。”
窗外的风拍打着窗子,那纸窗终于被推开,夜风夹着不知什么花的味道拥入房内。馨香无比。——开在雪地里的花。
白梓轩的眼神寂落下来,等到他恢复往常的神色时,我听到他用低沉和缓的语调命令:“慕容雪时,为我再唱一遍那日的曲子吧。”
我稍稍一惊,心上浮现出困他在床上那日的情景,那首曲子让他那般狼狈,他为何还……不等我想明白,他已继续命令。
“唱。”
我沉默片刻,终于听到从自己的喉间发出这样的声音:“好。”
静静坐到白梓轩身边的床沿上,他突然伸手将我的手握上,轻柔地摩挲,我皱了皱眉,却没有反抗。当我知道他快离开我之后,我觉得就算他要轻薄于我,也是最后一次了,既然是最后一次,那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原野之花,请告诉悲怜之子,人为何彼此伤害。
“寂静之花,请告诉堕落之魂,汝从彼方,曾看到何物。
“雨过夏移,天青云淡,面对常世如花一般摇曳之人,汝不发一语,直至枯萎逝去。
“汝有何思,为何赋于无言?无言之夜,为何手中之火不熄,风亦不住?
“莫非是为证明曾经活过,吾此时放声歌唱……”
没有琵琶的伴奏,这首歌的调子更显苍凉,我唱了好几遍,直到嗓子干涩地痛起来,身边的男子一直安静地听着,表情寂寞却冷淡。
“那把琵琶名唤春音,其主名唤伊沫,伊沫是清和太守之女,而我的母妃则是清和守最小的妹妹。父皇巡游经过清河郡时,强行临幸我的母妃,母妃因此含恨入宫,却一直未获册封,生下我之后,更是遭遇父皇的冷落遗弃……母妃不惧孤寂,却念我寂寞,含泪求其兄送那与我年差一年的爱女伊沫入宫,我的童年,便因为伊沫的陪伴而稍稍添上了少许色彩。竹马之情,两小无猜,大概便是如此吧……”白梓轩说着,捏紧我的左手,眼睛里烛光摇曳。
“我一直视伊沫为妹,谁料她却对我情深。年少不识情爱之事的我,便应允下她的感情,并许给她生生世世永不相离的誓言……”
他讲到这里时,我的眼前似乎升起朦胧的雨雾,世界是鹅黄色,一片暖意。
“可谁料,父皇竟将道清相国的小女儿许为我的正妃,我虽抗拒愤恨,却终不敌那君主的一句轻言……”
“于是,你便娶了华妃吗?”我答。难怪……
“那是盛大的婚礼,我这一生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红色,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这喜庆之色,可是心却潮湿冰冷……那日我喝了酒,很多很多的酒,因为只有借助酒力,我才能与那华妃行夫妻之礼,你知道吗,我多么痛恨那个女人……”
“伊沫是如何死的?”我问。
往昔之事像是褪色的纸张,无论怎样的语言,都不能有更加丰富的再现,我只能从白梓轩的脸上寻到一些早被岁月掩埋掉的蛛丝马迹。
“对于我奉旨娶妻,伊沫并不怨恨,因她独爱梅花,我便为她在府里建了这倚梅阁,将她安置在此,她每日在这里弹琴唱歌,不作他求……可恨那华妃生了一张纯良无害的脸,我竟然信了她伪装出来的温柔,伊沫身子弱,常需要参汤来补,没有料到,华妃竟然在送来的参汤里,下了那无解的毒……”
“天下最毒的,便是弃妇之心。” 我应道。“殿下,你对不起的人,岂止伊沫一个……若你不爱华妃,便不该娶她,若爱伊沫,便不该让她和华妃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你应该了解女人的妒火,燃烧起来会是怎样一种足以侵吞世界的东西。”我想我真的长大了,懂了很多道理,这些道理就连白梓轩都不懂,可是也许他只是不想懂罢了,他比我聪明的多,不然后来也做不了帝王。
对于我的话,白梓轩以沉默回应,过了良久,他才幽幽道:
“知道那日我在你的歌声里看到什么了吗?”他突然问。我安静地摇头,然后听他缓缓说:
“我看到了一落千丈之雪,千只飞鸟的黑色影子破碎在苍凉的大地上……雪时,我承认在那个瞬间,自己的心从来没有那般平静过,这就是我明知那是一个咒缚,却不愿意从那个幻境中出去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