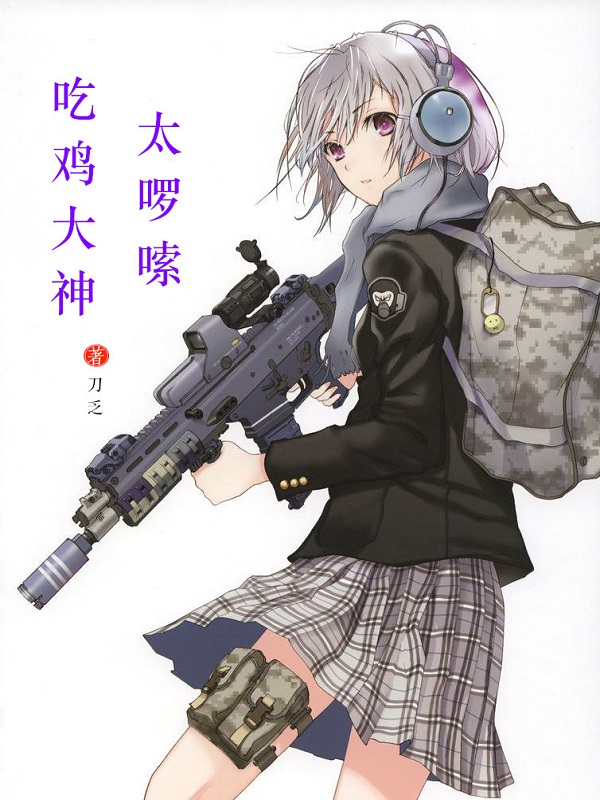我心想,他既然早已知道这件事,又为什么偏生过来问我要不要同他在一起,这着实让我有一些纠结。
我在许久之前就曾经思考过,若是我们二人当真有缘分,那么无论中间发生什么,最后一定是会在一起的,与他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既然从结果上来说,我们没能在一起,那便只说明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没有缘分,缘分这东西很玄乎,是强求不来的。
它该来的时候就会来,它不该来的时候,便是连个影子也看不到。
当我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白梓轩之后,他忽然将手撑在额上,然后自喉间发出低沉而含糊的笑声,是苦涩无比的笑。
他说:“也许是我真的太了解你,所以对于你说出这样的话,我一点也不惊讶。我也知道你向来都爱自己拿主意,而且拿定的主意从来不会轻易改变……只不过,雪时,我想问问你,你真的确定自己想要什么吗?”
他说完,缓缓抬起头,眼眸中映出我仓皇的表情,正在我含糊间,他忽然将我拥入怀中,下巴抵在我的头顶,声音疲惫而沙哑,低沉而醇厚,“雪时,你确定你不想要我吗?如果你确定不想要,又为何这么痛苦?”
我承认,自己为他的这番话而恍惚了起来,他说的很对,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左右摇摆,或左或右,总有个确定的归属,从来不会有中间选项,世事大抵如此,就是因为看的清晰,我这个人才很少会有矛盾的时候,自小便是。
然而,在白梓轩和南云之间,我却少有的矛盾起来——这让我很痛苦。
“白梓轩,我已是南云的妻子,我一定是爱着他的,所以,我的心里不能再有任何人,就算是你,也不能……”我无措地解释,我逼迫自己拼命地回想,回想我与南云一起生活的时日,也拼命地调动起身体里潜伏的对南云的所有感觉,当我确定我是爱着他时,我才终于安下心来——看吧,当我想着南云时,我确定自己爱他,这就足够了。
“雪时,你真的确定,自己对那个男人的感情,是属于你自己的感情吗?”白梓轩的这一句话,却犹如响在雾中的钟声,使得我的身体猛然间为之一震,一时间,竟像是浑身上下被什么东西浇的透彻,冷到透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颤抖着声音,手下意识地抓紧身下的床单,骨节处因为使力而有一些泛白。“那自然是我的……”
话没有说完,心里却不可抑制地动摇起来。
如果那感觉确定无疑是我的,那么,现在的我究竟又是在害怕什么?我隐约回忆起,似乎自许久之前开始,我便时常做着一个模糊的梦,在梦里,我同他是相亲相爱的,可是,我却清晰的知道,梦里的我,其实并不是我。
我开始惊慌了,如果我不是我,那么我的感情,又是谁的?
那个深深爱着南云的女子,究竟是谁?
“雪时,有些事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想知道,你是这么聪慧的女子,又熟读各种典籍,又怎会不知那些尘封的真相?当年自樱暖门坠楼的那位帝姬,她既是白帝唯一的宠妃……却,也是炎君的爱人。”白梓轩的声音仿佛带着毒药,使得我浑身瘫软,我无力地伏在他胸前,觉得就连呼吸都有一些难过。
大脑一片空白,却渐渐在那片空白里,喧嚣出了漫无边际的念头。
“雪时,你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点,你不过是在逃避罢了。”白梓轩的声音冷冰冰的,就像是一把刀,结结实实地扎在我的胸口,直到最后,他都这么残忍,就像是初次见到他那天一般。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继续用冷淡的语调,对我说出那些我多年以来一直刻意回避的“秘密”。
“那位帝姬的名字,唤作慕容锦离。在初代白帝在世的年份里,慕容家始终是相门,几代荣宠,直至你祖父的那一代,才因你祖父痴迷某个江南歌女而逐渐没落下去,就是因着慕容家的没落,才有了后来道清相国的权势……
“到了你父亲这一辈,慕容家的浮华才总算如幻梦一般破灭,可是,慕容家的生意能做到全国各地,也不全是得益于你父亲的商业才能——没有往昔权势的余荫,又怎能如此风生水起?
“雪时,虽然在民间,炎君的传闻有许多个版本,可是在皇家典籍中所载的炎君,却是个可以役使狐妖的男人,狐妖自古便是‘诱惑’的代名词……这样一个男人,难道不是想要在你身上得到什么吗?”
白梓轩不愧是最得先帝赏识的儿子,说起事情来,当真是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有逻而有辑,想必这样一个人,若是治起国来,一定会比现今御座上的那位,要精明干练许多。
可惜,真的好可惜……
正在叹息,只觉得横放在我腰际上的那只手,力道又大了一些,白梓轩似乎是要将我整个人揉进他的身体里,他的衣服上仍然有好闻的熏香味道,只不过这些年,我早习惯了另外一种香,虽然淡漠而飘渺,甚至有一些虚无,我却仿佛是中了毒,上了瘾,没办法让自己习惯上别的味道。
“雪时,回到我身边……我知道,那天是你救了我,我虽然昏迷着,可是你在那里,我是知道的。”
这个男人,几乎是在哀求我了。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好,而他又究竟是看上了我哪一点,我心想,大概是得不到的总是最完美的吧。
“好啊。”我凉凉地开口,只觉得他身躯一震,竟是不敢相信。
“雪时,你说什么?”他蓦地放开我,望着我的眼睛里,有巨大的喜悦,却也有更多的不安。
“我说好啊。”我紧紧闭了一下眼睛,然后缓缓睁开,我听到自己机械地对他说,“但是,你要答应我,永远不要去争那个皇位。”
他沉默下来,我与他对视良久,看到他眼里的挣扎,如同互相争斗互相追逐的两道光,最后,他握住我肩膀的手缓缓地、无力地垂下。
我只觉得一种无力感从头到脚侵袭我,将我变成空荡荡的躯壳,那棵生长在最柔软的角落里的种子,再也不会发芽了。
良久,我扯出一个荒芜的笑:“看吧,你要的,其实也并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