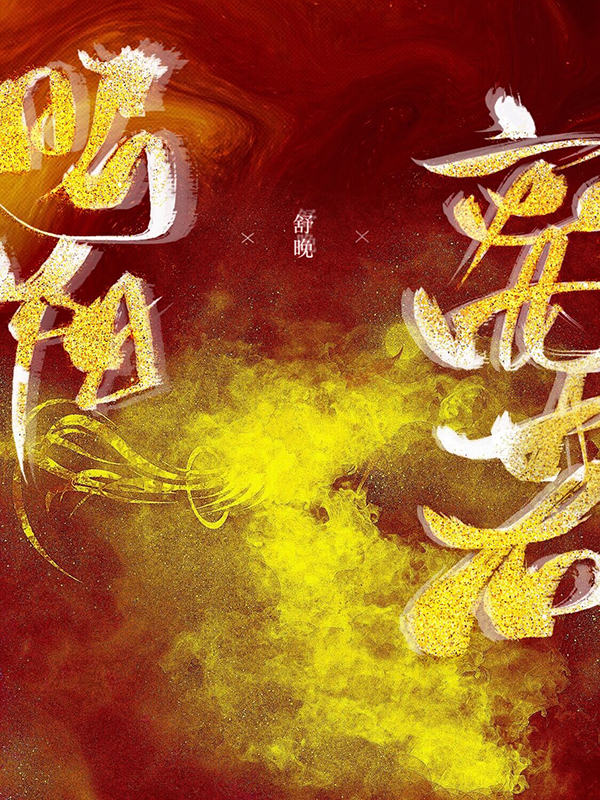那个白衣公子称我为慕容锦离。
我隐约觉得这个名字我似乎在哪里听过。至少慕容这个姓我应该很熟悉,我估摸着若是顺着这个线索去想,我应该能够记起更多,可奇怪的是,在我觉得终于要接近某个答案的时候,却又忽然被某种力量拽回,连方才的所思所想都重新归于虚无,这让我有些烦乱。
我自小便是个不将事情想明白便不会罢休的姑娘,若是某件事想不明白,我便会很痛苦,此时的我便是处于这种痛苦状态。所以为了缓解这种痛苦,我找到了一种类似于精神胜利的办法——将所有的事情归结为前世今生。
我想,这个慕容锦离大概是我的前世,而我现在之所以会在这个躯壳里,则是因为我的前世还有什么未竟的心愿——这个心愿需要我去完成。
所以我才假借了梦境,来到了过往的某一个时点。
这样想开之后,我就舒服很多,我隐约记得有人这样教导过我:既来之,则安之。
于是我安稳地跟在抱了一只白狐的白衣公子身后,开始盘算如何翻他的家底。
“你说我叫慕容锦离,那你叫什么?”我没有想好更好的主意,就只好假装失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真实状态。
他听完我的话之后颇为孤疑地看我一眼,眼梢微微挑着,我承认,这个人生了副祸水的模样,又清雅又淡漠,又难画又难描,我以女子的眼光来看,觉得大抵这世上的多数女子,都会为这张脸神魂颠倒。
他淡淡地这般开口道:“你是打算这样玩到底吗?”那口气明显不相信我是真的不认识他。
我心想,难道这个慕容锦离的脸上,天生写着“我不可信”这几个大字吗?
想到这里,我有些郁闷,遂闭了嘴,脚却紧紧地跟着他。通过孜孜不倦地东张西望,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偌大的花园,草木很深,想来整个宅邸应该是很大的,而这个白衣公子,想必来头也不会简单——看他身上的锦绣华服,应该是世家子弟。
正在沉思,就听到他在头顶对我说了两个字:“倾月。”
“……倾月?”我对于他突然说出这两个字而一头雾水,遂重复了一遍。
他的脸上立刻挂上“笨蛋”两字,然后颇为无奈地、额外赠送一般地,又加了两个字:“名字。”
此人说话当真是越来越简洁了。
“哦……”我做出恍然的模样,“原来你的名字叫做倾月。”
说出这句话时,脑海中却忽然涌上许多画面,那些画面光怪陆离,杂乱无章,每一个场景里却都有同一个人出现,他的面如凉月,他的声如夜华。
倾月,倾月……
“别的名字可以忘记,唯独这个名字,不要忘掉。”这是谁的记忆?
“锦离,如果是我的话,你愿意随我走吗?”这又是谁的声音?
“我未曾讨厌过你,从来都不曾。”是谁……
“就算他负了你,你也要同他在一起吗?”
不知道冥冥之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既模糊了年月,也模糊了梦景。
我还陷在纠结的印象中,就被那些因我们的脚步声而惊飞的鸟儿唤回了清明里,耳边是呢喃的风声,而我们正在捱过雕栏,转过秋千,最终在一个古旧却雅致的房间前停下了脚步。
随着倾月“吱呀”一声推开门,他怀中的白狐突然一蹬腿,轻盈地落地,然后优雅地回过头,拿诡异的墨绿色眼睛盯了我一眼,动作轻巧地朝回廊的那一头跑去了,不一会儿就不见了那个白色身影。
“愣着做什么,进屋。”倾月一把按上我的头,将我带进房间。
我叫了一声痛,然后没好气地瞪他一眼,他却极为淡定地绕到房间中央的桌旁,抬袖倒了两杯茶,我估摸着那两杯茶里有一杯是我的,遂走到桌旁坐了,托着腮望着他,开口道:“你好像不大待见我……”又问,“为什么?”
“你为什么觉得我不待见你?”他挑起眉毛,仍然站着身子,将一杯茶推到我面前,我看到他的衣袖上,用银线隐约绣几朵我分辨不出品种的花,很是别致,而衣袖之下露出一截手腕,手腕上系一根红色稠线,串着一粒碧色的珠子。
“都说女人的直觉很准,我的直觉告诉我,你好似不大待见我。”我自发现它开始便一直盯着那粒珠子看,看到它通身剔透,莹润无比,似乎有种摄人心魄的力量,盯得久了,不由得有些痴缠,可倾月的手略微一动,那枚珠子便隐在了衣袖下面。
“你也算作女人吗?”他轻飘飘这么来了一句,语气里似乎有轻蔑的味道。
我隐隐觉得自己的额上似乎裂开了那么一条缝,也隐隐觉得同此人的交流有些无法克服的障碍。
我自然算作女人的,虽然不能夸口说什么面似芙蓉、眉如新月,却也是裙带飘飘,此人若非眼神有问题,便是颅骨内的那玩意儿有问题。可是,鉴于我向来是个有教养的姑娘,再加上对目前状况搞不太明白,我大方地决定不与他多做计较。
压下心里的火气,我强装淡定地道:“你会瞧不起我,自然有瞧不起我的理由,我也不能强迫你一夕之间便改了主意……”说着拿起手边的茶杯,贴到唇边呷了一口。
那茶入口微凉,顿时觉得火气又去了几分,我正了正身子,这般道:“不过,我向来是个不愿意与人交恶的人,所以以往发生的一切,我希望可以就此一笔勾销。我们只当是今日才刚刚认识,你觉得这样如何?”
对于我来说,我们本来就是刚刚认识,这样甚好。
他对我的提案却不置可否。只见他缓步绕到我身边站好,抬起一只手放到我的额上。他手上的凉意贴着我的额头,我觉得很是舒服。
可是他竟然靠我这样近,近到我可以闻到他身上好闻的木槿花的味道,我不由都得因此而屏住了呼吸,心脏跳动的很厉害。
“你……”我张了张口。
“……你今日,似乎有些奇怪。”他这般道,“难道还在发烧吗?”
我的脸确实因为他的靠近而涌上了阵阵热度,而他似乎也终于因此而判定我确实还病着,便不由分说地扬声叫人,命几个丫鬟伺候我去里面的房间休息。
“我真的没有病……”我张口想辩驳,他的一双大手却压上我的头。
我定定看着他的漆黑而深邃的眸子,看到里面是一层温柔的光影,他说:“锦离,听话。”又道,“你也不想你亦柯哥哥回来之后见到你憔悴的样子吧。真的很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