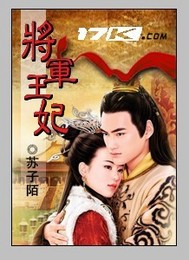陈应的指尖很凉。
轻轻触及玄羽的脸颊,把那面具从玄羽的脸上摘下。
指尖似乎有些颤抖。
陈应笑了笑。
“师父。”手指轻轻的滑过玄羽的脸颊,那层搞笑的,为了遮掩他本来面目的胭脂和污泥还没有洗去,只是因为那天玄羽回头,一头便栽倒在那里。
妫芷说,先别动他了。
可是妫芷,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冯英抓住的人真的是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萧琪伤了的人也是他?为什么不阻止他去金铃寺救我?为什么不告诉他他的责任是倾覆这天下?
“师父,你是逗我玩的,是么?”
陈应拿起手绢,细细擦去玄羽脸上的伪装。
胭脂和污泥的混合一点点的剥离开来,陈应的手指却停在了玄羽的耳畔。
师父,你的耳朵……
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
“师父,你还记着您和我说过的第一句话么?你告诉我,让我收拾收拾,带我回楚宫。然后我就看到你和妫芷坐在树上。也是那一刻起,我才觉得,能够站在巅峰,俯视他人的姿态,该有多么的完美。”
陈应细细说着,也不管玄羽是否听得到。
眼神忽而遥远了起来。
是啊,若非他带自己回楚宫,自己怎么看亲眼目睹到父王的昏庸,婉贵妃的狠辣。
自己,又怎么会生出与萧琪一决天下的心?
“师父,你还记着你和我说过的话么?”
陈应顿着的手指僵了僵,又游离在玄羽的额迹,轻轻笑了。
“你和我说,江山如梦,梦里江山。”
陈应俯下身,细细端详着玄羽露出来的容貌。
是江湖人士少见的白净,只是除了那白净,还有着一丝文雅,一丝清凉。如同雪山白莲,可远观,不可亵玩。陈应忽然想起一个模糊的梦,那梦里有一袭雅如白莲的背影,看不清容貌,只是觉得他在血与火的那端愈行愈远。
陈应笑了。
“师父,一袭白莲,我早该想到是你的。”
陈应撩起耳边的碎发,依旧是笑着,只是那笑,让人看着,便添了几分心酸。
“白莲,那样的高雅清洁,那样的惹人艳羡。我早该知道是你的,只是为何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想起来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呢?”
陈应依旧在擦着玄羽的脸。
那样精致的,却同样霸气的脸。
“师父,你说是不是一开始,就注定我们是这样的结果?”
陈应说着,从怀里掏出那禅房中带回的签,轻轻的放在枕畔,想了想,还是塞在了玄羽的手里,“师父,你看看,这就是那禅房中找出来的东西。桃花楚楚,映暮如晨。说的就是开的极艳极艳的桃花,把晚上映衬的如同早晨一样。可是师父,你也知道桃花是不长命的。断送一生憔悴,也不过是数个黄昏的时间罢了。”
陈应的手指贴近玄羽的领口。
一粒粒的解开衫上的扣子。
门外似乎有声音传来。
陈应耳边只留下昔日玄羽那为数不多的笑,轻笑,低笑,温柔的笑,爽朗的笑。
上衣完全解开了。
也是光洁的如同玉一般的身子,此刻却再也没有初见玄羽时偶尔冒出的迤逦的念头,只知道一点点的擦下去、擦下去。陈应那蒙蒙的眼,无神的盯着窗外,看着那看不见的桃树。
那年,便是在这树下,自己被这个人救下。
自己扶着树回头看过去的时候,这人的脸是红的,不由的让自己想起戏文里那所有的倾国倾城貌、多愁多病身。
再后来……
再后来呢?
他不知去了何处,而自己每晚都会在夜中惊醒。
好似又看见了那个救下自己的男子,白衣若仙的看着自己。
多久了?
多久没有想起过墨离了?
偶尔,陈应也会如此问着自己,可每当看到妫芷那袭飘然的白衣,总是会想到玄羽,那样谪仙的风度,那样狠辣却又温情的男子。
“师父,当初你就不该救下我。”
陈应低笑,仍旧失神的看着那扇遮起来的窗户,想着那颗桃树。
手却触到一块阻拦。
陈应垂首,看到玄羽的腹部和腰间,一块块的都是凝血的疤痕。
师父,你当初就不该救下我。
陈应又是一声叹息。
是啊,本来是堂堂正正,风度翩翩的一个宫主,便是倾覆这天下也不过是几天几个月的事情。却因为救下了自己而分神,如此宠着、让着自己。
浑然忘却了初衷。
师父,你为什么不告诉为了我弄了这一声的疤?这满心的伤?
陈应细细的擦着那些乌黑的血痂,仿佛想要擦去什么。可那些血痂,又能有什么呢?不过是已逝的岁月,和那些不为人知的伤痛罢了。
师父,你总是这么傻。
为什么要让着我?你明明知道我要的也是这天下,可你还是如此的顺着我,由着我。
自己承担了这么多,可从来都不多说一句话。
陈应的手指顿了顿,抛开那手绢。
那一块浓黑的血痂,似乎还是软的,新鲜的。时不时还有浓黑的,搀着不知什么味道的血,流出来。
陈应想了想,伸手取过腰间的短刀。
在心里默念,对不起师父,这里或许就是你听不到声音和晕过去的原因吧,让徒儿来试试,请原谅徒儿的自作主张,等到师父醒了,无论师父如何处罚,徒儿都认了。
挥刀而下。
呛人的味道传了出来。
陈应小心翼翼的挑出那里的腐肉,在里面触到一个硬的、像是箭头的东西。
这是……
陈应想了想,那无神的眼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兴冲冲的跑到门口,冲着外面候着的人叫道,“快去给我叫一个大夫,快,越快越好!宫主他还有救!”
借着门缝,看起来像是朱雀匆匆而去。
陈应忽然又现实了下来,陇西的大夫已经请便了,还有谁敢冒着生命危险前来?不过试试也好,就算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吧。
陈应回眸看向榻上的玄羽。
走过去。
轻轻的捡起面具,压在他的脸上,又抱出一床被子,摊开在他的身上。
忽然想到玄羽曾经对自己说的,“……你这样,就好像看到了十年后的我们……”
终于有两滴眼泪流出,洇湿了那半旧的深蓝的缎面。
如同红颜,转瞬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