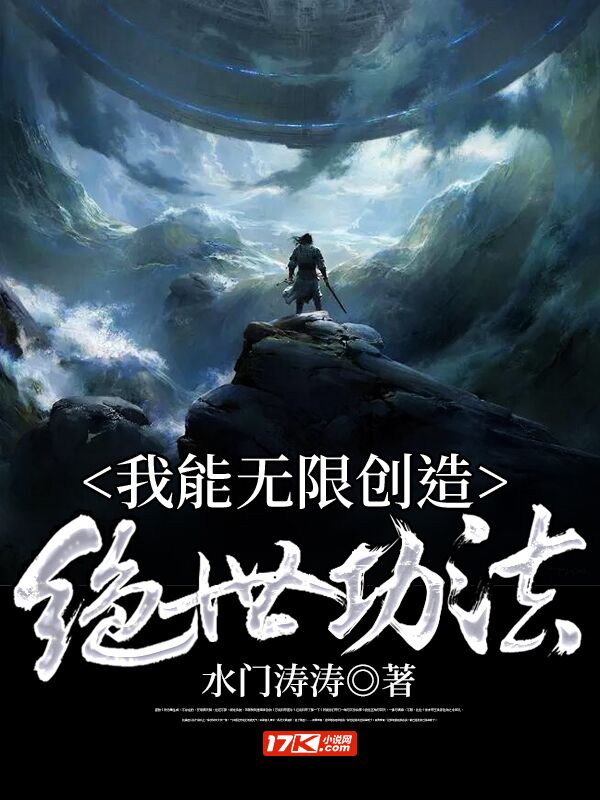他看了看表,快到中午了,索性上街对面的新华书店逛逛,下午再去医院吧。他在书店找到一本密尔的《论自由》,来到一旁的书友吧,要了一杯奶茶,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这当儿,尤俪在他的对面的座椅上坐了下来。
“嗨!”
“你好!你也常来这儿看书?”
“真巧。”
“对了,听说你是学哲学的。我一直有问题想请教。”韩宇说罢,叫服务员过来,尤俪点了一杯刨冰。
“不敢当。哲学嘛,都是虚的,大道理。不是一直流行那一句话吗:知道那么多大道理,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尤俪说着哈哈一笑,韩宇觉得她那带点鼻音的语调很有气场。
“那天吃饭,你说你不相信偶然性,也不信必然性的存在,言下之意,你是属于怀疑派的啰?”
“你或许比我更知道,近代科学和知识论的实质,就是要发现具有内在必然性的规律性,而因果联系一直被看做是一条最基本的自然法则。而依照某种理论,因果关系被看做是一种习惯性的联想,必然性只是一种主观的虚构,那么发现自然规律就不过是一种空话了。万物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一切因果关系,就是一种习惯性的联想。万物皆可怀疑的。 我认为,凡是从理性主义出发,为因果、归纳寻求确定性、必然性的,都注定陷入了困境;而凡是从非理性主义出发的,因果问题、归纳问题则被消解掉。 可见,理性主义对确定性和客观必然性的追求只是一种虚妄的幻想,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哲学问题。客观性真理不再是一种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东西,哲学应该放弃对这些品质的关注 ,从一种外在性入手,着眼于偶然的实践、变化的描述,其结论由于是人类社会实践范围以内的事,因而是可错的、可修改的。总之,科学也只不过是人们与对象打交道的诸多方式中 的一种,我们之所以接受它,只是因为它给我们的生活、行动带来方便,或有利于我们获得 幸福。所以,科学与宗教相似也是一种信仰。”
“你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早就决定了的吗?”
“我不认为,或者说我不知道。有关决定论和非决定论,我都保留意见。所以形而上学的东西,我都无法深究,也不想去深究,我只关心生活本身,真理是为生活服务的。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人真的没有自由意志。这听起来很不爽,可也许这是事实。”
“洗耳恭听。”
“你的想法并非由你一手创造,许多人相信,人类的自由表现为一种能力:我们能根据自己的思考,去做那些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这通常是指,我们可以克制暂时的欲望,从而追求自己的长期目标,或者做出更好的选择。的确,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拥有这项能力,而动物却做不到这一点。然而人类大脑所具有的这项能力仍然是根源于无意识之中。有时候,你只是自愿,并非自由,你还是被决定的,你不可能选择别的决定,这种理论就好像是说,事情本来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但实际上是非如此不可的。不错,我们的选择、努力和意愿以及思考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影响,但它们自身也是因果链条的一部分,这个链条先于意识知觉而存在。我的选择显然非常重要,而且我可以想方设法做出更明智的选择,但我无法选择自己的选择。从表面上看,我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我的选择是两权相较、反复思考的结果,但是我无法选择我自己选择的选择。这是一个可以无限逆推的过程,它的终点永远存在于某个神秘的角落。经常有人会说:要是当初这样做就好了。事实上这是将我们期待的未来和不可撤销的过去混为一谈。
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以及我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仍然是个谜。因此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拥有自由,等同于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件事,但它很对我的胃口,我并不介意这样做。当你准备做出某个决定时,你不妨想想它的现实背景:你无权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家庭,无权挑选自己的出生时间和地点,你的性别以及你大部分的人生经历都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你根本无法插手你的基因结构和大脑发育。你的大脑所作出的任何选择,都是建立在各种偏好和信念之上。这些偏好和信念根源于你的遗传基因和先天的身体发育状况,以及你与各类人物、事件、观点的交互作用。在你的整个人生中,这些偏好和信念被不断地灌输进大脑,因此哪里还有自由可言?当然,尽管如此,你还是可以按照你的意愿行事,但你的意愿又是从何而来?”
“有道理。不过我是一个决定论者。真正相信决定论,你就应该相信一切都只能是它发生的那个样子,因为一切都是早就被决定了的(你深信这世界存在普遍的因果联系);同时,你也相信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因为你并不知道明天会怎样被决定,哪怕你恣意妄为,事后你也会推脱说:这有什么办法呢,不是说一切都是决定了的吗,事情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换句话说,相信决定论既让你无能为力,又在怂恿你任性自我,因此,遭遇并相信决定论是我们这代相信科学的人的一场悲壮的人生际遇,相信它就得承受这个悖论的巨大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