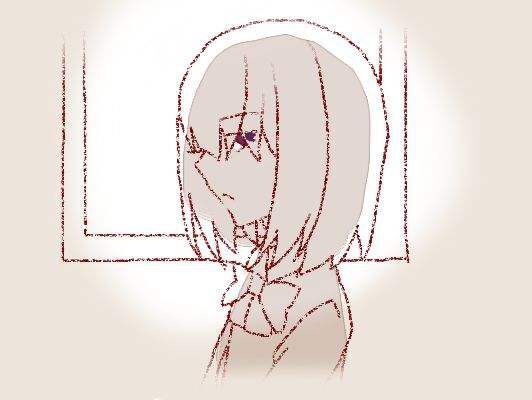这是我离开天界的第二十个年头,萧山的桃花开得漫山遍野。我拿着一壶黄酒,坐在镖局的门槛上,看着一群披麻戴孝的人们在桃花中穿行。
他们或拿着款待客人的食篮,或抱着还未裁剪的白布,其中也有几个穿着粗布衣虎背熊腰的男人和女人,来来回回搬运看上去就很沉的箱子。
今天是天道宗宗主小女儿的入土为安的日子。小姑娘缠绵病榻已经有几个月了,郎中开的比黄连还苦的汤药和仆人小心翼翼地照顾还是没能让她挺过这个春天。
宗主的夫人撕心裂肺、没日没夜的哭了三天,不少人唏嘘感叹,可我却怎么都无法理解,这或许是因为我来自天界的缘故。
天界并非一个没有死亡的地方,只是神族的生命太漫长了,根本是人界几十年能够比拟的。
每当天界有人死去,北方晴朗的天空就会下一场大雪。几万年过去了,北方的积雪便成了一片雪原。两千年来我一个人住在雪原的边缘,直到迷路的司命翻山越岭来到我的面前。
作为一碗水的报酬,他用匕首刺破指尖在白纸上为我算了一卦。但是这是没有结果的一卦,他告诉我说他无法预测出无心之人的命运。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我比起天界的其他人究竟缺少什么。
“喂喂,宗主叫你过去一趟,应该是有新的生意了。”安福忽然从背后拍了拍我。
“知道了。去忙你的吧。”我爽快的回答,将剩下的半壶酒倾倒在土地上,安福顿时露出心疼的神色。
安福究竟有多大年纪了我至今不清楚,不过看上去他和容与的年纪应该不相上下。他算是我的同事,每次有什么下山走镖一类的任务总是他告知我。
而容与是我在萧山脚下捡回来的,刚遇到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从哪来要到哪里去,“容与”这个名字还是我给他起的。
至于为什么要叫“容与”我心里也不清楚。只是从很久以前提到这个名字,我总感觉很熟悉,很难受,仿佛我们曾经一起患难与共,但我真的不记得我认识什么叫容与的人。
我登上长满青苔的石阶,向着半山腰处的观星台走去,宗主,也算是带我入门的师父,总是在那里接受他的“生意”。
观星台四周有一层看不见的结界,无论多强大的内功到达此处也无法发动。这层结界是我不知道的高人所为,并非宗主的力量能够达到。
“允星,这次还得请你去中原走一趟。”师父对我说。他的面容很平静,看来死去一个孩子的痛苦对于他而言尚且可以忍受。
我单膝跪地听候他的差遣。师父的身边还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他身体瘦削佝偻,看上去一副命不久矣的样子,委托师父杀人的钱应该是他毕生的积蓄了。
“你要处理的是当地的一个乡绅的女婿......”
“他夺走你家的田地了,还是强抢你的家的女儿了?”我打断师父,直接向那个老人发问。老人像是被戳中伤口一样,苍老的脸上忽然淌下眼泪来。
“他原本与我女儿有婚约,后来为了攀附权贵,便和乡绅的女儿把我女儿害死了.....”老人越说越激动,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我冷笑一声,道:“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知道了。等着那人的项上人头吧。”言罢从师父的手中接过那张生死状,在桌案上按下了手印。师父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一旁涕泗横流的老人。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第一天来天道宗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是天生的镖客,因为我没有感情。
是,没有感情的人这世上有很多,只是他们大多数曾经都有过感情,为了某个不寻常的目的强迫自己忘记感情,而我天生就没有,我没有心,不懂人间的生离死别,嗔痴怨怒。
我走小路,借着桃花林的掩蔽一人下山,却还是被容与拦了个正着。
“我想和你一起去。”他对我说。
“你和我一起去只会给我添麻烦。”
“也许,我能保护你。”他一字一顿认真地说。
我被他逗笑了,趁他不注意在他肩膀上点了三下,他顿时像个石雕一样定在了原地。
或许我真的应该相信有些人生来就是相克的,容与入门才四年,但在天道宗中并不算拖后腿的存在,只是每次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一招一式之间便方寸大乱。
我绕过定身在原地的他,继续向着山下走去。
萧山地处西北方,山脚下有几个小市镇,都是曾经东西通商时遗留下来的。这些小市镇并不算繁华,集市中交易的物品多是一些蔬菜粮食,不过好在这里作为曾经的商路,不缺少马车和驿站。我在山下要了马车,向着百里之外的中原赶去。
等我到达这单生意所说的镇子时,已经是七天以后了。
在黄土地上拔地而起的镇子古朴宁静,三条南北走向的主街被两条东西走向的小街打断,街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平顶屋。集市刚刚散去,街道中的老槐树下有几只公鸡在啄着地上的掉落的粮食,黄昏中一缕炊烟慢慢升起。
也许我应该为我即将给镇民平静的生活带来一场杀戮而感到抱歉。
我骑上马按照地图寻找那户乡绅的家,但当我找到的时候,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有人已经先我一步执行了我的“任务”。乡绅家的朱红大门敞开着,门口躺着的是一个家丁身首异处的尸体。
一股新鲜又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我跨过他的尸体,向宅邸内走去。一路上到处都是尸体,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孩子的,绫罗绸缎的粗布麻衣的.....这些人死前的表情很平静,像是根本没来得及恐惧就被一击毙命。
天井中,锦鲤池中的绿水已经被血染成了红色。我看见回廊的尽头有一个玄色华服的男子提着一个孩子静静地矗立着,仿佛在等待我。
他回过头,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将孩子抛向天空。
我下意识地发动轻功一跃而起,将那个孩子牢牢地接住。
“你是这家人的仇家?”我冷冷地问。
“不是。”男子用清朗的声音对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这声音像是一把刀一样刺中连我自己也不知晓的心中最难以愈合的伤口,伤口结的痂裂开,流出血来。
“常言道,从来纨绔少伟男。”男子轻笑道,“你瞧这家人,为自己的孙子庆生都这么大的派头,将来烟花柳巷里恐怕又要多一个浪荡公子了。不如让我帮帮他,给他提前创造一个适合成才的环境,让他明白什么叫梅花香自苦寒来。”
“......”
“你呢?想行侠仗义,还是想与我同流合污?”男子问道。
“你自己也知道是与你同流合污。”我不以为意地回答他。“我对两者都没有兴趣。我只对我该得到的赏金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