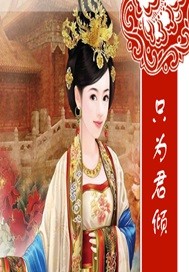夏日已渐渐显示出它的本色,太阳渐渐升上空中,越升越高,带来了光亮也带来了闷热。侯府内,张青不在,张东篱也不在。花爻一个人闷闷的待在房间练习张青昨晚所教内容,汗水也渐渐漫上了额头。
她搁下笔,带着研判的表情看着自己写下的字,嘴角不禁耷拉下来。虽然自小便随着娘亲习着汉话,什么都可,却单单这字是无论如何练不好的。不知是太复杂还是自己心生反抗,总之是气坏了不少先生。
那日张青好笑的看着她随意写下的字,只淡淡说“明日开始我教你写字吧。”
只是想多跟他待在一起,只是想慢慢的让自己与他走得更近,就同小时候一样,为了他那简单的一句话,便敛去脾气,安静的坐着日日侯他回来。
看着自己写在竹简上的字,花爻还是垂头丧气。看来,还是无所进展啊。
窗外,苏恒神色匆匆的沿走廊走过,花爻便轻跑出去。
“苏管家。”
苏恒脚步一顿,停下转过身,恭敬的服了礼,“花爻小姐。”
花爻浅浅的笑笑,“您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小人失礼了。”苏恒欠欠身,抱歉的答道,虽极力掩饰语气却仍透出些许着急。
“不妨,究竟何事?”
“宫里侯爷的亲信来话说侯爷有事耽搁了需晚些时辰再回,但是却又急着要旧房子里的一样东西。小人不知那地,东篱少爷也正在当值,所以,小人不知如何是好。”
“是灵云坡那里么?”
“灵云坡?”苏恒愣了愣。
花爻轻轻笑了笑,点点头“我去吧,我知道那里。是取什么东西回来?”
苏恒张了张嘴,却没有再提问,“宫里的人说侯爷要旧房子里的一柄木剑。”
“木剑?”花爻诧异的看着苏恒,他要木剑做什么?
苏恒慎重的点点头,花爻了然。
出了高大的城门,花爻突然觉得自己像故乡里的雄鹰一般,撒开了手的到处飞翔。似乎自己禁锢了太久了,似乎被幸福的柔纱包裹了太久了呢。
舒心的一笑,花爻走向了那个自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小道,通向了自己多年梦见的小木屋。
心里如同大地一样,被洒下的阳光装得满满的。
原来他每天都会打扫这里,原来他什么都没有忘呢,原来,他,也是眷恋着这里,如同自己一般的。花爻想着想着脸上浮现出诱人的羞涩。
“你那时还那么小,那么聪明美丽……”回想起他由衷的赞美,花爻捧着衣柜的衣物,将头埋了进去,笑得背影也散发着颤抖的喜悦。
他的过去有她,他的现在也有她。花爻慢慢抬起头,憧憬着,未来,他的世界也会有她吧。
花爻在衣柜最里面找到了那柄木剑,整理了下东西,顺手带上了门,离开了这里。
花爻欢快的跳了起来,感觉自己像小时候一样驰骋在草原上,轻轻的哼着娘亲教的歌谣:
“长相思,长相忆。与君别离,相去万里。往事尽飘散,故园如故否。”虽然娘亲从来不对她说这曲子的来处,也尽管这曲子有些悲戚的成分,但因为这是娘亲最喜欢哼唱的歌,所以她理所应当的学会了,不过她自己却将那调子给改了改,理所应当的将它纳为了自己最喜欢的曲子。
她仰头看向了正午的太阳,烈日灼灼照得她的眼睛有些睁不开,微微闭上眼睛,花爻看见不远处有个青衫男子屹立在那里,看不清神色,只觉得,他执着的站在那里,仿佛等待了几百年一样。阳光透过树叶射下的斑驳光点也成了他的背景,华丽而素雅,内敛却孤寂。
花爻好奇的看着他,没有耀眼的阳光的直射,她看清了他的面容,以及那清透的眸子中千年纠缠般的神色。
烈日下的徐风抚摸着他的发丝,衣带,如画的眉毛好看的拧在一起,如墨的眼睛闪动着星辰般温和的光泽,微抿的嘴唇几不可见的颤抖暴露出那人激动的情绪。露在衣袖中的部分手也紧张的握在了一起。
“大叔……大叔?”花爻走进,试探性的唤着他。
那名男子仿佛从梦魇中走出来一般脸色尽显痛苦之色。半晌他才问道:“蝉儿?”
花爻像被雷击中一样,浑身上下无不充满了针芒。
倏忽,那男子眼神渐渐清透,他摇摇头,微微有些苦笑道,“你唱的不错,只是还不够……”男子走上前,轻轻的拍着她的肩膀,“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花爻手不由得握紧了木剑,即使没有杀人的利器,她也能直取敌人性命,眼神不禁冷冽起来,好像身子中有另外一个嗜血的自己,蠢蠢欲动的想要杀戮!
男子看着花爻却似看透她一般,他转过身,看着远处的天际,喃喃自语道“这首曲子是我们一起做的,她命的名,唤作《长安》,”他神色一黯,“只是她说这词太过于凄婉,只唱了一次便再也没有唱了,”他眉眼看得很远很远,“后来我又填了下阕,她嫁人时,我用了完整的曲子为她送行,但,她已无法知晓。”
和煦的日光照射得人眼光有些迷离,他眼神望向远处,似乎从那里便可见当年的自己,便可见那女子含笑走向自己。
“你是谁?”想起娘亲闷闷不乐那么些年,不管父汗怎样呵护总是冷若冰霜,想起娘亲她那样惦念长安,曾经那样不喜欢自己,逼迫自己成为汉家儿女。花爻突然恍然大悟,她盯着眼前的人,仿佛从他的眼中看见了娘亲的笑颜,仿佛找到了娘亲内心最最脆弱的柔情。
收回放飞的思绪,他慎重的答道:“欧阳路,我是欧阳路。”他苦笑了一下,“她也曾这样看着我,问过我……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花爻有些不敢看他的眼睛,低下头,“我叫花爻。”
欧阳路愣住了,眼中浮现出当日花轿出城的画面,火红的颜色灼痛了他的双眼,泪水却被他生生的逼了回去,没有掉下。
十里长街,邵乐阵阵。
她一步一步的远离他,心一步一步跟着去了,碎了一地的尘沙。
那夜他应了她的相约,等了她一夜却迟迟不见她,却等来了禁宫中的执事。因为闯宵禁,疑似私会宫中女婢,父亲苦苦哀求,以退出朝野作为保全他性命的条件,却被秘密处以腐刑。
家里因为他无法继续游刃官场,他气死了老父亲,被家族人纷纷鄙视。
他却一直以为自己是遭人陷害了,而不是她。只是,在蚕室,在病榻上的日子渐渐久却迟迟等不到她的一句慰问之词。
子期说,这本就是一个圈套,欧阳家势力太过于大,她便是同皇上一起设计来铲除他的心腹大患。就是那个女人害得自己成了这样,那样心狠的女人是不会再来看自己了。
他动摇了。
子期说,她要嫁给乌智当汗妃。
因为家族,因为事实,他没有勇气再去认可他们的爱情。
他很想当面问问她为什么要如此对他,即使她说不爱他,他亦会放手,可为何要这样对自己!
等了好久只等来了青儿,她蔑视的看着自己匆匆一瞥,甚至不愿再看,她说:“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为什么还要去骚扰公主!你和公主已然陌路。”
他颓然的放弃了,是呵。即使面对她,他又能怎样呢?一个已废之人,是无法去要求她那般美好的女子什么的。即便她要追求荣华富贵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呀。
火红的花轿刺入眼帘,一路逶迤,邵乐阵阵,欢呼声震天。长安街铺就了好长好长的一条红毯路,那是当朝皇上给予她最盛大的婚礼,给予她最隆重的祝福。只是站在城楼一角,他怯懦且心酸的躲在一隅,眼中流转的是他自己都弄不太明白的情愫。
他爱过她,亦恨过她,而此刻,似乎那些都不再重要了。
只要她不走,不那么远离自己,即使可以让自己远远的仰视她,他也会感激涕零。然而,她还是要走的,她会成为乌智最尊贵的女人,带着朝音的诚意,或许还有她自己的荣华美梦……
花轿渐渐的要驶出城门,他的身影有些按捺不住的颤抖的走出了那阴暗的一角,缓缓,他吹奏起了那曲子,不知这样的喧闹之中那人能否听见,不知自己这样的做法只是傻得可怜,连面对她,质问她的勇气都已经没有,如今,只有这样自欺欺人与她离别。
悠扬的箫声在喜悦的钟鼓声中却显得突兀的凄迷惨清。
“长相思,长相忆,与君别离,相去万里。往事尽飘散,故园如故否。
长相守,长相知,与君白头,执手携行。风雨皆同渡,伊人恰如旧。”
他吹着他们耳熟能详的曲子,淹没在喧闹的声响中。
一如他自以为是的爱情,虽丝丝缕缕,却也捉不住了任何端倪。
咸咸的泪滴在嘴里,他苦涩的掩藏住笑意,原来,竟如曲子所言,成真了。
送亲队伍已然走出了自己的视线,他仍迟迟不肯收回目光,风吹起他的长衫,他冷得瑟瑟发抖,本就还未痊愈的身子摇摇欲坠。缓缓,他倒在了地上……
弥蒙中,他回忆起她泪花满面,有些哀怨的说着“这曲子好凄婉啊……”
却成真了……
他做了下阕,只是她却不知……
他做了自己的承诺,只是她已作他人妇……
高楼一角,伫立的是他支离破碎的心,拴住的却是她肝肠寸断的情。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邵乐阵阵,响彻天际,似在肆意的嘲讽他!
“你说,你叫花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她,是在恨自己么?
“嗖嗖。”两声刺耳的声响破空传来,花爻立即侧身躲过了两箭,推开欧阳路执剑于身前,双眼凌厉的扫视着空无人烟的四周,周身散发出不容侵犯的气息。
四周骤然静得不能再静了,花爻警惕的握紧了手中的木剑,顿时觉得许久没有闻见杀戮的味道自己竟有些不大习惯了。她转了转手中的木剑,挥手让欧阳路离开。
欧阳路却昂然站在花爻身前,高声喝道:“朗朗乾坤下,何方鬼神暗地偷袭……”
花爻无语的看着站立在自己身前的男子,突然大喝一声“小心!”一把拉回他,不管他是否摔得跌坐在地上,性命总算是捡了回来。欧阳路还没有回过神,就眼见几支利箭从自己的头顶呼啸而过,顿时冷汗淋漓。
花爻明眸半闭,发出精亮的光泽,四周短时涌出五个蒙面黑衣人,几番闪躲的身影后,人便如鬼魅般闪身到了离花爻咫尺间的地方,若困兽一般将花爻困在垓心。
花爻冷笑道:“何人指使?”
“小的只是奉命行事,请!”黑衣人瞬间齐齐动手,明晃晃的利刃从四面八方锁住花爻要害,欲一招致命。
花爻脸上划过嘲弄之色,眼光一掠,直接下腰,一手点地,一手中的木剑点中身后之人的麻穴,利刃顿时脱手。花爻趁势后退几步,左手如鹰爪一般直索那人喉咙,脚尖勾起地上掉落的剑握在手中。
“烦你好好看着这柄剑,莫让污秽的东西给玷染了!”说完将木剑丢给欧阳路,几乎在同时,利刃划过那人的喉咙,连一声闷响都来不及发出便一命呜呼了。
缕缕鲜血顺着泛着白光的利刃滑下低落在地上,花爻拖着剑,扫射着四周,脸上明目张胆的充斥着鄙夷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