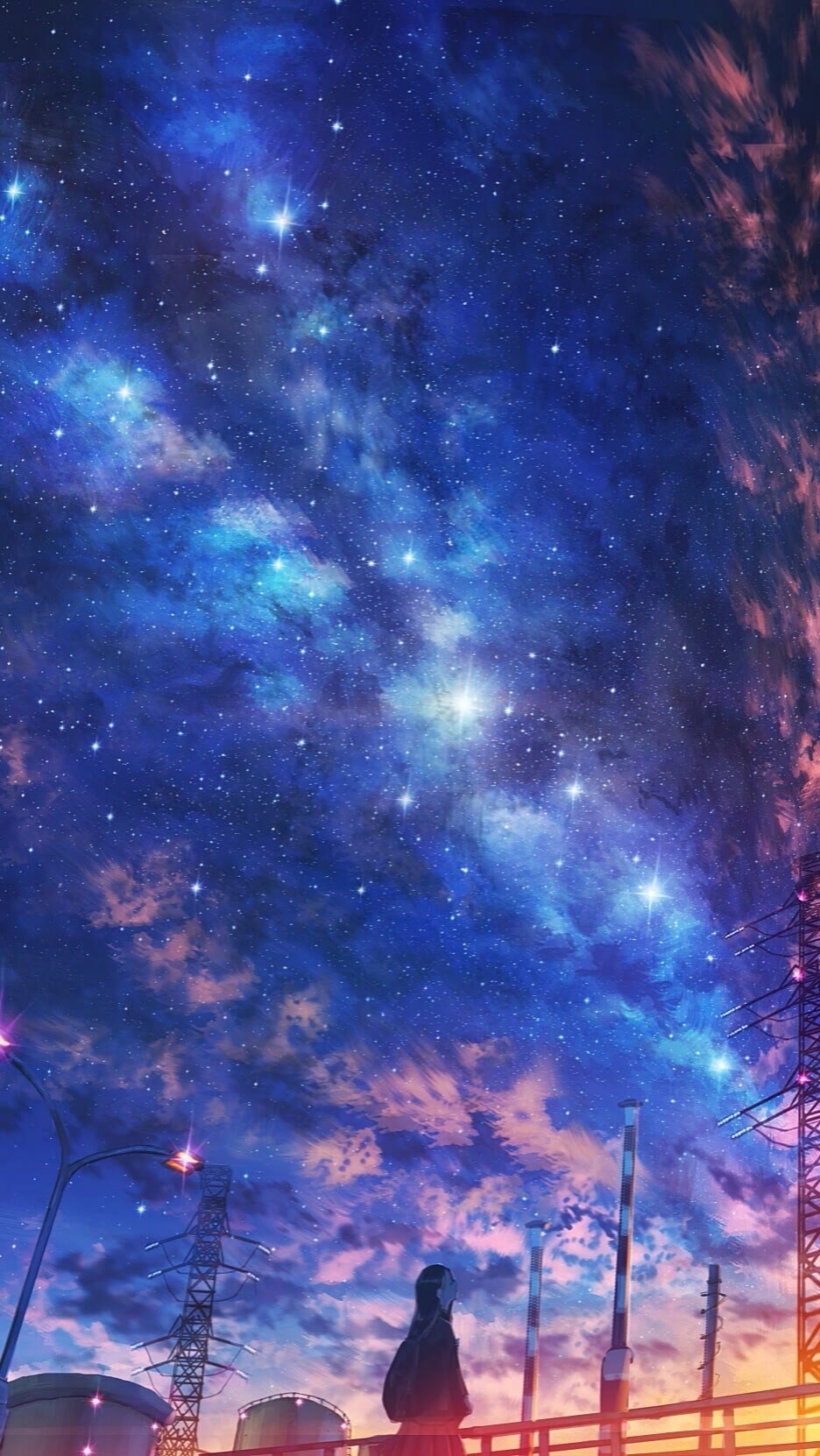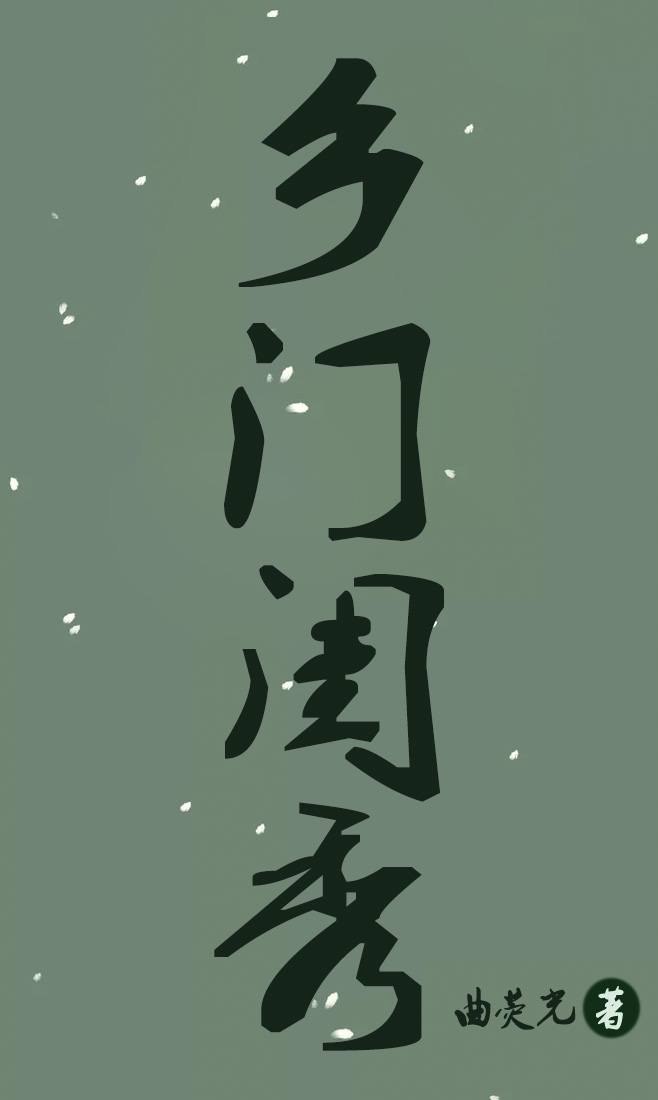如果问你,今天有意义吗?回答往往是“有”。时光如离弦的箭一般消逝,但是人生往往是每天都在重复做着同样的事。但是真要去发现一些新的事物,就难了。甚至,有时会意想不到。
来到了每年换配件的日子。每当在这时候器械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和锈蚀,需要进行处理,或用新的配件来适应新的需求。一大早,父母就眼特儿告别。带上门后,特儿还扒专毒在窗前复着父母远去的身影,伴随着晨光和人为踩出的小径一起消逝在远方,这种场景,是多么的熟悉,多么的亲切,但没想到,这一等竟然意味着最后一次决别。
傍晚时分,敲门声响起。正要去开门,突然发觉这敲门声不比平常,显得尤为急促。她仔细眯着眼朝门缝中望去,一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是邻里安妮啊。既然还算相识,放心了,特儿随即开了门。除了邻里外,门外站着几名巡警,交谈了几句之后便走开了。虽然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既然家里来人了,还是得要招待一番。特儿发现她时不时用怜悯的眼神瞥瞥她,时不时自顾自地叹气。这也太夺怪了,似乎是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请问,"顿了好一会,特儿终于开口道:“出了什么事吗?”安妮眼神突然一下子惊惶,泄露了什么重大机密一样,但随即又舒缓下来,颤抖着的手从腰包里不断摸索着,带出一份文件——既然事情已经瞒不住了,干脆就摊牌了吧。特儿疑惑地接过文件。土黄的封皮,酒红的定子,被一根白线接实地扯在一起。扣下定子,用手把纸张轻轻夹出来,血红色的“死亡报告’字样首先渗漏出来。特儿先是一怔,一阵不妙感蔓延了全身,心跳加速!左手捂着心脏深吸一口气,额料的右手开始把纸的剩下部分展开。直到,父母的两张照片映入眼帘。
一道晴天震需,直洞穿到她心里。“我——“话还没挤出来,她就感到天悬地转,直到两眼一黑,周围瞬间就一片安静了,事后发生了什么,一概记不清了。
再睁开眼时,世界都变成白色的了。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铺,白色衣服的人。“我这是在哪?”她想坐起身来,耐不住体力消耗太多,只勉强直起了身子。
身处在医院里啊。
现在她终于看清了。一边安妮跟咨询医师聊得正投入:“病人精力消耗太多,需要休息。哎,这可怜的孩子。”安妮转过头,特儿已经醒了,两人对视了几秒。特儿发现她眼睛红红的,似乎有哭过。前台医师眼睛也红红的,拿着手帕捂着嘴,径直朝门口走去,眼神示意了一下。前几天特儿见到的辅警大步走进来。
“是这样的没错。”高个子先开口了:“前几天,就是,百货公司开业的日子对吧。大楼被歹徒事先安放了炸药,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成废墟了。”
“那为什么工作人员发现了之后没有立即组织撤离?”
“是这样的,”瘦子翻着记录本:“前些日子也发生过类似事件,而那次是据传有人往女厕堆放固态炸药。但在人撤离之后,调查发现,一场恶作剧而己。”
“因此这次,人们都以为......“
“呃,大概如此。但是现在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还要做些善后工作。”
基于什么"善后工作”特儿当然不大了解,当她听说为了以后自己的生计,他们决定把她送到孤儿院时,心中不免害怕起来。阴暗、肮脏、恶臭,一群面黄肌瘦的孩子在一起干着繁重的活,吃不饱穿不暖,终日时着非人的生活......脑海里浮独出种种画面。但大人们却在那津津乐道:“你当那是济贫院呐,那个年代现在可以比的?”他们都不这么认为,反而觉得那是一个理想的去处。
身体恢复后,安妮第一时间把特儿送回了家。推开沉重的木门,似乎,没有了以前的古香,而多了些腐朽的浑浊气息。房间内静得出奇,心脏的怦跳都能感受得到。下了楼梯,每踩一阶,都发出质地的摩擦声,随着从窗户投射进来的光芒,消逝在了远方。最后一眼,都是最后一眼——可能等到这种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过去是多么的珍贵,多么难以忘怀。一言不发地,她把大门关上,锁链搭好,回头还不忘用手把泪痕拭干,
安妮已经在门口等着她了,伸出手,亲切地把她拉上车。但在特儿看来,那不是一双天使的手,相反,一双恶魔的手,正不知要把她带往何处去。顺着车窗,向外望去。傍晚的夕阳正没入云层,重重叠叠的火烧云洒落在那幢古色古香的建筑物上。随着车子的开动,房屋不断缩小,以致于从眼眸中谈化,留下一团散着光粒子的虚影向远处发散。
车身的颠簸和心情的压抑,阵阵困倦感袭来 ,眼睛防线被逐渐攻破,开始慢慢耸拉下来。
朦朦胧胧中,她感到有一只手在推她。勉强地睁开惺松的睡眼,周围天空的黑色幕布已经落下,伴着墨蓝的云雾装饰升腾起来。
下了车,一幢庞大建筑映入眼帘,全部用稳重的大理石堆砌,城堡一样。正门用端雅的紫铜镀上,经过时光的锤炼,油光发亮起来。两块竖木板构成了门的主体,锈蚀的锁柄秃鲁鲁的从门缝里伸出来。安妮用手敲了敲门。不一会儿,门被费力地拉开了, 发出与地面摩擦的刺耳声响。伴随而来的还有一抹光亮。从门内探出个头人来:墨绿的鸭各帽,身着一看便是乡村蹩脚裁缝缝制的粗呢服装,脚踏一双褪了色的皮鞋。一双狡黠明快的眼睛,伴着他那拉碴的胡子。安妮同他握了握手。他依遇见了老熟人一 样也抓着她的手使劲握了握,随即正了正身子,把他们请到了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