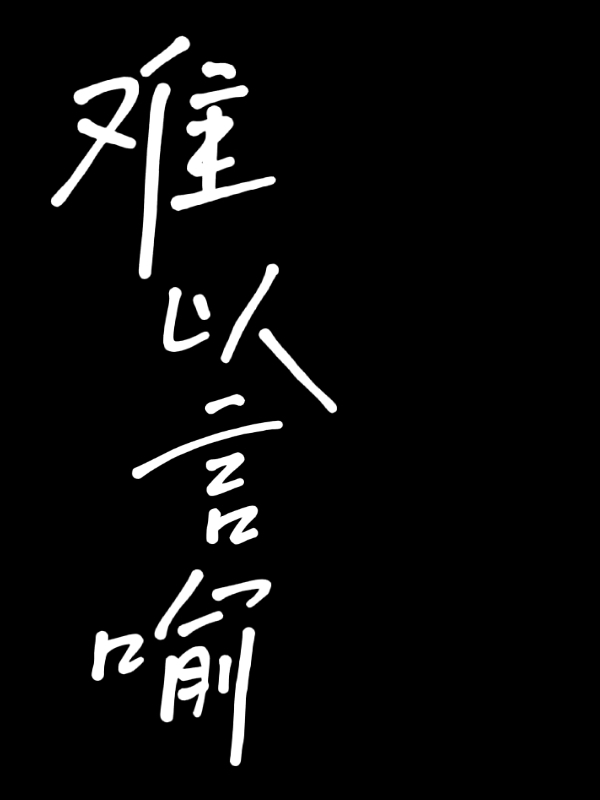“发誓你能做到这一点,一月,”当我离开城镇时,安雅说。 “如果我答应桑迪在 9 月前一本书,我们就必须在 9 月前出一本书。”
“那段时间我已经写了一半的书了,”我在风中喊道。
“哦,我知道你有。 但我们谈论的是这份手稿。 我们正在专门讨论现在需要 15 个月并且还在继续的那个。 你多远?”
我的心在狂跳。 她会知道我在骗她。 “没写。”我说。 “但这是计划好的。 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敲定它,不要分心。”
“我不能分心。 我可以成为不打扰你的女王,但请。 拜托,拜托,拜托,不要在这件事上对我撒谎。 如果你想休息一下——”
“我不想休息,”我说。 我买不起一个。 我不得不做任何事情。 把海滨别墅清空,这样我就可以卖掉它了。 尽管最近失去了对爱情和人性的所有信仰,但还是要写一段浪漫。 “事实上,进展非常顺利。”
安雅假装很满意,我假装相信她很满意。 那是六月二日,我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来写一本像书一样的东西。
所以当然,我不是直接回家上班,而是开车去杂货店。 我喝了两口皮特的拿铁咖啡,喝了三口太多了。 我在去 Meijer 的路上把它倒在垃圾桶里,然后从里面的星巴克售货亭换上一杯巨大的冰美式咖啡,然后储备了足够的食物(通心粉、麦片、任何不需要太多准备的东西)来维持我的胃口 几个星期。
当我回到家时,太阳已经很高了,热度又浓又粘,但至少冰镇的浓缩咖啡减轻了我头骨中的砰砰声。 卸完杂货后,我把电脑带到甲板上,才意识到昨晚我让电池没电了。 我回到里面把它插上,发现我的手机在桌子上嗡嗡作响。 来自 Shadi 的文字:没办法。 性感、邪恶的 GUS? 他问过我吗? 告诉他我想念他。
我打字回来,仍然性感。 还是邪恶的。 我不会告诉他,因为我不会再和他说话,只要我们都还活着。 他不记得我了。
沙迪立即回答。 嗯,这绝对不是真的。 你是他的童话公主。 他的影子自我。 或者他是你的,或者其他什么。
她指的是我试图忘记的另一个让 Gus 丢脸的时刻。 他最后和 Shadi 上了普通数学课,并提到他注意到我们是朋友。 当她确认后,他问她我的“交易”是什么。 当她让他详细说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时,他耸了耸肩,咕哝着我的行为就像一个被林地生物养大的仙女公主。
沙迪告诉他,我实际上是一位皇后,由两个非常性感的间谍抚养长大。
我告诉她,这么长时间后在野外看到他真是太可怕了。 我很受伤。 请来护理我恢复健康。
很快,habibi,她回信了。
那天我的目标是写一千五百字。 我只打到了四百,但从好的方面来说,在我停下来炒菜做晚餐之前,我还连续赢得了 28 场蜘蛛纸牌。 吃完饭,我坐在黑暗中,在厨房的桌子旁折叠起来,笔记本电脑的光芒映入了一杯红酒。 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糟糕的初稿。 我写了几十个,吐出来的速度比我打字的速度还要快,然后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煞费苦心地重写。
那么为什么我不能让自己写这本糟糕的书呢?
天啊,我怀念那些话语倾泻而出的日子。 在写那些大团圆结局时,雨中的亲吻和音乐膨胀的跪在地上的求婚场景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部分。
那时,真爱似乎是大奖,一种可以抵御任何风暴,使您免于苦差和恐惧的东西,写下它感觉就像是我能给的最有意义的礼物。
即使我的世界观的那部分是短暂的休假,但有时,伤心欲绝的女性找到了她们的幸福结局,她们下雨,音乐膨胀的纯粹幸福时刻。
我的电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我的胃开始翻腾,直到我确认这只是 Pete 的回复,还有她读书俱乐部的地址和一句话的信息:随意带上你最喜欢的饮料或只是你自己 :)))
我笑了。 也许某些版本的皮特会被收录进书中。
“一天一次,”我大声说,然后拿起我的酒,向后门走去。
我用手捂住眼睛,挡住玻璃上的眩光,然后凝视着格斯的甲板。 早些时候,烟从火坑里冒出来,但现在烟消云散了,甲板被遗弃了。
于是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世界笼罩在蓝色和银色的阴影中,潮汐冲刷沙地的声音因世界其他地方的寂静而变得更加响亮。 一阵风从树梢吹来,让我不寒而栗,我收紧了身上的袍子,倒掉了酒杯,然后转身回到了屋子里。
起初,我以为映入我眼帘的蓝光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发出的,但并不是我家发出的。 它从 Gus 家原本昏暗的窗户照进来,足够明亮,我可以看到他在他的桌子前踱来踱去。 他突然停下来,弯下腰打了一会儿,然后从桌子上拿起一个啤酒瓶,又开始踱步,他的手穿过头发。
我很认同那种编舞。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迷恋海盗和狼人,但归根结底,奥古斯都·埃弗里特仍然在黑暗中踱步,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胡说八道。
皮特住在大学校园边缘的粉红色维多利亚时代。 即使在那个星期一晚上从湖边掀起的雷雨中,她的家也像玩具屋一样温馨。
我把车停在路边,抬头盯着爬满常春藤的窗户和迷人的塔楼。 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山,但漫天的柔和灰色云朵将任何光线都散射成微弱的绿色光芒,从皮特的门廊一直延伸到她的白色尖桩篱笆的花园在雾气笼罩下显得郁郁葱葱和神奇。 这是我躲了一整天的写作洞穴的完美逃脱。
我从乘客座位上抓起装满签名书签和南方舒适行情别针的手提袋,跳下车,拉上引擎盖,冲进雨中,轻轻打开大门,沿着鹅卵石小路滑入。
皮特的花园很可能是我去过的最风景如画的地方,但最好的部分可能是,在轰隆隆的雷声中,平克·弗洛伊德 (Pink Floyd) 的“墙上的另一块砖”正在大声播放,以至于门廊 当我踏上它时,我在发抖。
我还没来得及敲门,门就被打开了,Pete 手里拿着满满的塑料蓝色酒杯,大声喊道:“Jaaaaaaaaaaaaanuary Andrews!”
在她身后的某个地方,一群人齐声唱回:“一月Annnnndrews!”
“Peeeeete,”我唱着回应,拿出我在路上从商店里拿来的一瓶霞多丽。 “非常感谢你有我。”
“呵呵。” 她接过那瓶酒,眯起眼睛检查标签,然后笑了起来。 它被称为 POCKETFUL OF POSIES,但我把 POSIES 刮掉并在它的位置上写了 PETES。 “听起来是法语!” 她开玩笑说。 “这是荷兰语中花哨的意思!” 她挥手让我跟着她穿过大厅,走向音乐。 “进来见见姑娘们。”
门口的地毯上整齐地摆放着一堆鞋子,主要是凉鞋和登山靴,所以我踢掉了我的高跟绿色雨靴,沿着Pete穿过大厅的赤脚小径走去。 她的脚趾甲被涂成淡紫色,以配合她刚刚修过的指甲,她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白色亚麻纽扣衫,给人一种比在商店里更柔和的形象。
我们扫过一间花岗岩台面堆满酒瓶的厨房,走进房子后面的客厅。 “通常,我们使用花园,但通常上帝不会在头顶上打一场完美的保龄球比赛,所以今晚必须在室内进行。 我们只是在等一个。”
房间很小,里面总共有五个人,感觉很拥挤。 当然,在沙发(其中两个)和扶手椅(第三个)上打盹的三只黑色拉布拉多犬也无济于事。 亮绿色的木椅被拖了进来,表面上是供人坐的,排列成一个小半圆形。 其中一只狗跳起来游荡,摇着尾巴,穿过腿海迎接我。
“姑娘们,”皮特摸着我的背说,“这是一月。 一月带来了酒!”
“酒,好美!” 一个金色长发的女人说着上前给了我一个拥抱和一个吻在我的脸颊上。 金发女郎退后,皮特递给她一瓶酒,然后绕过房间走向音响系统。 “我是玛吉,”金发女郎说。 她那高大、柔顺的身材因她穿着的白色衣服的海洋而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她低头对我微笑,与金色森林的凯兰崔尔夫人和年迈的史蒂维尼克斯相当,还有她棕色眼睛的皱纹眼角 甜蜜地皱起。 “很高兴见到你,一月。”
皮特的声音太大了,音乐从它下面消失了:“她是皮特夫人。”
玛吉平静的笑容似乎是一种深情的翻白眼。 “只有玛吉会做。 这是劳伦。” 她张开一只手臂,为我腾出空间与穿着橙色太阳裙、留着辫子的女人握手。 “后面,沙发上,是索尼娅。”
索尼娅。 这个名字像锤子一样击中了我的胃。 还没见到她,我的嘴就干了。 我的视线在角落里模糊不清。
“嗨,一月,”那个女人在打鼾的拉布拉多犬底下温顺地说。 她勉强笑了笑。 “很高兴见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