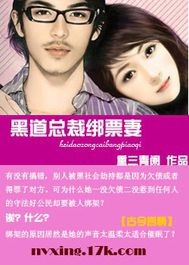黑龙会僻处在城郊,一个叫燕子坞的水泊旁,距郡城三十公里左右。妮可坐马车紧赶慢赶,一路疾驰,路上也花去了四十分钟。
正是月色初微、星光灿烂之际,一轮明月水润润、亮晃晃地挂在中天,怎么看都像是观音的脸。
在坞外二、三公里的地方,妮可听从了狗剩的劝告,一勒马缰停了下来。权衡再三,妮可还是决定把马和车寄顿在一个农户家里,以便缷下身上的包袱,全力以赴。
农夫看了看妮可,有些为难,妮可四顾无人,暗暗地在他的手心里塞了一锭银子。农夫这才眉开眼笑地应承了下来,把个脑壳点得像鸡啄米。
刚刚下过一场小雨,路有些湿滑难行,不时有些苦竹和葛藤挡住去路。妮可趁着夜色,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在前面,狗剩不即不离在后面跟随。
看得出,狗剩有些紧张和恐惧,两只营养不良眼睛睁得大大的,像饿惨了的非洲儿童。
妮可也有些紧张,但比狗剩好多了,她毕竟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老雀子了。
妮可笑了笑,不由自主地加步了脚步,不管怎么说,她不能叫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挡在她的前面。那样传出去也会叫人笑掉大牙,为人所不齿。
坞里灯火通明,远远近近的房子高低错落,一半浴满了融融的月色,一半沦陷在黑暗之中,远远望去,就像一只只面目狰狞的怪兽,让人大吃一惊。
进坞的道路有人把守,妮可和狗剩不得不停了下来,进一步观察,以徐图后计。
大路进不去,而没路的地方又修了围墙,架上了铁丝网。除非…除非人能插上翅膀。
妮可暗暗寻思,两只眼珠子不停地转来转去。突然,她看见了一根虬枝斜伸的歪脖树,一下子茅塞顿开。歪脖树从坞里伸出来,不偏不倚地搭在围墙上,正好可以当一架梯子。
妮可和狗剩手足并用,一前一后地爬上了歪脖树,爬上了围墙,敏捷得像两只猿猴。
正在观望,围墙下突然响起了几声狗吠,一条恶狗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妮可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好在狗剩早有准备,从怀里掏出一只浸过蒙汗药的肉包子,嗖地一声扔了过去。
恶狗见了肉包子,就像饿崽见了亲娘,一口呑了下去。不一会儿,就四肢绵软,扑倒在草丛里。想不到狗剩小小年纪,就己经是个老江湖了。两个人又蹑手蹑脚,凝神屏息,趁着夜色的掩护,悄无声息地摸进了一幢很大、很大的房子。
房子真的很宽、很大,像一个储备仓库,或者,某个工厂的生产车间。车间里摆着一排排的土瓮,横横竖竖,就像秦始皇的兵马俑,气势恢弘。
土瓮不高,在灯光下呈古铜色,颇有几分艺术品的味道。如果细心一点,还可以闻到一股人畜糞便的怪味。
妮可一皱眉头,仔细一看。妈吔!原来每一只土瓮里都住着一个小人儿,身子陷在瓮里,仅仅露出头和两只眼睛。
妮可一下子恍然大悟,天啦,原来矬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出自同一家工厂,同一个车间,同一个批次,就像超市货架上出售的那些人偶。
妮可忍了又忍,可止不住的泪水还是夺眶而出。狗剩也唏唏嘘嘘地哭出了声。都说人之初,性本善,都说连魔鬼也有一颗赤子之心,可现实是多么的残酷啊,人心又是多么的险恶?妮可正在感慨,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拖拖沓沓的脚步声。
“王贵,你带人到地龙车间去看看,里面好像有声音。我去蜜瓜车间。”说话的是个头,提着灯笼。叫王贵的唯唯诺诺,不知应了一句什么。那人火了,重重地一跺脚,接着又说:“张强、赵虎你们莫笑,你们也去做个帮手,凡是有人私闯我黑龙会,杀无赦!”
张强、赵虎挺着刀,王贵擎着灯笼,一行三人气势汹汹,朝妮可和狗剩藏身的土瓮走了过来,火光影影绰绰。
完了,完了。妮可暗暗叫苦,四肢筛糠似地抖个不停。狗剩也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额头上冷汗涔涔,腿杆子也在不停地抽筋。
几个人走到妮可和狗剩藏身的土瓮前,正要捜个仔细,一个土瓮里的小人儿实在忍不住,噗地放了一个响屁,惹得大伙儿都笑了起来,弄得整个车间里都臭气喧天。
王贵火了,捏着鼻子,狠狠地在土瓮上踹了一脚。冷不防从土瓮里又蹦出来一个响屁,薰得大伙儿几乎窒息。
“倒霉,倒霉!”张强、赵虎一声怪叫,转身就跑。王贵见同伙跑了,举着灯笼乱晃了一气,也没找到藏在土瓮阴影里的妮可和狗剩,也跟着跑了。一边追,一边喊:“张强、赵虎,你们等等我!”杂杂沓沓的脚步声响成了一片。
各位有所不知,黑龙会办有两大工厂,一曰地龙,一曰蜜瓜。什么叫地龙呢?就是将从全国各郡各区各县拐县、败卖、收容来的孤儿,择其男性,分成不同的年龄段,养在一只高约一米二的土瓮里,身子下陷,仅仅露出脑壳和两只可以骨骨碌碌转动的眼睛。
人吃饭就会生长,可孩子被土瓮困住,始终也长不大,长不高,哪怕人成了年,也始终制约、屈从在一米二的范畴,因个子矮矬,故名地龙。
矬子炼成之后,黑龙会再教以歌舞骑射和诸般乐器,聪明者可以出演小丑、嬖童等;智下者,则分配到各郡各区各县乞讨。
蜜瓜工厂就不同了。蜜瓜工厂里的全是聪明伶俐的女孩子,分成不同的年龄层次,养在一只高高长长的吊篮里,再配以一个可以自由伸展的弹簧。
弹簧一直从女孩子的下颌骨伸到脚踝,始终保持一种韧性和一种张力,以促进骨骼的生长和发育。
可以说,蜜瓜工厂生产出来的女孩子,个个体态妖娆,身材婀娜,要胸有胸,要臀有臀,故名蜜瓜。黑龙会再教以歌舞弹唱,自然而然,个个都是天生尤物,花中魁首。黑龙会进而可以凭她们,牢牢控制妓院、赌场和码头,乃至大小官员和豪绅巨贾。
紧盯着张强、赵虎和王贵渐行渐远,妮可才拍拍胸脯,从土瓮的阴影里站了出来,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狗剩也吓得不轻,小脸上白一块黑一块地沾满了污泥,横竖都像戏里的小丑。妮可忍不住扑哧一笑。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这些养在土瓮里的小孩,是他们用屁一次又一次地迷惑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搭救了自己。
妮可偷偷摸摸地潜出了地龙工厂,冷风一阵阵地吹了过来,全身陡添了几分寒意。月色阑珊,星月满天。
狗剩也仰住脸,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就像干滩上濒死的鱼。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又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两辆马车风一般地疾驰而来。
妮可怔了一怔,一把扯住狗剩的胳膊,两人相视一笑,赶紧在黑暗里蹲了下来。马车嘎地一响,稳稳地在一栋木楼前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来一个身披鹤氅的黑衣人。黑衣人蒙着头,看不清脸。另外一个是胖子,满脸横肉,谨小慎微的样子。
“夏总管,这批货什么时候到?男娃有多少?女娃有多少?你验过货没有?”黑衣人一边走,一边问,口气十分威严。回头看了胖子一眼,接着又说:“妓院、赌场、码头的账,你要负责及时回收,抽头一两都不能少。还有是乞讨的矬子要再多派一些,盆大刮得粥来。”
“是,是,会长!”胖子眉开眼笑,连连点头。
“助残基金会的人真是可恨,垄断了整个益稼郡的孤残儿童,屡次断我资源,坏我大事。”黑衣人顿了顿,凶相毕露,接着又说:“夏总管,你派去刺杀艾米莉和妮可的矬子有消息了吗?成没成功?暴没暴露?对我们的刑天计划有没有影响?”
“会长!”胖子沮丧地低下了头,怯怯地说:“矬大死了,矬二被开水烫伤。”
“死了的就死了,开水烫伤的那个,你找个机会把他做了,免得到处乱喷,死人是开不了口的。真是两个废物!”黑衣人恨恨地骂了一句。
“那个妮可还杀不杀?”
“杀!犯我黑龙会者,虽远必诛!”黑衣人斩钉截铁。
“会长,听说这个妮可是艾米莉的亲姐姐,来头可不小。”胖子怯怯地看了黑衣人一眼,接着又说:“听说她是现任郡守的夫人?丈夫还兼着大理寺的正卿,官居极品。”
“我不管她是什么来头?也不管她的丈夫是谁?都得死!”黑衣人恨得咬牙切齿。
“会长,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胖子征询地看了黑衣人一眼,诚惶诚恐惶。
“夏总管,你先缓一缓,等我在海外请的忍者到了,把艾米莉、妮可、朱平他们三个一并做了,一箭三雕。”黑衣人阴险地一笑,做了个杀鸡抹脖子的动作。
“会长高见,那到时候,艾米莉的宝树就是您的了。”胖子见风使舵拍起了马屁。
“哼,岂止宝树?”黑衣人鼻子一哼,满脸不屑。
天啦!妮可虽然蹲踞在黑暗里,全身血流不畅,腿脚有些发麻,可黑衣人和胖子的对话,她却听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风险真是无处不在。原来…原来丈夫、艾米莉和自已,都有人在暗中下手。看来,她一定要赶回去向人精报告,一举端掉黑龙会的老巢。
妮可丝毫也不敢大意,跟着狗剩凝神屏息,原路返回。院墙下,不时有些护院提着灯笼,扛着刀枪梭标,昂然而过,牵在手里的狗也汪汪地叫个不停。至于护院中有没有张强、赵虎和王贵,妮可就不清楚了。她只得和狗剩只得原地蹲在草丛中,等护院们先行通过。
顺着歪脖树爬出高高的围墙,剩下的路就顺畅多了。妮可和狗剩轻车熟路,找到了寄顿车马的农户。农夫得了银子,不敢走远,守在马车旁边打着盹。马儿卸了辕套,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青草,尾巴一甩一甩的,样子十分悠闲,把活动范围内的青草践踏得一塌糊塗。
见到妮可和狗剩,农夫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站了起来,高兴坏了,忙着牵马驾辕。送走妮可和狗剩,银子就到手了,何乐而不为呢?
妮可心事沉沉地坐在车辕上,一抖缰绳,马儿欢快地奔跑起来,如一艘白白的航船,劈波斩浪,缓缓地在月色中穿行。
妮可归心似箭,片刻也不敢停留。这次意外截获的情报太重要了,事关大局和丈夫的生死。她不能马虎,也马虎不得。对于妮可来讲,自己的安危还在其次,人精的生死她就不得不考虑。有人对人精不利,就是对她妮可的挑战,她可以豁出一切!
艾米莉也有危险!妮可虽说不知道什么叫宝树?可她知道黑龙会的人,黑龙会重金聘请的那两个忍者,一定不会放过艾米莉。
妮可的心咯噔一响,一下又悬了起来。她一边策马驱车狂奔,一边牵挂着妹妹艾米莉的安危。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