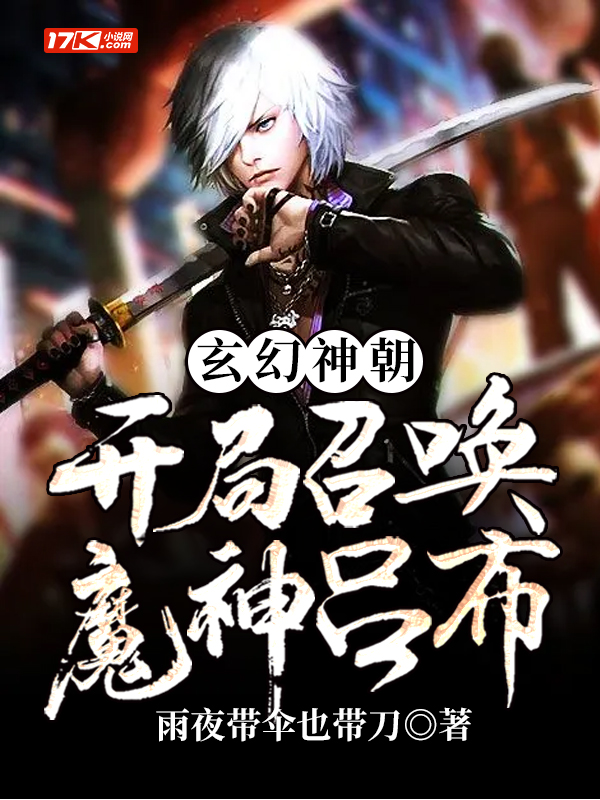九月二十五是个好日子,秋高气爽,稻菽飘香,天蓝得就像一块巨大的玛瑙,纯净得没有半点杂质。艾米莉带着僮仆们进场的时候,场子里已经人头攒动,坐无虚席。
好在艾米莉早派人占了位,一行人在第五排的中间位置坐了下来。座位不靠前,也不靠后,正好可以总揽全局。拍卖会的会场原先是一座教堂,有穹顶,有飘窗,有西式雕塑,充满了欧式建筑的风味。
公证员和拍卖官早就到了,一个个正襟危坐,或埋头翻阅桌子上的资料,或交头接耳,或抽烟喝茶。看样子,拍卖官和公证员年纪都不小了,秃的秃顶,白头的白头,彼此也都很熟悉,一副踌躇满志、老谋深算的样子。
李皇亲进场的时候,场内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全体拍卖官和公证员都站了起来,点头致意,鼓掌欢迎。那情形,根本就不像资产拍卖会,倒像是出席一场盛大的晚宴。也难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皇亲就是皇亲。
坐在最显要的位置,李皇亲明显的,有些局促不安,左顾右盼,且心事沉沉。艾米莉知道:他是在等聚德轩和仙客来,在等毛德雨和谷正喜,在等他生命中,最后的两根救命稻草。艾米莉暗暗有些好笑。
拍卖会开拍之前的五分钟,聚德轩和仙客来的人都来了。不过,毛德雨和谷正喜都没来,来的是全权代表。这些日子以来,聚德轩和仙客来狗咬狗,一嘴毛,自顾尚且不暇,哪有兴趣参加拍卖会?来了人,就是对李皇亲有个交代。看来,一切都在艾米莉的掌控之中。
拍卖马上就要开始了,艾米莉的心又悬了起来。秃头发的拍卖官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老花镜,照本宣科地读完了拍卖公告,公证员也宣完誓。拍卖官一敲法棰,拍卖会正式开始。拍卖的标的是皇庄内的全部资产,打包拍卖。这样一来,就把一些实力不济的小公司全部关在门外。
场上有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些有心参与的小公司,不满拍卖官的打包二字,愤而起身,纷纷离席,座位立刻空出了一大半。不过,又有一些人补充进来。艾米莉看了看,都是些拿着白条子来讨债的粮农。
第一个举牌的是德聚轩,出价白银五千两;第二个举牌的是仙客来,出价白银一万两;德聚轩和仙客来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就好比白素贞和法海斗法。你一万五,我二万;你二万,我二万五;以五千两为基数,步步紧逼,一路攀升,把价格拍到了白银五万两之巨。
看到德聚轩和仙客来斗法,李皇亲乐得眉开眼笑。两大财阀再这么比下去,不消几个回合,把价格抬升到二十万两的高位,他的目的就已经完全达到。他早就请人评估过了,皇庄也就值这个数,多也多不了多少。
拍卖在五万两上面卡了壳,只有李皇亲预估数的四分之一。李皇亲的心紧张起来,一双热眼不由得东张西望。他多么希望有个人接盘,把拍卖再继续下去,抬升到二十万两的高位。可场上鸦雀无声,看样子,根本不会有奇迹出现。
冷了二分钟的场,拍卖官在五万两上面叫了两次,满头虚汗,面白如纸。关键时刻,艾米莉举起了木牌,要了六万两。场上一片哗然,李皇亲眼巴巴地看了过来。看到艾米莉,他不知是感激?还是惶惑?
紧接着,德聚轩和仙客来也紧紧地咬了上来,德聚轩要了六万五,仙客来要了七万两。李皇亲如释重负般地松了一口气,高度紧张的心又恢复了常态。看来,天无绝人之路,上帝无处不在。
艾米莉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又举牌要了八万两。按照艾米莉的精确估计,如果没出事,德聚轩和仙客来都有能力吃进皇庄,价位在十八万两至二十二万两白银之间。出事之后,双方都流了血,死了人,给死者作了巨额赔偿,再加上伤者和营业上的损失,七七八八,德聚轩的承受能力应该在十万两到十二万两白银之间。仙客来的承受能力更小,在九万两到十一万两白银的范围。
果不其然,当艾米莉举牌要了十万两之后,德聚轩和仙客来的全权代表都高度紧张起来,一个个坐立不安,汗出如浆。德聚轩勉强加了五千两,举牌要了十万五千两。仙客来见势不妙,则干脆弃权,缴械投降。
关键时刻,艾米莉又乘胜追击,果断举牌要了十一万两。德聚轩的全权代表见大势已去,已超出了自己的权限,最后的一举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只得悻悻地弃牌退出,满脸沮丧。
一时里,全场默然,静得能听见艾米莉剧烈的心跳。拍卖官环顾了一下四周,重重地一敲法棰,声音朗朗地说:“十一万两一次,十一万两二次,十一万两三次,成交!”拍卖官重重地敲下了法捶。
突然,全场欢呼起来,有人脱下了自己的帽子,奋力抛向空中。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雷霆般地席卷了整个会场。艾米莉像个明星,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了起来,黑亮的瞳孔里噙满了亮晶晶的泪花。
李皇亲简直气炸了肺,一座价值百万两的皇庄,才拍下了区区十一万两,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相隔了十万八千里。这不是他所期盼的。他含着金汤匙出生,在蜜罐子里长大,父亲留下了巨额财产,亲姐姐又嫁了皇帝。命该大富大贵,位尊爵显。
为什么命运就这么残酷呢?他李皇亲想要的,偏偏就得不到;不想要的,又总是强加给他。他想方设法捞钱,甚至不惜巧取豪夺,坑蒙拐骗,费尽了心机。可钱还是离他而去,像个反目成仇的爱人,弃之如敝履。
这么些年来,李为就像一个可怜的倒霉蛋,四处折腾,四处碰壁。永泰没了,华益没了,眼看着皇庄又没了。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困浅滩遭虾戏。本来,他跟德聚轩和仙客来早就商量好了,把拍卖价格抬升到二十万两银子,谁知道他们中途退出,做了缩头乌龟。世态炎凉啊!墙倒众人推。
人活着就是一个笑话。
想他李为,一个富甲一方的大财主,一个地位显赫的皇亲,一下子就成了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一个人人所不齿的破落户。命运真是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完了,完了,这辈子都完了。不,他不甘心。他要东山再起,他要赢回失去的一切。
李皇亲越想越急,越想越气,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截住了正在收拾文件的拍卖官和书记员,脸红脖子粗地说:“公证员兄弟,拍卖官大爷,皇庄我不卖了。我太亏了,亏大了。那可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祖业,卖不得啊!”李皇亲死死地拽住了拍卖官的手,一把夺下了他手上的法棰。
“你说不卖就不卖?法律又不是儿戏。”拍卖官的脸涨得通红,秃顶上的麻子粒粒发光。
“我说不卖就不卖,皇庄是老子的,我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李皇亲脖子一抻,响亮地拍了拍胸脯。
“李皇亲,我们尊重你的地位,也承认你是皇帝的亲戚。可你欠下的那些账呢?总不能老拖着不还吧!”公证员也在一边帮腔。
“你算老几?老子是李皇亲,我说不还就不还!”李皇亲怪眼一翻,耍起横来。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拍卖官冷冷回怼。
“我李皇亲大小也是个财主,好歹也是个皇亲,我欠别人的是理所当然。就可以先欠着,就可以不还。”李皇亲重重地一跺脚,越说越跑调,越说越无理,有点胡搅蛮缠的味道。
“我的个皇亲老祖宗哎!你也体谅、体谅我们的难处,粮农们天天逼,郡守天天催,皇上也下了圣谕。你不卖皇庄?我们就丢饭碗。求皇亲爷爷高抬贵手,通融、通融。”拍卖官拱了拱手,团团转转作起了箩圈揖。另外的几个拍卖官和公证员也大声附和。
“那你们容我先想想办法。要不,我进宫去找我姐姐,向皇上求情,说不定皇上一高兴,就替我把这些钱都还了。”李皇亲摸了摸后脑勺,还在异想天开。
“李皇亲,进宫就没必要了,皇上早就下了圣谕,限定我们必须在九月二十五日之前,把皇庄卖了,以偿民户之欠。这么多老百姓造反,后患无穷哪!”拍卖官据理力争,又煽动性地朝台下看了一眼,大声地说:“粮农大哥,你们说是不是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老子就不还钱,看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一群泥腿杆子,难道还想翻天?”李皇亲的犟劲又上来了,且一脸轻蔑。
“李皇亲,我们忍你已经很久了,我们敬你是个皇亲,但不代表我们怕你。你欠下的,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哪!”一个粮农举起了手上的白条子,声泪俱下,大声控诉。
“不还钱,就打死个狗日的。”粮农们群情激愤。
“上啊,打啊!”不知谁喊了一句。粮农们纷纷响应,潮水似地涌了上来,把李皇亲和几个保镖团团围住。拳头,口沫,耳光,窝心脚,一齐向李皇亲身上招呼。李皇亲左闪右避,无奈人太多,躲过了张三,避不过李四,被重重地踹倒在地上,一身狼藉,满脸血污。
艾米莉有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就像三伏天喝了冰水,心里爽得很。她等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真是老天开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世界上没有白得的财富,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是报应未到而已。
不知什么时候,李皇亲趁人不注意,从人的腿缝里钻了出来,挣起身子站了起来,一只手拿着一只踩烂了的朝靴,蓬着头,赤着脚,朝大家点了点头,憨憨地笑着说:“老子有的是钱,老子是天上的仙童转世!玉皇大帝是我的岳父,鸿钧老祖是我的亲爹。哼,你们敢打老子?老子上天去告你们。”
一时里,大家都惊呆了。看着李皇亲举着自己的一只朝靴,跌跌撞撞地向门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嚷嚷:“老子有的是钱,老子是天上的仙童转世!玉皇大帝是我的岳父,鸿钧老祖是我的亲爹。哼,你们敢打老子?老子上天告你们去。”
李皇亲疯了。
艾米莉看见李皇亲转过身,在阳光下越走越远。他身上的锦衣撕成了碎条条,红的红,绿的绿,色彩纷呈,就像一面面万国的旗帜,在风中招展。他裸露出的屁股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舞台上的追光,白得耀眼。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仙童两个字,就像一记重锤,重重地砸在艾米莉的心间。触动了她的情感,牵引着她的思绪。艾米莉本能地抬起了头,望向辽阔而蔚蓝的天空。仙童哥哥,你在天庭还好吗?过得幸不幸福?艾米莉又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