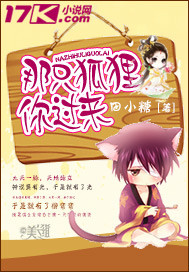人精之所以向白眉老翁自荐,愿意接替那个愤而辞职的先生,也是完全出于一片私心。他渴望有一个安稳歇脚的地方,他不想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凭自己的本事自食其力,与贼王这个名号彻底拜拜。
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教书使命光荣,可以洗白自己,赢得村民们的好感。更进一步的话,可以凭才华和自己的努力,考取举人,博取功名,谋一个晋身的阶梯,腰金衣紫,飞黄腾达。
说实话,人精不想做官,做官风是风光,但那只是表面,骨子里还得受上司、受繁文缛节的朿缚。可做官能完全洗白自己,达到并实现张友亮当初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与妮可夫唱妇随,一辈子永远在一起。在人精的意识里,只要妮可喜欢,他就喜欢。他愿意尽最大的努去博取,中举,从政,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人精在白眉老翁的指点下,去了一趟县城。县叫苍南县,不大,却很繁华。人精找到县衙里治学的官员,拿出自己的秀才文关,登记注册,换了去郡里考试的文关,一切还算顺利,人精仅仅给学官孝敬了二两碎银。
办好文关,人精回了一趟湾子村。然后,又去了一趟郡里。郡叫仁川郡,位于傲来国的最北端,山高皇帝远。在仁川郡,他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学官再三盘诘,故意刁难,说是异地不能在当地落籍,参考。没奈何,人精拿出了身上仅有的五两银子,学官还嫌少,硬是脱去了人精一件新买的青缎袍子,这才把学籍搞定。
苍南县在东边,仁川郡在西边,而湾子村介于苍南县和仁川郡之间。人精没了盘缠,不敢造次,只好徒步走回湾子村,又不想妙手空空,重操旧业,一路上只得风餐露宿,忍饥挨饿。
人精回到学馆,就着一碟酸盐菜,一碟咸萝卜条,一口气连吃了四大碗米饭,连喝了三大碗白米粥,就像囚徒刚刚逃出了饿牢,把白眉老翁也吓得不轻。
白眉老翁听人精诉说了原委,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自古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可如今,连学官都腐掉了,读书人斯文扫地。看来,傲来国真得出一代明君,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是很遥远的事情,与人精毫不相干,他也懒得去过问。他白天教书,晚上埋头苦学,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背得滚瓜烂熟,重点的地方还做了笔记。
白眉老翁旁听了几堂课,觉得人精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旁证博引,学识渊博,知识宽面,信息量大,深为折服。人精哩?白天备课讲学,晚上关起门来,如饥似渴地研读四书五经,一熬就是一个通宵。为了功名,他豁出去了。
好不容易等到九月二十八日秋闱,天下大考,人精备好墨砚纸笔,带了干粮和盘缠,踌躇满志地向仁川郡进发。考场设在一座关帝庙内,用竹木隔成了一小间,一人一间,设一桌一椅。关帝庙戒备森严,门口有枪兵把守。
人精分在二十八号。左边的二十七号是一个大胖子,挺胸凸肚,肥头大耳。右边的二十九号是一个穷酸秀才,衣服上缀着大补丁,年纪也不小了。
人精磨好墨,展开纸,考官一颁考题,他就笔走龙蛇地写了起来,才思泉涌,文不加点,一口气洋洋洒洒写了四千多字,又反复核对了一遍,感觉还可以,不觉有些洋洋得意。
做完题,离交卷的时间还早,人精有些闲得无聊,开始关注左右两个考生的动静。二十七号的胖子伏在桌子上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哈拉子流了一脸。二十九号的穷酸秀才咬着笔头,长吁短叹。他轻轻地敲着板壁,从壁缝里扔进来一个纸团。
人精四顾无人,用脚尖轻轻地把纸团勾了过来,捡在手里,拂开一看。原来是秀才在请教,策问中的润格是什么意思?一个连润格都拎不清的人,也想中举?人精莞尔一笑,把纸团揉了揉,放进嘴里,伸长脖子咽了下去。
让人精气炸肚皮、大跌眼镜的是:他和二十九号穷酸秀才都落第了,反倒是那个呼呼大睡的二十七号大胖子,叫高明举的,却高中榜首,成为仁川郡的第一名举人。
人精大惑不解,自己和穷酸秀才落第,也许是运气不佳,或才气不够。而那个压根就没拿过笔的胖子,却高中第一名举人,这会是什么原因?这其中一定有猫腻,有故事。
在租住的喜来登客栈,人精辗转反侧,一夜难眠,鸡叫头遍的时候,他索性换上了夜行衣服,翻出窗户,一路隐高伏低,向郡衙疾行而去。
郡衙建在一座山梁上,乌泱乌泱的一大片,人精飞身上了一棵柳树,身如流星似地一闪,跃上了高高的屋脊。
郡守的书斋里还亮着灯,门口守着两个正打瞌睡的衙役。郡守年纪不大,叫马奇,四十多岁左右,广额悬鼻,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相貌堂堂。看上去像一个清官。桌子旁恭恭敬敬站着两个学官,一个叫佟仁,一个叫陶俊,一正一副,一个瘦高个子,一个一身横肉。
“佟学官、陶学官,本郡交代的事办好了吗?”郡守翻着书,头也不抬地问。
“办好了,办好了。郡守大人的钧旨,卑职一定全力以赴,二十七号考生高明举已经中了本郡的第一名举人。”佟学官、陶学官唯唯诺诺,异口同声。
“很好,很好!这里有八根金条,你们每人四根,拿去买一杯酒喝。不瞒各位,高明举是我的亲外甥,无奈相貌堂堂,腹中空空,本郡只得出此下策,来个移花接木,瞒天过海。”郡守搀了搀胡须,满脸堆笑。
佟学官、陶学官小心翼翼地揣好金条,拱了拱手,答谢不已。临出门之际,陶学官良知未泯,斗胆说了几句。“郡守大人,那个叫人精的二十八号考生太冤了,卷子被人掉了包,还一无所知,我们是不是让他在第二榜也中个举?让真正的读书人有个晋身之阶?以不负孔孟之言。”
“大胆,放肆!我说不行就不行。”郡守狠狠地一拍桌子,怒目而视,把两个学官嚇得满头虚汗,心惊肉跳。
人精像一只蝙蝠,倒挂在屋檩上。郡守和两个学官的对话,他听得一字不漏,真真切切。原来自己名落孙山,竟是拜郡守和两个学官所赐,他们私欲薰天,财迷心窍,上演了一出移花接木的诡计,玷污了孔孟之道,寒了天下士子的心。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精身子一拧,身如陀螺似地旋转起来。他掣出腰上的鱼肠宝剑,匹练似地抖开,幻出千万朵剑花,电光火石地向郡守刺去,一剑直指眉心。人精舌绽春雷,大喊一声:“呔,狗官,看剑,纳命来!”
郡守吓破了胆,身体弹棉花似地抖个不停,一泡热尿禁不住流了出来,湿透了大半个裤裆,一个啊字还没喊出口。人精飕地一剑从眉心贯入,从后脑勺透出,一股热血夹杂着一些红红白白的脑浆,泉水似地从洞隙里涌出,一眨眼的功夫,就淋漓了大半个书房。
郡守四肢抽搐了一阵子,嘴里吐出了一串血泡,就寂然不动了。眼看着一命呜呼,魂归地府。
其时,佟学官和陶学官还未迈出门槛,他们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得不知所措。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争先恐后地往外逃,无奈关键时刻,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步步如同踩在棉花堆里。
人精抽出剑,迅捷如风地赶了上来,只一剑,从佟学官的脊背刺入,前胸透出。佟学官就像一只沉重的麻袋,仆倒在地上,揣在怀里的金条哐当一响,散了一地。
人精拔出剑,幻出一片剑花,势如长虹地刺向陶学官。不知是陶学官仗义执言打动了他,还是人精尚存一丝善念。手上的剑心随念转,滞了一下,剑锋偏了偏,从陶学官的小腹刺入,后背透出,刺穿了三根肋骨。
陶学官也不是一个怕死之人,闭目领死,连哼都没哼一声,双手捂住腹部,踉跄了几步,强撑着,始终没有倒下去。
郡衙里发生的血案,惊醒了两个正在打瞌睡的衙役,一个挺刀,一个持棍,一前一后地攻了上来。人精挥剑相迎,三个人斗在一起,刀剑相撞溅起的火花,把整个书房照得如同白昼。
两个衙役的功夫都不弱,棍沉刀疾,与人精旗鼓相当。人精不敢恋战,久则有变。他想找个机会脱身,无奈衙役们步步紧逼,寸步不离,刀和棍舞得就像一阵疾风。
糟糕透顶的是:书房里的打斗声,惊动了在院子里值守的衙役,衙役们一传十,十传百,都抄着家伙,明火执杖,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大叫抓贼啊抓贼!
人精明知不妙,也只有硬着头皮迎战,咬紧牙关,苦苦支撑。可能是气力透支,也可能是输了声势,人精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热汗淋漓,渐渐不支,脑子乱得像一钵浆糊。
两个衙役见有援军加入,信心倍增,愈战愈勇。人精斗也斗不过,跑也跑不了,心里暗暗叫苦。老天爷啊!想不到我人精英雄一世,一条命却丢在这里。再见了,妮可。罢了,大丈夫死则死矣,何惧之有?
人精舞着剑指东打西,状如疯虎。无奈双拳难敌四手,腿部、胯部先后被铁棍扫中,剧痛难忍。紧接着,他的头部也挨了重重一击,眼前一黑,金星四起,一个踉跄险些仆倒。
生死关头,一条黑影一片树叶似地,从一棵杨树上飘了下来,状如一只展翅的大鹏。一根细细的莹绿竹棍,点,挑,搠,摆,撞,疾如暴风骤雨,衙役们哼哼唧唧地倒下了一大片。
来人蒙着面,身手矫健,力大无比,像极了三弟地煞。人精精神一振,勇气倍增,手上的剑又利索起来。
人精正杀得性起,来人一把扯住他的胳膊,脚尖一点,飞身上了一棵大树,又纵身一跃,跳上了高高的屋脊。
就在这个时候,九门提督带着一队官兵赶来增援,他们拈弓搭箭,一阵铺天盖地的箭雨,射向院中的那棵大树,把个树干攒得像一只刺猬。
好险哪!人精吐了吐舌头,十分感激地看了蒙面人一眼。蒙面人爽朗地笑了笑,紧紧地握住了人精的手。
人精心里一热,涌起了一股暖流,喃喃呐呐地说:“地煞,我的好兄弟,谢谢你救了我!”
蒙面人不出声,友好地点了点头,拉着人精兔起鹘落,一路疾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