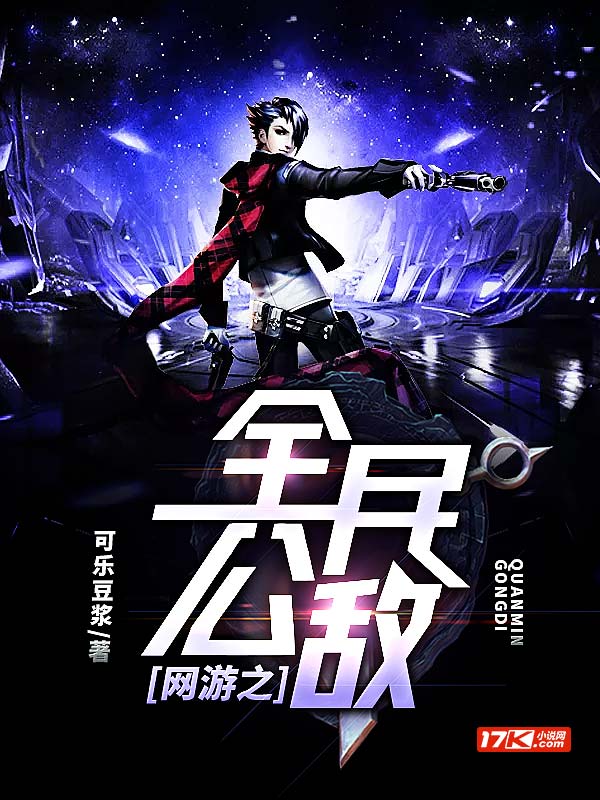二、父亲的青年时代
由于奶奶的早逝,尽管爷爷后来又续娶了妻,但是这个奶奶又是体弱多病,父亲姊妹三人基本上都是在他们的姑姑、姑父的照顾下成长的,等到父亲长大成人,他们又张罗着给父亲娶了一门亲事,也就是我的母亲进到家门。母亲来到这个家里同时也给家里增添了人气,她是本村南街刘家的三女儿,两个姐姐出门嫁人,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家境虽不算富裕也属于中等水平,进我们家门就帮着奶奶一起操劳家务,烧火做饭、洗锅刷碗、洗衣磨面、缝补衣衫样样都做,当然也是跟着奶奶一边学一边做,过门四年后母亲给家里添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哥哥。都说老生儿子长孙子,是老人的命根子,我哥哥确实也是家里的宝贝疙瘩,取名申宪民。1958年公司合营,家里的买卖不能做了,所有的财产、土地全部归人民公社,由于家里爷爷积攒的财产都买了土地,导致土改时根据土地多少我们家被定为中农,六四年四清时村里有人想要给我们家定富农,三榜定案我们家最终给定了一个上中农,**后又恢复土改成份,我们家又改成了中农了。当时在农村,成分高低就是一个人的名片,成分高了大家都看不起,贫下中农才是最吃香的,无论是上学、找工作、还是出门办事,贫下中农就是拥有各种优越待遇。好在公私合营父亲被安排在村里供销社当了一名营业员,由于从小在家帮着爷爷做生意得到的炼厉,待人接物、迎来送往不在话下,父亲在供销社工作很出色,经常得到领导表彰和广大群众的赞扬。
1955年朝鲜战争前线需要补充兵源,村里的干部力推我的父亲应征,我爷爷和老姑父百般请求,并承诺出一千块大洋,但是丝毫也没有任何效果,甚至那村干部为了让父亲参军把自己儿子也带上送到部队(但是人家到广府就偷偷的跑回去了)。父亲只能舍弃一大家老小应征入伍,老姑、奶奶和我的母亲以及年仅三岁的孩子(哥哥)哭的死去活来,爷爷和老姑父不甘心,步行从大北汪赶到永年广府,那时候广府是永年县城足有四五十里。但是当他们赶到哪儿,应征的队伍已经开拔,人家告诉他们部队已经去黄粱梦坐火车了。爷爷和老姑父顾不上旅途疲惫,又向黄粱梦火车站奔去,他们就是想看一眼自己的孩子,但是当他们又从广府步行赶到了黄粱梦的时候,天色已黑,火车早已开走,疲惫、失望和饥饿把两个男子汉彻底打垮,他们面对着火车开走的方向大声的呼喊父亲的名字,我的爷爷:这条14岁就失去父母双亲,不到三十又丧妻的硬汉子,这时候蹲在地下嚎啕大哭起来。就这样父亲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人。离开疼爱他的姑姑、姑父还有二大爷,离开老爹、后娘,离开尚未成年的妹妹、弟弟,还有刚过门没几年的媳妇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从此父亲参军成为了名军人,服役于石家庄27军司令部警卫连,成为一名警卫战士,为司令部站岗放哨。有一天连长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去北京给正在北京党校学习的军长傅崇碧送工资,我父亲第一次去北京,公交车路过天安门广场,他看到了天安门城楼,和悬挂着的毛**巨幅画像,内心充满着无限的敬仰和向往。当他把工资交给傅军长的时候,军长看他眉清目秀,言谈得体,甚是喜欢,当他得知面前的这个小伙子还读过几年书的时候就说:“你愿意留在我身边来司令部做我的文秘吗?”父亲礼貌的回答:“这事我做不了主,您得跟我们连长说。”就这样等父亲回到连部,很快就得到连长的指令,让他去司令部报到给傅崇碧当文秘,从此他的办公室就在司令部了,一个三间大的屋子里,军长在里间,他在外间,外间也是会议室、接待室,有个很大的会议桌,旁边是他自己的办公桌,桌上放着好几部电话机和近期各大报纸,父亲平时就是接电话,接收中央文件、给军长读文件、报纸,重要的内容则需要摘抄下来。几年的文秘工作父亲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由于他各方面优秀、表现出色,多次受到嘉奖,所以很快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光荣的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58随着部队改革,从士兵里提干制度取消,改为由军官学校培养军官,父亲的军旅生涯也到了尽头。是时北京有个科研单位新成立,需要从各大院校、各地科研单位和转业军人中配备工作人员,傅军长征求他意见问他愿意不愿意去北京工作,父亲写信给爷爷商量,当时家乡正遇******,村村寨寨闹饥荒,本来盼子心切爷爷这时看到家乡的人们都饥不果腹,爷爷果断的回复:去吧!北京是个好地方,是党中央、毛**待的地方,应该饿不着肚子,总比回家跟我们一起饿肚子强。就这样父亲回了趟家告别父老妻小踏上了北京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