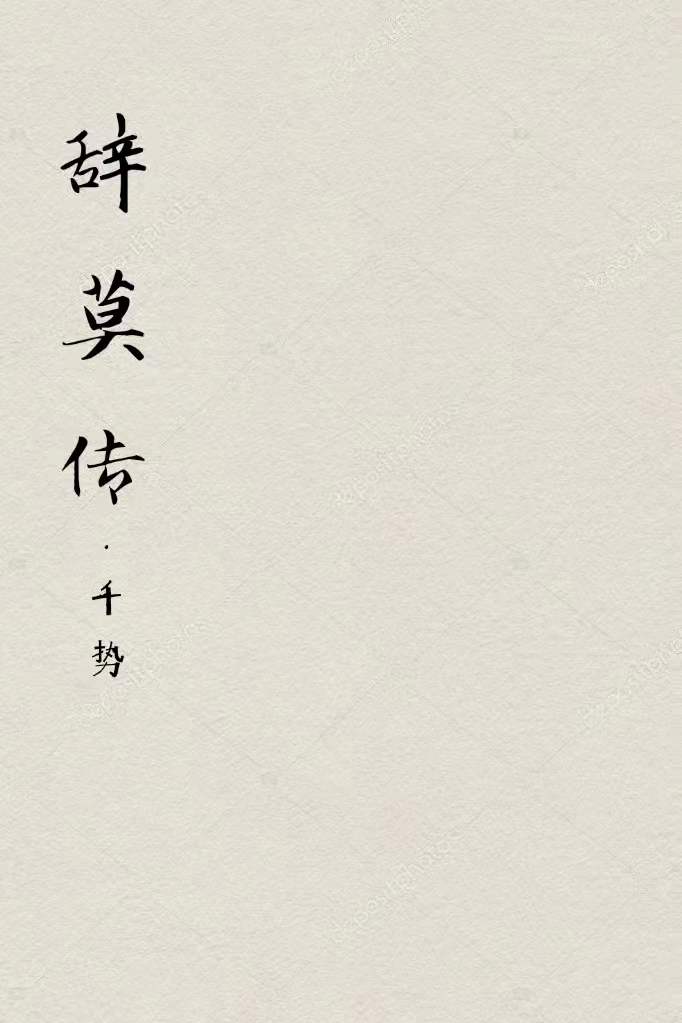苍白的闪电划破天际,照亮了乌云密布的天空。
雷鸣滚滚,暴雨倾盆,豆大的雨滴在地面上轰炸,满是泥泞的道路上,两条车辙印正在一路延伸。
用麦秆充当的挡雨布下,是被斩去双腿,切去手掌的尼萨,被掏空脏器的肚子里尽是塞满的麦秆…
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给坞维尔老先生一个交代,在场的二人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尽可能的整理仪容,抚平他死不瞑目的双眼。
在瓢泼大雨下,仅剩下可以做的几件事里,首要的便是把让尸体不再有损伤的带回去,等雨停后通知警卫厅…
凶手能够将像尼萨那样的魁梧男子虐杀,在他极有可能没有走远的情况下,诗人选择了带瑞赶紧离开这里。
车轮在泥泞中翻滚,捡起的泥水弄脏了两人的裤腿,雨势大的让人睁不开眼,雨水像溪流从山岭的缝隙里透下一样顺着头顶往下流淌。
暴雨之中,恐惧之余,瑞紧闭双眼将眼泪和雨水挤出眼眶,再睁开,默念一声:
“对不起……”
—[月食屋]饭店内—
“谢谢,艾尔,水温很合适。”
饭店二楼的阁楼,暖色调的窗帘把雷雨声隔绝在外,安详的室内只有水流哗啦啦的轻响,面容慈祥的老奶奶坐在椅子上,脚尖点触着脚下的木盆,慢慢插进水里。
“嗯,那梅菉奶奶我先去看店了,一会儿再来。”
提着水壶,艾尔走到了楼梯口,老奶奶又想到了什么出声说,不好意思的开口,
“艾尔,今天的报刊我还没看,可以帮我拿上来吗?”
“好的梅菉奶奶,我这就去!”
扯着尚且带有稚气的嗓音大声应答,艾尔踢踏着脚从楼梯上“咚咚咚”赶下楼,脚步的余声消失,老奶奶捧着脸躺到椅子靠背上。
“艾尔还是那么的懂事啊。今天雨下的那么大也真是少见,我连报刊都快忘了读。”
艾尔跑下楼,重新装水在炉子上架起了水壶后,赶到了饭店的前台。
“阿嚏!”
走到用餐的大厅,只有几盏油灯在发挥着光与热,雨声格外的大,百叶窗阻隔着雨水,屋外时不时的电闪雷鸣,寒冷也渗入肌肤,让艾尔打了个喷嚏。
饭店里只有艾尔和老老奶奶是常住人口,其他员工早在暴雨的前兆下就匆匆回家,艾尔在店里照顾着老奶奶的起居,气候变化无常,这才中午,天空乌云密布的就已经给人感觉到了晚上。
揉揉鼻子,艾尔提起前台桌上的油灯照亮周围的桌椅,小心的走到门口。
一开门,雨滴被风吹着闯进屋里,艾尔手一伸出门口就被立刻打湿。
手勉强够到门口的信箱以后,艾尔伸进去摸到了一卷纸,这就是今日的报刊了。
拿到报刊,艾尔飞快抽出手把报刊收进屋里,这时,艾尔的小半片身子都变得湿漉漉的,他赶紧把手里沾水的报刊放到桌上,用桌布小心的吸了吸水。
看到报刊上的字迹没有花太多,艾尔打算关门上楼时,无意间向门外一瞥,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骑士?”
——
瑞和诗人急匆匆的推着车回到坞维尔家宅,但是站在屋外,谁也没有去敲响那扇门。
在屋外的暴雨中,瑞的衣领被水所压垮,斜斜的倒在肩上,诗人的帽子也被雨水冲的发生了变形,现在他们身上的衣服湿的可以挤出桶水,身体也仿佛吸水了一样变得沉重,最后,还是吟游诗人抓着帽子,迟疑的叩响了大门…
“外面下着大雨,你们终于回来了,快进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父亲他…”
凯尔·坞维尔打开门,见到两人马上笑着打开门让路,但是诗人意外的沉默也没有动作,凯尔意识到了不对劲,
“有…其他事吗?”
诗人深呼吸了两回,但还是没有把话吐出来,而是和瑞一起站到了门边,把身后又一位丧命的兄长揭示在了至亲兄弟眼前。
屋内的空气也变得冰冷了,与屋外如出一辙。
——
“砰”
听到新的噩耗,坞维尔老先生本以有所好转的身体再一次崩溃,
“我的…我的……尼萨啊……呕!”
茶碗摔碎,扛不住压力的坞维尔老先生吐出一口鲜血,凯尔坐在床头,眼角闪着泪光的给他顺气,让他在床上躺好,但老人挥舞着手就是不肯乖乖就范,
“是谁!要害我的孩子们呐……啊啊…啊啊……”
痛恨的捶打床单,老人嗷叫着,气息断断续续,
“布鲁!尼萨!你们不能走啊——”
老先生已经开始胡言乱语,在连续两次的巨大打击下,他精神失常了,仅剩的小儿子凯尔也流下了两行热泪,
“爸爸…你快好好休息吧…我去给你拿药。”
说着,抹一把眼泪,凯尔打算出去煎药。
“不要!你别走!乖,凯尔,就待在我身边…不要走……”
见凯尔要离开床头,受刺激的老先生马上身子一扭,上半身悬在床边,抓住了凯尔的手臂,恳求着他留下来。
老人被泪水洗涤的脸在烛光的照耀下,悲伤而无助,好像一甩手就可以被打碎一样,凯尔眼眶又湿了,马上在床头坐下,紧紧握着自己父亲的手,搀扶着他在床上躺好。
“我就在这陪着你。”
“好…好啊……”
虚弱的回答让人心痛,卧室外,诗人与瑞坐在客厅,进去一起向老人证实噩梦的真实性未免太过残酷。
早上还色香俱佳的丰盛大餐到现在也没有人动,早已冷成了冻块,桌边突兀的放着尼萨·坞维尔的尸体,下身和手腕血肉模糊的切口还在渗出点点血渍。
用干净的布头盖上了死者的遗容,坐在椅子上的诗人依然抓着帽子,眼神里是抑制着的悲伤,卧室的谈话一字不落都传进耳朵里,更加深了沉重的氛围。
诗人很感性,可以为一个陌生人的逝世表现出溢于言表的悲伤,已经做了很久了,他浑身湿透了的衣服在一点点被壁炉烘干,眼睛里却一直没有恢复与瑞交谈时的那种热情。
如果诗人不是一个虚伪到极点的人,那么他就拥有着博爱的品质。
瑞:真希望你是后者啊,神烦。
于瑞而言,一前一后死去的两个人和瑞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甚至瑞刚来时还差点打爆了他的狗头,即使是到后来的误解消失,短短一个晚上的态度转变依然没有让瑞对他们产生深刻的情谊,但是瑞是一个人,他有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思想,距离的拉近即使语言不通也让瑞在陌生的世界里感到些许安心。
而死亡让人离开的同时也撕扯着瑞来到异世界时心里积攒的安心。
自发现尼萨·坞维尔死亡后,瑞闭上眼睛都是围墙上爬动的黑色身影,凶手会是他吗?为什么要那么做?自己如果留下来久一点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这种彷徨纠缠着他,瑞从来没有与一场真实的凶杀这么近过。
瑞看向死去的尼萨·坞维尔,白布遮蔽着不堪的尸身,瑞也像诗人一样垂首。
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奇幻,我希望你的灵魂能够安息。
沉默良久,瑞伸手摸向胸口,如果这个世界就如书籍所言,充斥着奇幻与魔法,那么我是不是还有回家都可能?
那条挂坠是我唯一的念想了…还没来得及和太多人说声谢谢……
闭上眼睛,瑞嘴角微不可查的上扬,手在胸口摸索了半天…
咦?挂坠呢?
最后瑞锁着眉头,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上下摸索,胸口空荡荡的,哪还有挂坠的影子。
诗人疑惑的侧过头去,看见瑞站起来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衣装以后就捂着胸皱眉,
“是不舒服吗?”
瑞的手在胸前虚握,心里焦虑不安,自己真的是太大意了!
挂坠是我的生命,是我过去生活的证明!
眼神灼灼的巡视屋里一圈,没看到任何的雨具,火急火燎的瑞干脆就在壁炉旁的柴火堆里翻找出一块木板,头顶着它拉开了屋门。
“嗯?骑士你去哪?”
马上注意到瑞要出门,诗人也走到门口,雨吹到了他的脸上,
“外面现在雨很大…”
虽然说称呼瑞为骑士很大程度上是诗人的一时兴起,只因瑞的气质脱颖而出且品格端正。
在诗人的眼光里,瑞可谓是个正义感十足,能够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路人追击小偷几条街的正人君子;也是一个安静斯文,善于倾听诗人自己喋喋不休的优秀听众;同时还是品格端正到能够在深陷误解之时,还能够一心向光的谅解他人的好好先生。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异域气质的男子,很快在诗人的标签里就又要多出一个了。
瑞早就料到诗人要出来搭道,于是拿着顺手从炉边拿的木炭在木板上写——我出去一趟,你留在这,马上回来。
抱着板给诗人看了一眼后,紧了紧衣服,瑞就走进了暴雨中。
麦子地,那里可是凶杀现场,这时候去是打算冒雨追查真凶的踪迹吗?
“等等!外面的雨还很大。”
诗人想跟上去,但是脚步一迈出屋门又停住了,他与瑞眼神交触,瑞眼中有一种另类的光彩,那对他来说很重要。
诗人凌乱的头发滴着水珠,视线穿过金色的头发透进瑞的眼睛里,收回脚,
“我知道了,我留在这。”
——瑞出门了。
走在这样的大雨下,一块木板还是显得形同虚设,该淋一个不落,照样把瑞淋成了落汤鸡,瑞索性也就把木板丢到了路边。
照这个淋雨进度,不早点风干的话,我明天就会发烧吧?
脑袋里虽然这么想,但对挂坠的执着胜过了对身体状态的担忧,他要回到居民街后的那片田野,找回象征着自己过去的挂坠。
拒绝了随行的神烦,瑞觉得大雨天找小物件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还是他一个人来就好了。
神烦真的帮了自己很多了,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
镇子的石砖路面铺到林子边上就停止了,瑞重新蹚着比刚刚还要泥泞不堪的路面穿过林中的小路,路面上掉落的鸟羽都被雨水冲刷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坨又一坨的烂泥,稍有不慎就会摔成泥人。
不过身上本来就很脏的瑞已经不在乎了,到了麦子地上的斜坡甚至直接用屁股着地用滑滑梯的方式一路滑到田埂上。
瑞走过一处处自己经过的地方,麦子地里的那个奇怪足迹已经在水的洗礼下消失不见,瑞走过那片泥地,在发现尼萨尸体的地方站住脚。
被凶手拿来固定尼萨的木桩依然插在这里,瑞在木桩下找到了自己的挂坠,和它一起的,还有一块未完全消失的泥印。
失而复得的瑞满心欢喜的捧起挂坠,坠子上的流苏被泥水浸透,脏兮兮的,瑞丝毫不介意,把它视若珍宝的放在了衣服的内衬里。
这下就不会弄丢了。
长舒出口气,瑞瞥见了脚边的泥印,依稀勾勒出一个奇怪的脚印,瑞站在脚掌所朝方向的对立面。
转头,是从围墙那个方向过来的…
很难想象,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自己,这时候居然萌生出要去找一个变态杀人犯的痕迹,是出于自己与还活着的尼萨擦肩而过的愧疚?还出于自己对于恶徒的愤怒?
可能是,也可能都不是。
在这个没有一点归属感的世界里,瑞对着人或笑或哭都覆盖着一层虚假的表象,与其随波逐流,也许自己更爱在人生的另一个开端来场不一样的冒险。
虽然只是一个借口,不过瑞还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
去看看吧,也许能发现不可思议的东西。
从田埂到围墙,瑞的鞋里都要被泥水灌满了,每一脚都像是在拎一包泥浆。
在靠近墙脚后,瑞查看了一下那个自己当初看到爬动黑影的位置,确实又疑似钩爪刮损墙壁的痕迹。
好不容易走到围墙下面的遮雨棚下,瑞第一件事就是靠着墙把护胫里的泥水倒出来。
脱下护胫,甩着水,瑞看到了地上散乱的武器,矛和剑躺在湿滑的地面上无人收拾,有些不太寻常,墙缝里的色调也感觉怪怪的。
捡起武器,瑞依稀发现了一些污渍,不过污渍太小,碰水后一经触碰就马上消失,瑞也不能确定这是什么。
观察…观察…侦探都是时刻保持细致入微的洞察力才能找出罪犯的。
再伸手去摸墙缝,入手黏糊糊的感觉,瑞马上抽回手,黑色的黏稠液体与手指之间拉出了一条诡异的细丝。
应该不会是血吧?
瑞搓了搓手指上的液体,把手指拉近,鼻子嗅了嗅。
这…不太像是血……闻着也没有什么刺激性的味道…
可能是鼻盲缘故,瑞不太闻得出来是什么。
我离侦探的道路果然还很遥远……
围墙下面还有一条漆黑小道,阶梯弯曲着一路向上,顺着它应该就可以到城墙上面去,瑞如此猜测。
那么这样的话围墙上面应该也有士兵才对。
这个想法一出现,围墙上爬动的黑影又从脑海里闪过,瑞不寒而栗。
难道…不会吧…难道说……
害怕归害怕,对于人生重开一次的瑞,这还不足以让他退缩,瑞打算走上楼梯看看。
外面的暴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欲望,乌云盖顶,雨点拍打在遮雨棚上,雨水像瀑布般哗啦啦的从棚上流下,缺乏光线的楼道里,一片乌漆麻黑。
瑞眯着眼睛,一脸凝重,他,坚定的向前迈出一步…随即马上拐弯左顾右盼的在角落里找到了一盏提灯和一盒火柴~
“呼…在杀人犯可能待过的地方怎么可以疏忽大意呢。”
瑞拿着提灯到光亮处,刚要抽出火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之处。
提灯外壁上有被燃烧过的痕迹,并且……
瑞手指刮了刮灼烧痕迹周围的黑色斑块,摸了摸,也是黏黏的,气味也和墙缝里的不明物质如出一辙。
脑神经狂跳,瑞的直觉在告诉他,不要尝试去点燃提灯,不然会有非常不妙的事情发生。
“还是点点试试看吧。”
直觉总是这样,和本人意愿反着来。(或者应该反过来说)
瑞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毕竟人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有直觉提示自己的,连穿越这种操蛋的事情都发生了为什么不信一回直觉呢?
嘛~强烈的好奇心掌握着人体行动的最高等级权限。
瑞后退两步,划开了一根火柴,正要凑过去点灯,心跳无故加快了一下,直觉变的更强烈了,瑞歪头想了想,还是又往后退了两步,小心翼翼的把快燃尽的火柴丢进打开的提灯里。
火柴轻飘飘离手的那一霎那,瑞暗自腹诽,又犯蠢了!点灯应该去点灯芯啊,这样怎么点的着!
不过现实马上给了他一耳光,火柴甚至都没碰到提灯里的灯芯就忽的产生了巨大的火光,炽热的火花原地盛开,绽放时那些许芳华距离瑞仅咫尺之遥。
瑞骇然,仰着身子哆嗦着大步不断的后退,火焰只持续了两秒便骤然熄灭,只有被烧的更焦的提灯和提灯边上燃着的一撮小火。
火焰在黏糊糊的粘液上燃烧,跟着粘液滴落到地上,发出呲呲的声响。
靠在墙上,瑞缓慢的摸上自己的脸颊,刚刚的事就好像是错觉,可是那卷过面庞的火舌如此真实,他何其庆幸自己的直觉拯救了自己一命。
那是非常可怕的热量,被这火烧过一遍以后,地面上都被蒸腾出一层水汽。
瑞迟疑着重新靠近那盏提灯,围着它转了几圈仔细观察下,发现黑色的粘液消失了,只有黑乎乎的碳粉。
火焰结束后粘液就消失了,最后的小火苗也是在粘液所在的外壁继续燃烧,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黑色的粘液其实是一种类似汽油的黑色燃料?
虽然很像,但是没有那种刺激性的气味,相比焦油入手也非常容易被洗掉。
看着伸出手淋了片刻雨后就干净的手指,瑞这么想。
但是这种粘液的危险性不言而喻,重新看了眼提灯,担心楼道里可能也存在着这种粘液,为了避免点燃招致生命危险,瑞还是选择了摸黑爬楼。
当瑞在黑暗中走上台阶,外面雨点的轰响似乎也被隔绝世外,一路向上,只听到水滴的滴答声,脚下的奇异触感也让人在意。
摸着黑扶墙,明明响着水滴声,墙壁却干燥异常。
楼梯走完还有一条额外的梯子,连接着一个小窗口,瑞顺着梯子往上,
“哐啷”
顶开木质小天窗,瑞探出头,眼睛脱离黑暗瞬间,眼睛瞪大,瑞浑身肌肉抽搐,抓着窗口的手一阵颤抖。
围墙上,乌黑的砖瓦,融化的铠甲,裂开的骨头,数具死尸横七竖八的以各种怪异姿势靠墙倒下。
雨水冲刷着僵硬的残骸,再从骸骨的漏洞中流出,铁质的头盔划开在头部,变成了勾勒出死者生前面容的铁面具,持有的武器看不出原样,少数的铠甲碎片以撕裂状散落在地,这幅场面给了瑞穿越以来最强的精神冲击。
顶着猛烈的雨势,瑞爬出窗口走到围墙上,每一具尸体都看了过去,他们无一例外身上都有着黑色的附着痕迹,且都面朝着瑞当前站着的位置。
眼睛向下看,瑞见到了一枚踩裂了地砖的脚掌印,形状与麦田里如出一辙。
一段连续性的画面出现在瑞的眼前,当一个可疑的身影突兀的出现在围墙上,所有人都尝试阻止他,但是都在黑色液体助燃的火势下死于非命。
围墙上的士兵知道了结果,那么,围墙下的人又在哪里?
带着这个疑惑,瑞拉开窗口,打算回去,天空一道闪电划过,映衬出了黑暗里痛苦的灵魂。
瑞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在黑暗中听到的滴答声就是尸体被放血后持续不断的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