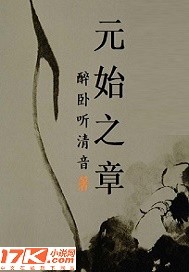卸下斗篷;头戴束发金冠,身穿紫罗袍的安平王单勉嘴角挂上了一丝怪异的微笑,其人似乎是刻意紧了紧自己的袖口,随后便从腰间的金质如意勾上摘下了那柄谢观星已然见过一次的宝剑。
显然是看清了安平王的这一举动,围绕一旁的禁军军士无不倒吸一口凉气,同时向后退出了数步。也许对于王哈儿那样的角色来说,一个比宫中的太监强不了多少的皇子无需太过在意,但这些寻常军士却明白的很,自己可没有涉川二品以上的官职,更没有像某位京中红人那样威风八面的岳丈,若是被这安平王平白砍上一剑,那当真是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见!
看到一众军士后退,那个领兵来此的百人尉眉角微不可察的向上挑了一下,其人似是嘟囔了一句,随即翻身下马,单膝跪地拳击左胸高声致歉。
“小的成怀素,乃京都提卫周大人制下百人尉,今日奉命来此,实不知安平王爷大驾躬亲,属下未能及时远迎参拜,还望王爷勿怪。”
单勉手持配剑,远远望了那名百人尉一眼,忽然笑道:“周谨的人?因何我从未见过你,如此巧言,怎地才是个百人尉?你此番带兵前来所为何事?如此兴师动众莫不是存了旁的什么打算?”
那百人尉闻言,面上堆笑,却并不打算靠近言语。其人再施重礼后朗声说道:“小的职司低微,入不得周将军大帐,王爷自然不识。此番前来,只是从得将令,京都宵禁一刻不止,五柳巷衙内人等不得擅自离开。属下依令行事,并无旁的意思!”
安平王单勉闻言眼眉倒竖,发出一阵渗人心肺的冷笑。
“既如此,取将令我看!”
那百人尉面色微微有些发白,可言语却不见丝毫退让。
“王爷和我家将军交情莫逆,应当知道军中的规矩,若王爷执意要查证将令,还请出示兵马司的令牌!若无令牌,圣上手谕亦可!可若无此二物,请恕小的斗胆不从,小的及所属部众的身家性命全在王爷您一念之间,还请王爷三思!”
此等“用心”言语,确实触动了考虑问题与旁人多少有些不同的安平王单勉,其人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禁军军士,忽然发觉,那些原本已经有些垂下去的刀枪,此刻又有了抬头的意思。
看着那一双双默默盯着自己的眼睛,安平王单勉的心中忽然涌起了一丝悲意,可这几年生不如死的清冷境遇,让单勉早就学会了如何掩饰自己的情绪。
转身迈入官衙,单勉将手中宝剑随手抛到那个还站在门边发呆的五柳巷总推官方胜怀中,头也不回的说道:“既如此,本王不为难你便是,来日若是见到你家将军,本王会替你说上两句,如此心志,只做个百人尉,可惜了!”
眼见着安平王单勉和那名总捕进入官衙,门外的军士无不暗松了口气,可就在那官衙的大门行将关闭之时,门内却再次传出单勉的言语。
“将此剑悬于门眉之上,我倒是要看看,一个没了卵蛋的王爷能有多大的用处!”
……
“切!不过是个过气的王爷,要是没了那把宝剑,倒有个甚用!只怕此番事了,这剑也要被人收了回去。”
一名十人尉悄悄凑近了自己的上官,边抹着额头冷汗边小声说道。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名十人尉半晌都不见自己上官有任何答复,其人不免有些纳闷,忙抬头去看,可这一看之下,这名十人尉当即愣住,方才还振振有词的百人尉成怀素,此刻却面色阴沉眼露凶光。
“大人这是怎地了?即便这安平王爷是个废人,可若是能为大人您说上两句好话,周将军那里怎会不给些面子,属下倒是要恭喜大人了,大人何以是当下这副表情?”
那百人尉闻言狠狠瞪了这十人尉一眼,随即扭头看向远处说道:“你等倒是懂个屁,若是他不说,消息传过去,或许真能逃过一劫,可要是他去说,你就等着给本大人准备棺材吧!”
且不论官衙外是何种状况,那百人尉手中的将令上又究竟写着什么?安平王和谢观星的到来,便如同给衙内的众公人服食了一味强心壮胆的猛药,众人面带欣喜上前施礼。此时此刻,安平王便是所有人的救星,而那个能请来安平王的谢观星,毫无疑问是个有着天大本事的奇人,就连喜滋滋跑出门去悬挂宝剑的方胜,也受到了所有新人的再次礼遇,那剑不抛给旁人,却独独抛给了总推官大人,哪有不上前恭维两句的道理?
说起来,这当真是件玄妙的事情,以五柳巷官衙当下的状况,请谁来能比这安平王更为合适?官做得久了,哪个不懂得趋利避害?更何况这周谨是什么人?京都提卫!其人行止那代表的就是圣意,能跟圣意对着干的,涉川之内自然没有几人,可要是能和“老子”对着干的,最合适的莫过于那些受过委屈,又一点好处都没落下的“儿子”。
众人的猜测,无疑有他的道理,可知道内情的谢观星却恨不能将这安平王一脚从官衙内踹出去,这一切的起因很复杂,需要从谢观星回返家中一事说起。
离开方胜之后,谢观星急于赶回家中,他必须提前安置柳如烟前往诸子巷,有了自己岳父大人和诸子巷街坊邻里的照应,谢观星当能放心不少,就算真的有事,诸子巷那里还有一条偏僻小道直通刘公祠。这逃命逃出得路径,难免要翻过一两处断墙残房,出于好奇,柳如烟曾经跟随谢观星走过两次,自然识得其中路径,可要是换了旁人,只怕先要到老君村历练一番方可寻到出口。
可就在谢观星将将看到自家院落,从街角暗处却是传来了一声轻微言语。
“大人慢行,……有一事相告。”
这声音压得极低,人又藏在阴暗角落,即便是谢观星也没有完全听清,可当谢观星手压刀柄靠近之后,这人身上的装束以及那张熟悉的面孔让其人放松了握住刀柄的右手。
“小武,你方才去了何处?出了这大的事情,怎地也不打声招呼?”出于谨慎,谢观星仔细留意了一下周围的动静这才小声问道。
那出声之人正是五柳巷官衙新任捕头小武,只是此刻这少年全然没了往日的精干振作,只是于黑暗中,一脸无奈的看了谢观星半晌后,这才小声说道:“大人无需担心,小武方才留意过,四十步内再无旁人。大人戴小武不薄,小武便是要走也需给大人打个招呼,官衙那里大人还是莫要去了,小武想了许久,有样东西交给谁都不妥贴,还是交给大人您稳当。小武左右是要离开京都,不想再欺瞒大人,小武原是宫里的人,只是上官暴死,故而没了联络。如今小武摊上是非,此物无人敢收,只能交给大人,大人是毁去此物也好,留下此物来日做个佐证也好,都和小武再无关联,小武不敢耽搁,就此告辞,还请大人自己珍重!”
言罢,那小武将手中的一样物什塞入谢观星掌中,随即便再次隐入阴影当中。谢观星被小武这番言语说得莫名奇妙,连忙上前想要阻止,可贴近所见却不过是一面黑漆漆的墙壁,那看似没有多大本事的小武,在转瞬间便消失的无影无踪。
早已被打击到麻木的谢观星这次倒是没有感到意外,自己过去眼界尚浅,难免在有了些本事后扬扬自得,可这段日子以来,高手层出,谢观星已然看清了自己和那些江湖人物之间的差距。即便这小武有些来头,和那些高手相比却也不足为奇,要像小武这样遁走,谢观星自问,若在此处一样可以办到,只不过小武尚比自己小上两岁,便能藏的如此之深,又有这般本事,当真让谢观星感到有些钦佩。
“是什么东西让小武恐惧至此,定要逃离京都?”谢观星困惑之余,将手掌中的那件物什举到了面前。
一阵腥臊之气扑面而来,谢观星眉头立时皱起,其人多少有些动怒,羞愤之下,忍不住便要将这盘在一起的物什撇将出去。
“这小武可是疯了,寻了条女子的羞布来作甚?可是想临走前消遣我谢观星?”谢观星已为人夫,自然识得这掌中是个什么物什,但就在那羞布将要出手之时,指甲的一点轻微感觉让谢观星改变了主意。
接着微弱的月光,谢观星忍住咯应,将那羞布张开来仔细搜索了一番,很快,一张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做成的薄片就被谢观星从那片有些恶心人的羞布中抽了出来。
这薄片轻薄坚韧,上面依稀写有文字,只是这文字再次让谢观星看傻了眼,怎地这方胜认得昌余文,小武也认得,偏偏自己不认得,既然如此,那此事只得先放上一放,左右寻到方胜在做打算。
犹豫片刻,谢观星将那薄片连同羞布一起揣入怀内,小武方才言语中的一些暗示,让谢观星多少有些担心官衙那边的状况。
其人略做考虑,还是决定先提醒柳如烟一声后,再即刻返回官衙,可就当谢观星到了自己院落门口,却看到了令他完全不敢相信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