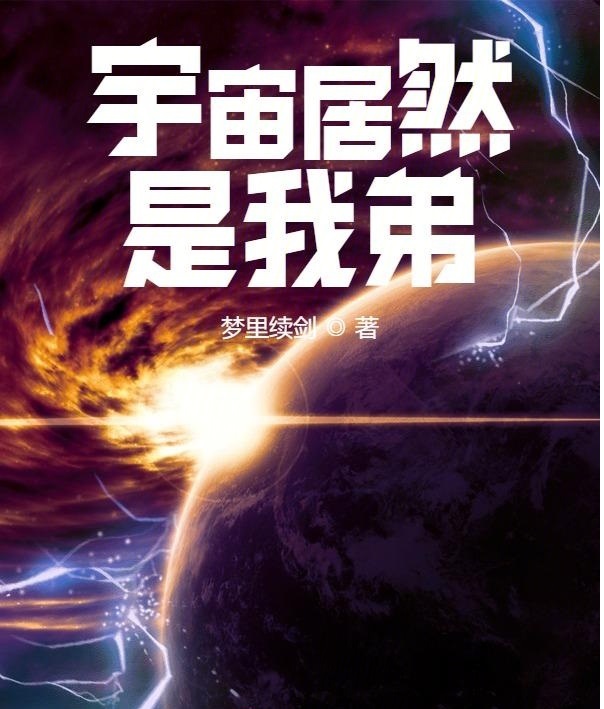时间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左右,那时候的东凰山还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乡村,而非像现在这样的山被房子挡死了,河也被杂物给搅浑了。风和日丽的某一天,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管它呢,反正乡下人都得一律地做活,只有稍微清闲的时候,才发现头顶的太阳总是那样温柔遍照,只是有时光线略略刺目了些罢,风也就那么细细地吹,带着幽微的草木气息。
就在这难得的清闲中,屋前河水潺缓,夹岸翠枝摇曳,层层漾去的水波上,跳跃着无数灿烂的金色小精灵。水面时不时会浮动起几个气泡来,继而一个男青年便利利落落地从水下抬起身子,扬起几朵清凉的水花。青年的手里总会抓着鱼,宽大的骨架上附着线条分明的匀称的筋肉;两眼虽被水花润得微红,却仍闪动着澄澈的光芒,在迷离的树影下同挂着水珠的圆溜溜的鱼眼睛对视。
“春来,又一条了,装好!”青年冲岸上的刘春来喊道。
“这也不大呀,胡枫,我看你还是上来歇歇吧,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候,晚上指不定还有什么活呢!”刘春来翻了翻小竹筐里尽是些手指大小的小鱼,“这是不会有人要的。”
眼前这个青年就叫胡枫,是东凰山一个生产队的队长。现在他之所以能不知疲倦地泡在水里,并不是为着捕鱼贴补家用,而是因为他对瞬息万变的水上世界的热忱;他总觉得将来要是有机会,他还会乘着大船出海,在海上住一段时间,等他载着许许多多稀奇的鱼回来时,码头上翘首以盼的乡亲们会是一片欢腾,大家就都幸福起来了。
“小点就小点呗,留着给你和阿娟烤着吃――听说阿娟都有喜了?”他说道。
“这也就在嘴里含个味,”刘春来笑道,“别整这些没用的活了,上来躺一会儿。等会儿你沉下去了我可没力气爬起来捞你。”
“你是不是以为我抓不到大的鱼啊?等我攒足了这口气,潜下去久一点儿抓给你――看啊,给我数着。”
胡枫正捏了鼻子准备伏下身去,只听见桥头传来有人招呼着下田的声音。胡枫随即溜上岸来穿好外衣,一面用脚拨了拨迷迷糊糊睡去了的刘春来的腿:“欸春来,起来养媳妇了!”
胡枫大步流星地来到田里,见爹已经挑了两桶水走在田埂上,他连忙赶上去接下担子,抓起那支在长竹竿尾部穿个破桶便制得的水勺开始浇田。
爹背转过身子去捆那在田里零零星星地散成一摞一摞的秸秆,但仿佛背后长了双眼睛盯着胡枫似的,因为他说:“你这头发和衣服怎么又是湿的?刚刚是又下水了?”
胡枫一愣,瞟了爹一眼,见他仍弓着背在用手拢着秸秆像只是随口一提,于是默默不做声。
“就离开田里那么一会儿,至于么?”爹知道胡枫在听,继续说,“晚上可别累得一回去倒头就睡,家里会来客人。”
“客人?咱家还有什么客人我没见过?还非要我回家去。”胡枫果然发问了。
“不是亲戚,是你娘的相识。”爹说,“算是你娘的客人,但你娘可让我提醒你得回去。”
“我只是传你娘的话,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别问啊。”爹起身去捆另一垛秸秆。
胡枫一个人思忖了一会儿,依旧专心做手里的活。远处传来隔壁生产队你来我往、此消彼长的对骂声,持续了好久后最终只剩下一个忿忿不平的声音――那便是李树贤的叫喊。他还有个叫李树良的弟弟,兄弟俩都不是什么好胚子,上学堂那会儿就老偷偷翻人书包,常常拿坏的东西借别人,然后扯着对方的衣角索赔,又哭又闹,腌臜至极;等到长大进了生产队,队里闹矛盾的,也常常有他们俩。昨天胡枫在河里游泳,闲来无事的树贤就一直怪声怪气地取笑他,还故意地在他面前用力踢水溅他一脸。胡枫气不过树贤得意洋洋的样子,便踩着树贤的大腿往水下一蹬,树贤当场就呛了好几口水,气急败坏地说:“你他妈的,就你能是吧!这事没完,我跟你说,我跟你没完。明天有胆你来,我把命都给你收了!”
此刻胡枫见他已完全沉溺于另一场厮斗之中,料想他那一段气焰嚣张挑战宣言,大概是不作数的愤激之语。然而胡枫还是决定晚上回去时路过一下河边,因为向来他做什么和别人做什么是毫无干系的。
不觉薄暮冥冥,太阳渐渐消融在东凰山西边无垠的大海里,粼粼的海面耀得人目眩心花;村民们也都三三两两地带着斜长的影子回家。那时虽大兴农业合作化,倡导集体劳作,但生产分配却早已不是什么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也已是将近七八年前的事了。农民们凭借着工分和家庭人口数领米,在自家灶台上炊。作为队长,胡枫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匆匆赶回去吃顿饭后,晚上还得挨家挨户地去收集村民们烧灶余下的草木灰和养猪棚里堆聚的猪粪。这些在当时可是宝贝,草木灰代替稻草让牛卧着取暖,猪粪作肥料,都是要原封不动地充公的。胡枫想着得事先跟他娘通告一下,然而娘却早已吃完饭不知去向了。
等胡枫把一切都弄得妥妥贴贴了,已到夜阑人静的时候了。村民们晚上少有别的活动,都纷纷关门闭户地入睡去;挂在门前的松垮垮的竹帘,不知从哪代人起就开始默默独对着这清冷的光辉,破漏了的好几处靠着薄薄的白纱藕断丝连着。草丛里虫鸣聒絮,同庭前如流水般的月光相映成趣,颤得溪水也跟着汩汩地流动,流进载着丰收美梦的沉甸甸的枕头里。
那时的夜晚顶凉喽!转眼间,胡枫已经走到小溪前了,他四下看看,发现远处黑黢黢的山影下,有两个人正一前一后地自隔岸朝他走来。
走在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那盛气凌人的李树贤;不过他也真够可以的,来同别人较量,竟还时刻不忘带着他的弟弟李树良。
“过去呀!”他挺着胸脯挡在胡枫面前,树良站在他身后看。
胡枫笑着轻摇了摇头:“够了,就这样吧。大家一人一下,也都不吃亏了。你还要再打架干嘛呢?”
可树贤还是推了他一把:“我就是不爽了,有种来咧!”
胡枫一个趔趄,伸出手来防备。树贤见状像是一下子被点燃了似的,即刻掣起拳头就要来打;忽然听得有好几个声音乱哄哄地先后喝住了他,且仿佛是从四面八方向他合拢了来似的,搞得他个措手不及。树贤慌不择路,转身就跌进了河里,树良也被一拥而上的人影追得抱头鼠窜。胡枫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几个小伙伴儿来了,他们不知从何而来的消息,只见他们喊着“敢搞我枫哥”的口号,把树良一直逼到林子里才乘兴而返。
胡枫舒展了观战时紧皱的眉头,笑着对兄弟们说:“本来不打算打架的……”
“那两兄弟只会装有种,不收拾一下他们还真想要‘小鬼压大神’呢!”一人说。
“枫哥人别太好了,有人弄你我们都会一起上的。”另一人说。
……
“那个没娘的树贤呢?怎么还不爬上岸来?”忽然有人担忧了起来。
“不会给淹死了吧?”
“是他自己跳下去的,还能淹死?”
“四处找找吧。”
众人循着河岸细细搜查了一番,然而水面上一片平静,在黑夜里水下深邃得似乎能轻而易举地将一个人吞没。
“找不到――估计游回家去了。”
“农村人能有几个被淹死的。”
“要是他溜了,我们还一直在这里找他,岂不是显得我们在被他耍。”
“那回去喽?”
“可是……”
所有人望着河面无所适从地站着,最后是一个能裁断的人认定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好不耽误明天的日程,于是大家也就自我宽慰地各自离去了。惟有胡枫走了一小段路后又忙不迭地跑了回来,此刻他忧心如焚,回去怕不也是夜不成眠。胡枫面色凝重,对着河自言自语道:“这树贤,弱成这样了,还学人挑事。”紧接着就打算下水去捞。
“在那里干什么!偷东西啊!”村里一个在船上安家的老头儿冲着他的船尾喊道。
胡枫侧过身去看,李树贤正死死扒着船不敢松手,也不敢出声。
那老头儿气汹汹地走过去,胡枫意识到树贤刚刚是见岸上人多,便一直躲在船后头不敢露面,现在被误认为贼了。他赶紧向老头儿解释道:“阿伯,那人是我朋友,他掉水里了,还不怎么会游泳。”
老头儿将信将疑地看着树贤爬上来。
“还有那个人,”胡枫指着林子里慌慌张张跑来的树良,“就是他的弟弟,来领他回家的,不信你等会儿问问看。”
树贤脸色苍白地盯着胡枫看,好像还有一丝不甘。趁着树良还没到这里,胡枫决定先行一步闪回家去。走到巷子口,和迎面出来的刘春来互相一吓,春来抓着他惊诧地问:
“你哪去了?就只找你不着――你家里来了客人,你娘在招你回去呢!”
“欸,是女客哟!”没走几步,春来回过头来神秘地笑着。
胡枫道别了春来即拐进巷子里。寂静的深巷中,一排望去各家各户全都浸没在黑暗里,只剩下巷尾的自己家仍泛着昏黄的灯光。
胡枫轻手轻脚地慢慢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