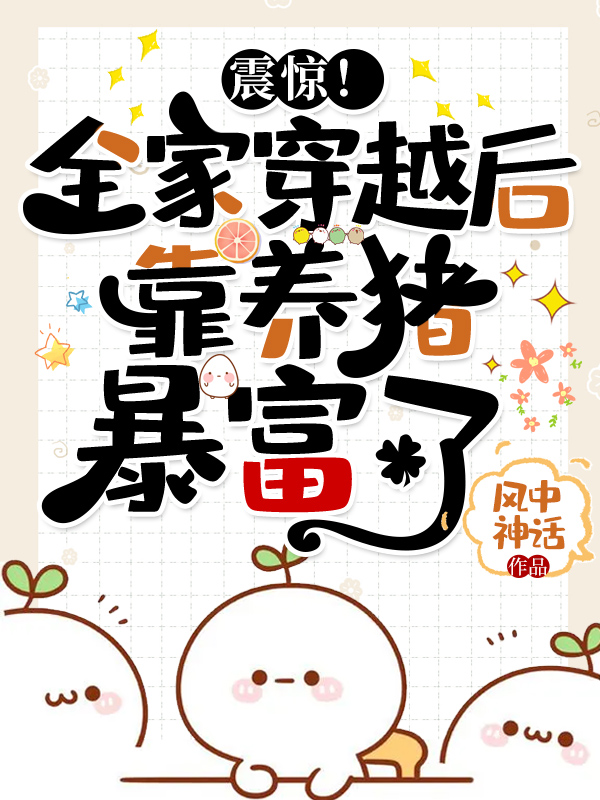“有毛病为什么不早说?”病房里的人明显少了一些,这回是孟瑶的声音,看来之前我的沉默似乎被当成默认了。
“我……”我本来想跟她说我的看法,就算全告诉她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被一声“嘎吱嘎吱——”打断。
我听见走进的声音,“头低下,让我看看你的伤。”
“以你现在的状况其实不太适合动手术,”我能闻到孟瑶身上的味道和眼罩上残留的味道是一样的,但是我没时间也没心情心猿意马,“但是你已经拖了一天左右的时间,你要是再不说就有可能失明。”
“学姐,我也是学医的,这些我也懂。”我苦笑着,事到如今,不管怎样我的眼睛肯定是有问题的,至于声音和视频中的黑影,乐观一点可以将它们归为脑震荡后产生的幻听和莫须有。
“那什么,我有点饿了。”我尽量让自己不去想。
我听见饭碗被端起来的声音,“有些凉了。”小李就站在我的旁边。
“没事,给我吧。”我伸手去接,早上一番折腾确实有些饿了。
“还是我来吧陈少。”我听着饭匙搅动的声音,“来张嘴。”
说实在话我现在对小李的好感又进了一层,可是越这样就越替她感到不值。“你早上到真的是吓到我了。”
“抱歉,我没想到会这样。”我喝了一口粥。
“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有什么问题还是不舒服就说啊,瞒着能自己好一样。”孟瑶好像是站在床尾在写着什么,我能听见笔与硬纸板碰撞的声音,看来是在写签到卡。“亏你也是学医的,这点道理都不懂?”
这次还不算严重,也是能找到病因,要是像最早在梦里那次,你们不得把我关精神病院里去?我只是把事情尽可能的往好的方面去想,这世界上本就不存在悲观的人,因为人总是想方设法的要好好活下去。
“服了你了。”孟瑶应该是写完了签到卡,“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赶紧说。”
“那个,眼罩可以送给我吗?”我顺水推舟。
“行,你带着吧。”我听见孟瑶似乎很无奈的叹着气,“你要是有这份心去配合,现在就没这档子事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先被推去做了眼部超声,虽然我不确定这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在摘下眼罩的一刹那我还是看见了缩在墙角里的那团黑影。超声的仪器设备是亮的,电脑屏幕也是亮的。我不太想去多想了,想不明白自己吓自己更没意义。做完超声没多久就打了麻醉就被推上了手术台。那些手术器具像极了古代的刑具,先是用支架撑开了我的眼睛,然后又是刀又是针的就往我的眼睛上杵。
打了麻醉之后就和喝了酒一样迷迷糊糊的,感觉也有些不太真实,勉强能看出一个个围着我的脑袋,聚在并没有打着的手术灯下。我只是借着旁边微亮的心率监测显示荧幕的光才能看清这些。
“嘎吱嘎吱——”那个东西也跟来了,只不过我不知道它现在在哪,但我知道它一定在盯着我。
“心率有些快了,放松。”一个女性的声音朦朦胧胧的在我耳边响起。
我直视着上方,一个巨大的机器射出一束暗淡的光打在我的眼睛上。进手术室之前我记得那个老谷跟我说过,需要开刀配合激光光凝缝合。
“嘎吱嘎吱——”声音又响了起来。我突然有了一种羔羊被推上屠宰场任人宰割的感觉,每一张口罩下面的脸都带着扭曲的笑意。
“心率过快,镇定剂。”一股凉意顺着胳膊上的针头钻进我的身体里,瞬间我所有的焦躁和恐慌都被冲散了。那之后我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已经对时间没了什么概念,一只眼睛被包上之后又是另一只眼睛,做完之后也被包上,然后细细的缠上了不知道多少圈的纱布,就漏了个鼻子和嘴。
我被推出了手术室,又被转到了病床上,之后好像是陈老头在我耳边说了什么,但我没听清。实在支撑不住麻药和镇定剂的后劲,意识全无的睡了过去。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模模糊糊的醒来,但是眼前一片漆黑。对,我刚做完手术。我伸出僵硬的手,我记得呼叫器就在头顶后面,但是病房里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让我停了手,听着像是塑料袋的声音。
“现在几点?”我不知道是陈老头还是小李。
在我说话的瞬间声音就停止了,但是没人说话,也没有脚步声,只能听见我的呼吸声。
我感觉身上开始冒冷汗,慢慢伸出手摸向床头。
“哗啦——”我听见卫生间抽水马桶的声音。我已经感觉到我的牙在打颤了,人在丧失视觉之后首先是会加深听觉嗅觉触觉等的感觉体会,并且会对其极其敏感,之后会对此产生恐惧或者激动兴奋的心理。一句话概括,你看到的世界和听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尽全力的安慰着自己,塑料袋的声音是风吹的,一定是小李怕我闷开的窗,开来现在天色还早。至于卫生间一定是隔壁病房,这些单人病房的质量竟然做的隔音这么差,找时间一定要跟陈老头反映一下。
我摸到了呼叫器,有了一种解脱的快感。也就是同时,我听见了我的床下传出了一个拖行的声音。我身上的汗毛瞬间炸起,那个声音离我如此之近,和我仅仅一个床板相隔。声音还在不断响着,像是什么东西正在缓缓地爬出床底。
我不想在犹豫了,按下了呼叫器。可是却没有声音,对,没有声音。以往那个让我有些厌烦的声音真的没有响起,一种绝望的感觉充斥着我的全身。我又不信邪我按了几下,终于传出了声音,但那声音不是呼叫器的,而是来自于床下,一声尖叫让我双耳欲聋。
我顾不上别的,凭感觉撑着双手想要下床。手背上应该挂的消炎吊水,我这么一番活动把针头扯了出来,疼痛钻入我的心里,我咬着牙硬挺着,终于双脚着了地,我也顾不上四肢百骸的不适和坠痛,向着我记忆中的门摸索了两步。那个尖叫一直在我身后,好像催命鬼一般,似乎下一刻就能抓到我。我不知道踩到了哪里,突然脚下一空,我跌了下去。
我猛地醒来,大口的喘着气。看来是梦。但我的视野里仍然全是黑暗的,看来我应该刚下手术台。眼皮被牢牢地粘住,想来在恢复好转之前大概一直要这样。
我伸手摸向了呼叫器,梦中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我生怕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出现在我的附近,我甚至感觉到我的手在颤抖。
“嘎吱嘎吱——”那个让我无法摆脱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它一直在我的周围,想来自从出了事故以来,它就一直在我身边挥之不去。
我感觉裹在我脸上的纱布几乎被冷汗浸透了,如果我还能听见它的声音,是不是说明它还存在呢,这并不是视网膜裂孔产生的幻视,而是一些其他的原因。我不太敢想下去了,颤颤巍巍的手终于摸到了呼叫器,犹豫了一下还是按了下去。
呼叫器的声音格外刺耳,但现在对于我来说却是天籁。很快病房门被拉开,“陈少你醒了?”这是小李的声音,她走到了我的床边。
“几点了?”一种解脱的感觉油然而生。
“八点二十分。”小李回答,看来因为镇定剂和麻药的效果睡了整整一天。
“让你受罪了,从早上忙到现在。”我撑着身体想要坐起来,眼睛在隐隐作痛。
小李摇起了床板,听见我这话明显楞了一下,“还好,中午换班休息过了。”她把枕头垫在我的脖颈处,“今天晚上可能会很不舒服,要止痛剂的话直接按铃。”
“我现在很不习惯,陪我一会吧。”我脸朝向小李,我知道她就在我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