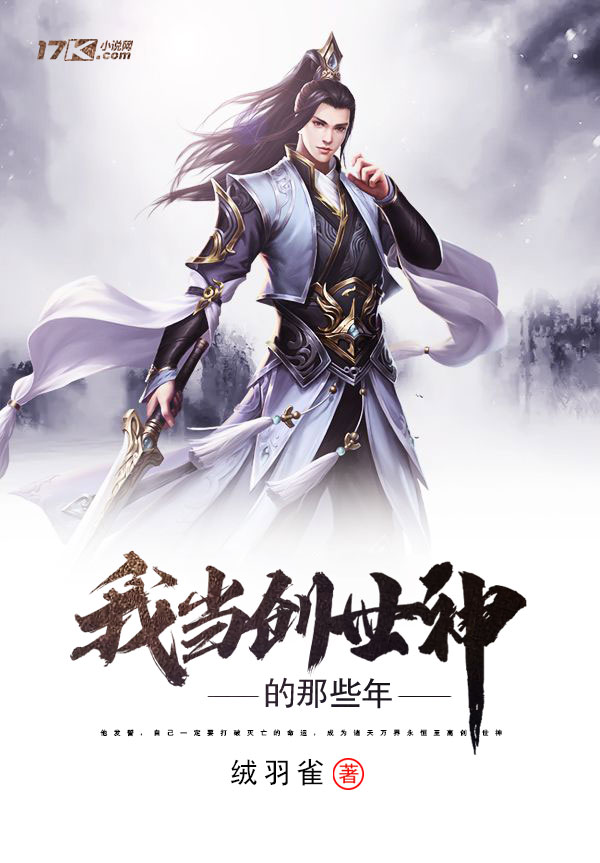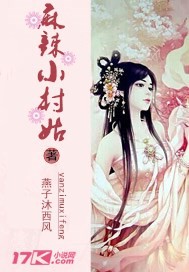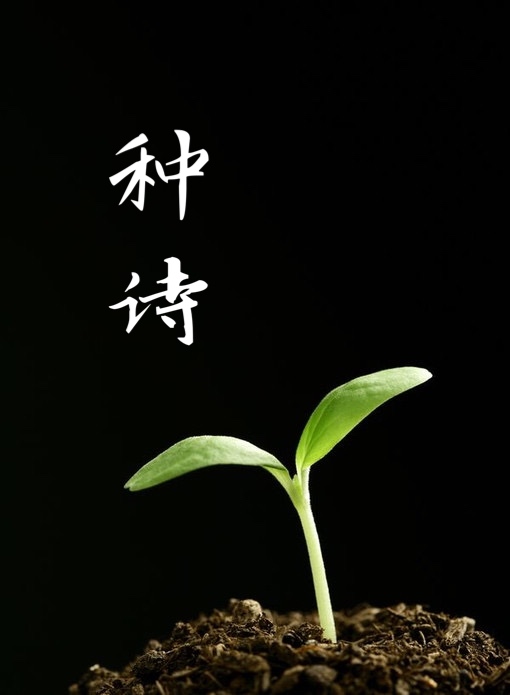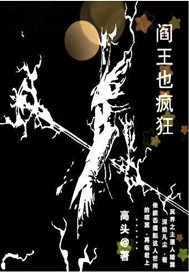子夜已经过了一个多时辰,方艾与柳星河都不时望向来时的路,默契地保持着沉默。
柳星河已经重新半躺在了地上,恢复了之前的从容淡定。倒是方艾时不时地来回度上两步,焦急全都表情和动作上,不言而喻。
其实方艾和冷凝川并未相识多久,按理说方艾没理由太过担心。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就晦涩难明,莫名的亲近,莫名的信任,莫名厌恶疏远,有的缘由明了,有的仅仅由心而生。
譬如人之初见,不同的人感觉自会不同。或是一眼,两人便能成为多年的挚友;或是一眼,两人便能互相托付;亦是一眼,两人便能擦肩而过,不相往来。常说人心难测,人心的确难测,且万般不由人。
冷凝川给方艾的第一感觉便是亲近,这种感觉无根无缘,难以揣测,就像人看到水就知道能解渴一样自然。说不尽,道不明。可若非要非要说一个原因的话,那便是不如此,剧情便不得已发展。
正因如此,方艾这时自然地感到焦急。刚才的剑光太过霸道,让人不寒而栗。剑光存在于天地之间的那段时间,原本呼啸的夜风都为之停止,人的呼吸也不受控制得变得艰涩。
方艾试想过,如果是自己面对刚才的剑光,不必多说,必死无疑。
月色如水,朦胧间可以看到远处的光景。忽然,柳星河的嘴角微微扬起了一个弧度。他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和草屑,然后缓缓转身。
夜色下,百丈开外正有一个人影靠近。人影移动的很慢,不仔细看的话很难注意到。随着人影逐渐接近,月光落下,一张略带沧桑却饱含笑意。
越过山丘,有人等候。这时方艾也发觉了后面的情况,见是冷凝川出现,他连忙迎上前去,脚步匆匆,脸上的焦急已然化作不加掩盖的笑容。
“大叔,你可算回来了。好不容易出来,我还以为又要回去伺候老爹了。”方艾快步来到冷凝川旁边,打趣道。
“情况和预想的有些出入,耽搁了。”
“出入,是不是刚才那道剑光?”
迈步间,冷凝川点头:“没想到赵家还能请动那种高手,是我疏忽了。”
方艾仔细打量了下,发现冷凝川虽然没受什么伤,可衣衫上多了几处明显的破损,应该是刚才留下的,一时之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了。缓步间,三人汇到一处,柳星河上前迎了两步。
“那般霸道的一剑都奈何不得前辈分毫。恕在下眼拙,还是低估前辈了。”
冷凝川摆了摆手,无奈道:“刚才在江面之上,大家都只有一招之力,我才能勉强退开。如果拉开架势,我怕也不是那人的对手。”
柳星河笑着,既没认可,也没表示怀疑。转而问道:“前辈可知那人是谁,我对他的剑倒是有些兴趣。”
“齐国江湖鱼跃潜龙,一一细数不太可能。不过南边地界有此种剑道的,我倒是知道两人。”
“哦?哪两个人?”
“一个是东海剑派的宗主向东来,此人修为多年前便已入神闲,剑法凌厉霸道。自称什么‘东海剑仙’。虽然多少有些不要脸,不过实力倒是不容小觑。”
冷凝川看了对方一眼,两人刚好对视。柳星河悠悠来了句:“你这么清楚。怕是除了我柳家,今天这赵家,那东海剑派你也没少去找麻烦吧?”
“咳咳,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冷凝川挑了挑眉,表情稍微有些不自然。
“那还有一个呢?”
有人等着下文,叙述只好继续:“另外一个好像叫沈白易。这个人游走于齐国南部,行踪飘忽不定,专门拿钱办事,做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听说这个人剑道天赋很高,二十五岁就已是半步神闲。至于现在什么修为还真不好说。”
“二十五岁,半步神闲。”柳星河自语了一句。
“没错。和你倒是颇为相似。”
接下来柳星河陷入思索之中,气氛又沉默了下来。方艾见自己好像插不上嘴,只得在一旁时不时地溜达几步。
“我知道你小子在想什么,想找人长长见识也不是不可以。沈白易就是个亡命之徒,犯不着招惹,倒是东海剑派那臭不要脸的老头挺不错的。”
柳星河投去一个询问的眼神。
“这有什么不懂的。到时候去了报上你柳家少主的名头,说要和他切磋切磋。他如果同意,那就打,反正那老家伙肯定不敢真把你怎么样。如果不同意……”
“那怎么办?”方艾忍不住凑了过来。
“不同意,你就站他山门,狠狠地骂,狠狠地羞辱他。不出一柱香的时间,我保证那老家伙会忍不住出手。”
夜风呼啸,空气中不见言语之声。柳星河斜瞅着冷凝川。方艾则是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不停微微点头,一副赞赏之色。
好像是意识到了气氛的尴尬,冷凝川舔舔嘴唇,干咳两声:“我也是听说,听说。这种江湖传闻你们听听就好,别当真,别当真啊。”
“前辈真是深思熟虑。现在看来,我被骗的着实不冤。”
“哎?说了是听说,怎么还阴阳怪气起来了?”冷凝川背着手,开始故作严肃。
柳星河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转而到一旁牵着两匹马走了过来,把缰绳分别递到了两人手中。
接着后退半步,抱拳道:“前辈,小兄弟,咱们就此别过。今天和两位相处的很愉快,特别是前辈的指教,真是让我受益匪浅。”
“啧,你小子还来劲了,注意你大家子弟的风度。赶紧走,赶紧走。本来还想送你匹马的,现在你马没了。”
“柳哥,咱们有缘再见。”方艾也学着柳星河抱了抱拳,语气真诚。
“告辞。”
柳星河转身,看了眼夜色下的江城,迈步而去。两人则目送柳星河走远,直到他消失在夜幕之中。
“咱们也走吧。”冷凝川率先动身,向着反方向行去。
方艾连忙快步跟上,问了一句:“大叔,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青天剑宗。”
人物有杰出者,国家有辉煌者,宗门也自有强盛者。而在各国之间最负盛名的便有两个宗门,一为齐国的青天剑宗,于齐国东部,处东海之滨;二是楚国的南山宗,位于楚国南部的莽莽群山之中,得此名倒也不足为奇。
两个宗门的实力处于伯仲之间。不过青天剑宗主修剑道,“修心,养剑,以破万法”的理念根植于门派的传承之中。剑之一途,已是登峰造极。
反观南山宗,其和青天剑宗却是截然不同。南山宗博采众长,底蕴深厚,武学功法更是不知凡几,浩如烟海。比之青天剑宗的一剑破万法,南山宗更在意的却是万法皆通,殊途同归。
两宗功法路数大不相同,甚至可说是南辕北辙。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同样强大。可谓是威立各地,名扬各国。
“剑上青天,武蕴南山。”
正因如此,各国之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不仅代表着两宗实力之强,普通宗派早已无出其右,更说明了两宗在天下人心中的地位,无由则不可撼动。
不过地位可以靠实力来获取,名声却不尽然。两宗能有如此声名,其立场和行事作风也是不可或缺。
若是从不见山水说起,两宗都有着数百年的历史,传承漫长而悠久。
其中青天剑宗秉承着“乘天地之正”的信条不断延续。所谓“乘天地之正”,即遵循天地之大气运,亦是遵循天地之正气,不偏不倚,道法自然。
归结一句,青天剑宗持名门之气象,怀正派之道心。
而在这一方面,南山宗也是当仁不让。其弟子行走世间,秉承着用恶人之血证道的原则,以诛邪除恶为己任。
而在南山宗两百年宗门大典,也是南山宗风头正盛之际,其当代宗主更是在天下同道面前表示,南山宗要为天下正衣冠。
如此一来,地位彻底巩固的同时,其门下弟子更是将“为天下正衣冠”一句奉为圭臬。
一路之上,或是无聊,或是其它,冷凝川不时给方艾讲着一些江湖之事,青天剑宗和南山宗自然也在其中。
方艾在听这些事情的时候也颇有兴趣,毕竟他从小就喜欢听老爹讲这些趣事。不过老爹的讲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冷凝川的一番讲述倒也让方艾受益匪浅。
可相比于江湖之事的有趣,此刻映入方艾眼帘的景象却让他震惊。一眼望去,四周地势平坦,视野开阔,除了远方那一片绵延的山脉,这样的地势可以说是非常奇怪。
过了横江,方艾和冷凝川一路行来都是大片的平原,不见山岭。眼前的山脉好似凭空拔起一般,就这么突兀地摆在了人的面前。
但这只是让方艾震惊的冰山一角罢了,让他更为惊叹的是远山的壮丽景象。
只见远方苍峰十数座连结为山脉,广阔的平原被宏伟的山脉阻断。那高俞千丈的山仿佛一道天然的屏障,隔绝了小半个天地,遮天蔽日,垂范千古。
不知屹立多少年的山脉散发着恢宏而磅礴的气势,恍惚间如一头远古的巨兽睥睨着世间,又如十数道剑刃直抵苍穹,让人心底不由地升起一种弱小且难以抑制的不安感。
其中最为显眼的莫过于山脉的主体。山脉主体看起来仿若一只翱翔于天际的大鹏,云雾飘渺,紫气生烟间,其模样更为神似。
大鹏展翅而非,其翼不知里许,穿云气,且背负青天。
冷凝川和方艾示意了下,表明那就是两人一行的目的地,青天剑宗的所在,鹏来山脉。东海之滨有鹏来,鹏来之上有青天。
“不愧是大宗门啊,山门所在就如此气派。”方艾发自内心地感叹了一句。
冷凝川策马继续前行,悠悠道:“的确如此,这样的景色可不多见。不过还是抓紧赶路,剩下的路也够你看了。”
鹏来山附近有不少人口聚集区,形成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城镇,棋布在山的周围。方艾和冷凝川顺路前行,临近天黑来到鹏来山的外围,然后进入了一个路过的城镇。
城镇中有青云剑宗设立的驿站,两人将马匹交付过去,然后随便找了个客栈将就了一晚。
夜晚,清冷的月光洒落在鹏来山间,不由地为鹏来山增加了不少朦胧的美感,也让其变得更加难以捉摸。难以捉摸来源于未知,而未知则会让人感到危险。
在这里早已看不到鹏来山的全貌,可却更能近距离地感受这座山脉所带来的压迫感,这种感觉说不清缘由。
正如晴天霹雳会让人心惊一般,这座山脉自行拔地而起,鬼斧神工间似乎也带上了煌煌天威。
不过这些没来由的感受都会留给那些去感受的人,方艾正好不在此列。因为他实在是太累了。连续几天的赶路让他身心俱疲,几乎是一粘到枕头就沉沉睡去,今夜的一切早已与他无关。
第二天一早,方艾和冷凝川收拾了一下,然后徒步进山。虽然鹏来山都属于青天剑宗的势力范围,但其山门仍处于中心地带,所以继续赶路自然必不可少。
行走于密林之中,周围草木生长,荆棘丛生。树木与藤蔓相互缠绕,盘根错节地遍布于长满苔藓的地面上。
参天古树的繁茂枝叶遮蔽了头顶的天空,不过阳光透过枝叶间的缝隙投下的斑驳光影以及某块空地上洒落的大片阳光,倒也使得林间不至于太过阴暗潮湿。
一路行来,杂草横生,荆棘遍地。方艾的衣服难免被划破,甚至有几处已经开始有血渍浮现。冷凝川似乎也有所发现,有意无意地放慢了前进的脚步。
不过随着路程的继续,这种情况也逐渐有了好转。古树依然高大茂密,荆棘和莫名的植物却少了许多,甚至已经慢慢地有了可见的路径。
这种情况,看来应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