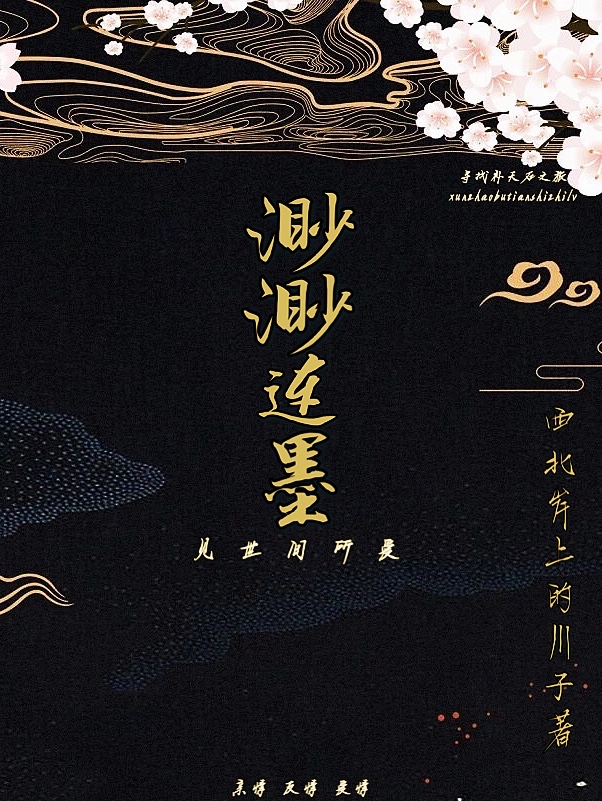第二十九章
“当今世上,固魂丹可谓修补魂魄的万能灵药,万千魂魄得一粒固魂丹,便可重新往生,获得实体,即为复活之道,可是这世间族类各有所别,固魂丹又是否真的适用于所有族类?”
浣歌僵在原地的时候,洌溪问出这番话,仿佛已告诉了一个她不愿面对的答案。
“漓歌的真身…是什么?”浣歌觉得这一问,竟花费了她极大的勇气。
洌溪面朝着西方的迷茫远山,叹息道:“漓歌是这世间最特殊的存在,故而一般常法,对他皆没了用处。”
自小与漓歌相处的上千年岁月里,浣歌只知漓歌是既上任水神洛涵之后的水神,那么漓歌的真身必是与洛涵一样,由水灵所化,却从未想过有其他可能,也从未发问,她忽然想到,甚至连洌溪的真身,她也未曾较真地想过。
前世的记忆里,她只记得一场桃林繁花后,第二日便见漓歌带着洌溪出现在烟波殿里,那时一心激动于水明泽上又出现了新的伙伴,将洌溪的来处悉数抛诸脑后,后来,因为洌溪也精通水术,故而潜意识里也认定他是水灵所化,可是,眼下,她已不能再如此笃定。
“漓歌于你,从来都不是多话的人,他不愿在你身边聒噪,也只会如你所愿地出现和离开,可是许多事情他不肯言说,你便不曾去关心吗?”洌溪忽然转头激动质问。
浣歌低下头,只觉对于这一质问,她无言以对,更无颜以对。
脚下的雪银光闪亮,白的刺眼,浣歌痴痴望着,仿佛看见前世里如雪洁白的一袭白衣,他有一双温润的眸子,笑起来淡泊而和煦,令人没有负担地安然享受,她生前的最后一刻,便是由他护着,一个救了她性命的人,她却连他的真身是什么都一无所知。
她怎么就这样没有良心地活了这么许多年!!!
胸口剧痛,一颗心像是要自行碎裂惩罚自己,浣歌蹲下身子,将头埋进双臂里,许久,终于放声哭了出来。
当年眼睁睁看着漓歌为她身死,她徒留魂魄,竟连一滴泪也来不及为他流出,及至五百年在莲花里的沉睡,她更是从未有机会发泄自己心底这一处隐痛,而今天,洌溪终于为她找到了出口。
她这突然的一哭,让洌溪忽然有些不知所措,一贯淡漠的表情渐渐有了不忍,好像感觉到自己的过激,洌溪有些犹豫又有些挣扎地伸出手,抚上浣歌的肩膀。
浣歌肩头一震,有些意外一向冷淡的洌溪会突然做出这样亲昵的举动来。
撞上浣歌突然抬起的眼,洌溪像是受惊的莺雀,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猛然缩回的手。
有片刻的尴尬,在两人之间弥散。
洌溪轻咳一声,别过头去,淡淡开口道:“漓歌…漓歌怕是这世上仅存的一个族类。”
浣歌有些震惊,世上仅存的族类?除了这一世她所归属的精灵族,她实在未曾听说还有什么其他族类。
“说起漓歌的真身,便要从师父尘永的真身说起。
相信上一世师父赠与你须椹草的时候,你已经知晓师父的真身是一株灵参,集了千年天地灵气后,修得人形,无意间进入人界,遇到人界百年一遇的瘟疫之灾,短短几日便夺取千万条性命,师父心性慈悲,于心不忍,便用自身须椹草解救了这一场凶猛的瘟疫,人界才终于得以继续延续存在。
而人界延续的代价,师父一力承担,后果便是修为散尽,留得最后一口灵气只够他化作原形—— 一株即将枯萎的灵参。
师父的这一舍生取义的善举被路过的西方佛祖看在眼里,内心大恸,落下泪来,其中一滴落在灵参的枝叶上久久不曾风干。
许多年后,籍着这滴佛祖之泪所携带的灵气,师父最终熬过了枯萎而死的劫难,重新以一株普通灵参之形平凡地存在着,陪伴他那么多年寂寥岁月的,便是那滴似凝在他枝叶上的泪水。
不知多少年过去,人界似乎已经忘记曾有一个白胡子的老人在他们面临灭顶之灾时,挺身而出救了他们全族性命,却有一人在翻看六界全史的时候,留心记下了师父的这一壮举。
于是,那一日花神柘舞出现在师父面前的时候,师父以为自己是否已经死去,以致出现了幻觉,竟能看见一个犹如神邸的女子,对着他这样一株平凡地灵参微笑,那一瞬间似乎漫山遍野的花朵齐齐盛开,令他久久不能回神。
待他神智归位的时候,他已经如许多年那样,化作人形站立在这世间里,而他只约莫记得那笑靥如花的女子不过是伸手轻轻抚了抚他的枝叶。
从那以后,他终于重新做回人形,从那以后,他多了千年修为,从那以后,他追随花神柘舞,一心打理水明泽,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徒弟,那滴陪伴了他许多年寂寥岁月的泪水。”
“漓歌就是那滴泪水……”浣歌喃喃说道。
果然是这世间最特殊的存在,浣歌相信没有人可以精准地界定漓歌到底属于哪种族类,他的真身不过是佛祖感念所化的泪水,一朝借助花神柘舞施与尘永的法力化作人形,成为这世上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修炼却一旦被法力所激发,就修为大涨的人。
而花神最后选择他作为水神的继承人,想必也是明白漓歌的这一特殊身份,不易为他人所察,修为潜力无穷,且由慈悲之念所化,生来心性纯善,更能驾驭水之心和神器。
浣歌想起前世里,她纠结于自己的身份没有归属,可其实漓歌才是真正没有归属的那个人,他却一直那样淡然处之,这让她不禁觉得自己前世里的那些执念真是个笑话。
“一滴泪水……”洌溪苦笑道,“每每想及此,我就痛苦万分,漓歌,他是这世间我最想拼了此生性命也要助他复活的人,可偏生他也是这世间我最最束手无策的族类。
浣歌,这五百年来,我一人居于汶疏居内,常常整夜整夜不能入睡,闭上眼好像漓歌还在屋外弹着琴,我只消迈出屋门,就可看见他双手翻覆琴弦,莹莹蓝光将他的眉眼照亮,比之天上明月还要皎皎如玉。
可是,常常我摸出门外的时候,只有满院清寂,好像那么多年我们一起共弹琴的日子不过是一场梦境,可是这汶疏居里里外外明明到处都还飘散着他的味道。
这味道像刀,割向我每一寸血脉,这味道又像酒,我沉醉其中,好像就能浇灭我的愁苦,于是,我矛盾挣扎,在痛苦里寻求解脱,最终只能狼狈地逃脱,再不敢回汶疏居。
浣歌,你说,我觉得洌泉能复活漓歌的想法,是不是我的偏执?”
浣歌看着无声落下泪水而不自知的洌溪,不知该要如何作答。
洌溪却并不计较她的答案,只是继续喃喃道:“可是,若是我的偏执,为何敖嫣公主听了以后,也那么笃定地相信了呢?”
洌溪忽然转过头,定定地望着浣歌,“她说她会帮我,浣歌,你呢?你也会如此坚定地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