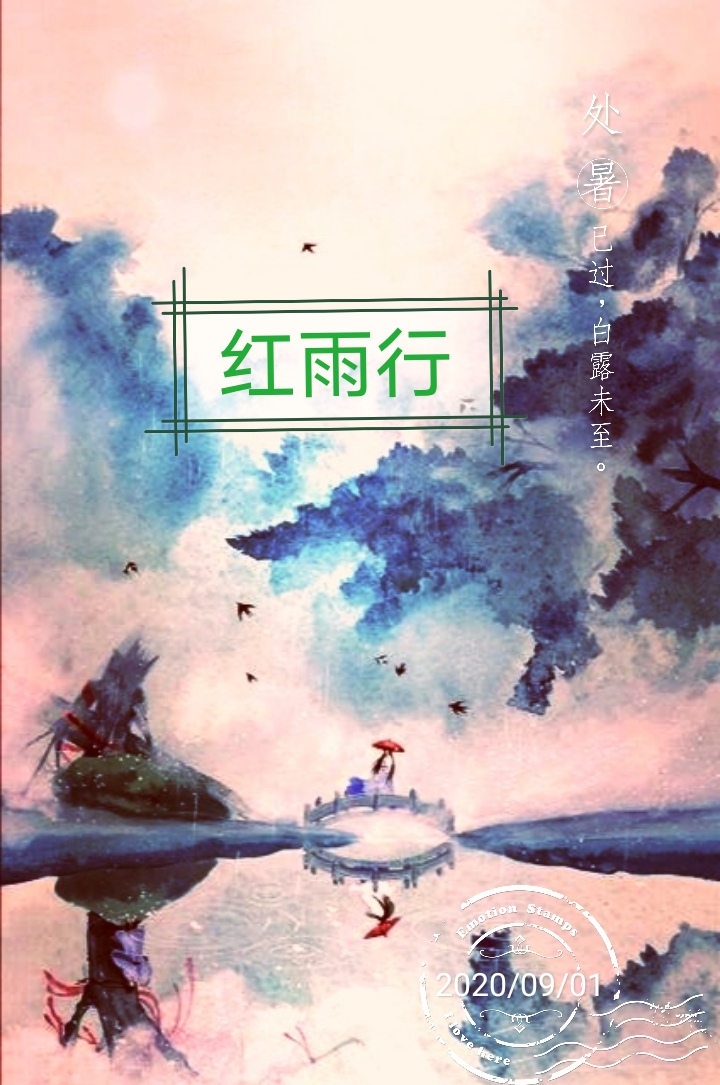“能出得起大价钱请来影杀,又花费重金买来鼠魔乱者,你的雇主想必是位拥有万贯家财的富贵之人吧?”季怜月并未从艾离身前退开,而是傲立相询。
君子如竹,不落俗囿。眼见面前之人全无惧色,本藤枷反而谨慎地停住脚步,“不要乱猜,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
“你说过,可以放过我。看来雇主仅让你杀她一人,对吗?”季怜月唇边噙出一抺浅笑,似是在与他闲话家常。
“正是!你速速退开,我便饶你一命。”本藤枷目露凶光,将短刀舞出一片白光。对方安之若素,令他心底生出一丝不安,只能以凶残掩饰。
“我若是不退呢?”季怜月含笑而立,如馨香之兰,淡静宁远。
这……本藤枷动作顿止,不禁流露出一丝为难之色。
“我已知你的雇主为何人了。”季怜月敛起笑容,神情肃然一冷,“你回去吧!告诉你的雇主,不要再做出此等不义之举。”
“你怎么可能知道?”本藤枷不解,他分明什么也没有泄露。握紧短刀,他低吼道:“不,你不可能知道!你一定是在诈我!”
“既然如此,你不是要杀她吗,为何还不过来?”季怜月侧移半步,让出艾离,并朝他招了招手。其举止优雅,态度温和,仿佛不是邀请他过来杀人,而是在招呼友人来家中饮茶吃酒。
“我们影之忍者生于黑暗,存于黑暗,从不正面攻击敌人。”本藤枷语声强硬,目中却疑惑渐起。
“你在等我毒发?”季怜月了悟地颔首,“过来一试,不就立即可知。”
本藤枷却未动地方,等了片刻,他终于忍不住问道:“为何你还能好端端地站着?”
“或许我只是在强撑不倒。”季怜月手执玉扇轻扣掌心,斯文得如同一名弱不禁风的书生。
本藤枷的眼珠随着他掌中玉扇上下而动,心底疑心大作。传闻此人有勇有谋,连聪敏绝伦的四王都曾败于他的词锋之下。他如此示弱,其玉扇又可解百毒,莫非他是在引诱自己靠近,好一举擒杀?
似是猜出他心中所想,季怜月睨他一眼,将玉扇一分分展开,慢悠悠地说道:“又或许我并未中毒。”
“不可能,我分明看到你与她都饮过那酒。”本藤枷像是证明什么似的,用力晃了晃短刀。
季怜月微微一笑,“那么还有一种可能,鼠魔乱之毒虽然霸道,却并非不可解除。对于顶级高手而言,只要有解药,想要恢复功力亦非难事。而我,或许正好带有解药。”
他边说,边背转过身,从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倒出一颗丹药,送入艾离口中。
眼见他泰然将后背暴露于自己面前,本藤枷惊疑不定,不敢妄动:此人身为地擂擂主,本领之强,有目共睹。若他不曾中毒,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令他更加震惊的是,艾离吃下丹药后,竟撑着长刀缓缓站起!
“你!你们!”本藤枷慌乱起来,一个玉扇公子他已不是对手,何况再加上一个武功名气更大的焰刀!
“代我向你的雇主问好,转告他不要再插手我派中之事。”季怜月像与老友打招呼般随意地迈前一步,语声却极为冰冷。
“你真的知道了……”本藤枷在他上前之时,便极为谨慎地后退了一步,始终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这并不难猜。”季怜月双眸幽静而深远,似黑沉无星的暗夜,“你之所以会来杀她,皆因这地擂擂主之位而起,对否?”
“不,你猜错了!”本藤枷猛然摇头,心底蹿起一股难以名状的寒意,令他急切地解释,“与我接洽的只是名仆从,我根本从未见过雇主!”
“凭你的本事,一个仆从也尽够知晓雇主的身份了。”季怜月再次向前踱出一步,唇角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念在初犯,你这位雇主也是心向于我,此次我便不多做计较。但我不喜欢旁人指手画脚,若再有下次,休怪我不讲情面!”
本藤枷脸色霎时一片青白:他竟然真的知道了!
“跟他说那么多干嘛?敢来杀我,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艾离满眼不耐,抬手挥刀,一个带着焰光的刀刃瞬发而至。
本藤枷猝不及防,被焰刃削中肩膀,连忙向后急闪。
她竟能运劲发功,看来鼠魔乱之毒已然失效!他大惊失色,立刻从腰间摸出一颗黝黑的小球砸向地面。小球落地即爆,院中升起一团浓厚的烟雾。
浓烟散后,本藤枷已不见踪影。
季怜月举扇挥去未尽的烟雾,讽然而叹:“难怪影杀身为外族,却能在大唐混成资历最深、价格最为昂贵的杀手。我这般相诱,他都不肯近前,忍耐之术如此精深,大唐的确少有人及。”
他将玉扇别回腰间,返身揽住艾离,温柔地说道:“师姐受惊了,我送你回屋吧。”
艾离抬手搭上他的肩膀,一双晶润的杏眸一瞬不瞬地凝视着他,其内波光粼粼。
“师姐为何这般看我?”季怜月不觉微怔。
艾离薄唇轻抿,似笑非笑,“传闻玉扇公子对敌很少动用武力,仅凭一张利口便可退敌,今日方始有缘得见。”
“师姐又来取笑于我。”季怜月双颊飞起一抺薄红,眼底泄出几分无奈。
“不是要送我回屋吗?”艾离不客气地将长刀推给他。
“师姐慢走。”季怜月一手接刀,一手环住她柔韧纤腰,漫步往其房间走去。
艾离轻轻“嗯”了一声,螓首微侧,倚上他的肩头。
微光的夜幕旖旎勾划着二人的背影,像极了一双耳鬓厮磨的情人。只有离得极近之人才能够发现,艾离微垂的额头上布满了细密如珠的汗滴。
季怜月将她扶到屋中床上坐下,返身关好门窗。他站立于窗侧,自帘缝向外观察些许时候,方回转到艾离身旁。
“影杀走了?”艾离用力压住腹部,丹田处暴走的内力,令她冷汗涔涔。
季怜月沉默地点了点头。僵立片刻,他涩声道:“你不该使出内力的。”
“不使出内力怎能吓退影杀?”
“我再与他周旋片刻,他便会退走。”
“那影杀一向如跗骨之疽,若是不让他确定你我并未中毒,这一晚上都别想好过。”见他还欲再言,艾离艰难一笑,“好啦,现在这样不也挺好。你那丹药再给我一颗吧。”
“麻药吃多了并无效果,且对身体不好,至少需隔上一个时辰才能再次服用。”季怜月死死抿住唇角,脸上泛起一片苍白。
他并没有鼠魔乱的解药,拿给艾离的只是一颗镇痛的麻药而已。艾离正是察觉到此点,才配合他,运动内力吓退本藤枷。
“那便算啦。”艾离抺了下额上的冷汗,不在意地说道,“鼠魔乱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剧毒,抗过十二个时辰,自然会消退。”
十二个时辰!季怜月攥紧拳头,深深地垂下了头。无可作为地无力感,令他淡青色的眼白上泛起根根血丝。
瞅见他眼底深切的自责,艾离眉梢一挑,奇怪道:“是我误饮了毒酒还拖累了你,为何你却一脸对我不起的样子?”
“不,影杀之所以来此,皆是因我而起。”季怜月身体轻颤得似梅压厚雪,嗓子暗哑得几乎发不出声来,“是我累及师姐。”
艾离无力与他争辩,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你若定要觉得有愧于我,便过来让我靠会儿,与我聊会儿天,我也能够好受些。”
季怜月愣了一下,挨着她坐下,僵硬地将她揽于怀中。
艾离放松地向后靠去,不由舒服地叹了口气。她一向独行惯了,平日里有任何麻烦都是自行解决。也许是他的神情触动了她,今夜她想放纵一次,偶尔找人倚靠一下。
见她脸色缓和了许多,季怜月紧绷的神经随之舒缓下来。方才揽她进屋之时,他的全部心神都在戒备于身后,然而此时,怀中的温软令他恍惚失神。不同于男儿,女子即使精神坚强如钢,身躯亦是这般柔嫩若水。
如此一想,他忽觉面上阵阵烫热,如能燎起火来。与她相触之处,似有一条条麻酥酥的火蛇钻入,并游走全身,令他极感不适。忍耐了一会儿,他问:“你好些了么?”
话一出口,他立即狠狠咬住嘴唇:这怎么可能!
不料艾离却点了点头,“你那麻药的确有些效用,这疼痛也并非难以忍受。”
季怜月闻言,下意识地紧了紧怀抱。那些火蛇突然一条条钻入他的心脏,狠狠噬咬,绵绵密密。
“对了,你怎么会刚好带有麻药?”艾离问道。
“此药是小师妹送给我的一位友人的。只是我还未来得及给他。”
忍过一波疼痛,见他不再开口,艾离说道:“都说你口才极好,不如讲些趣事给我听听吧。”
“你想听我讲些什么?”季怜月抑住心脏处的阵阵绞痛,一时思绪无措。平日与他相交者大都是江湖豪客,相聚之时多是谈论武功或江湖见闻。若谈武功,此刻她需要平定内息,并不适宜。若论江湖见闻,她最喜游历,知道的并不比他少。
这位真是江湖上盛传,排忧解难、舌灿莲花的玉扇公子吗?艾离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是带艺上山的吧?一直不见你提起上一位师傅,他为人如何?”
“我上一位师傅与宋师是至交好友,不过我已不在他的门下,他令我不得再提起他的名号……”季怜月顿了一下,涩声说道:“我少时被他捡到,从而收入门下。与咱们的宋师不同,他对我异常严厉。”
艾离听他语音滞缓,想是经历坎坷。她不愿掀开旁人的艰难过往,便压下好奇,转而问道:“那你是怎么来到咱宋师门下的?”
见她不再追问,季怜月语声明显顺畅起来,“我那位师傅与宋师因道法结缘。有一次,二人不知因何事打赌,我那位师傅输给了宋师。宋师看中了我,说他还缺少一名为他打理山门的徒儿,便将我要了过来。”
艾离想了想,道:“与宋师相熟,又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徒儿,你那位师傅必然非比寻常。”
骤闻夸奖,季怜月面上燃起一片红霞。暗自深吸了口气,他方平稳答道:“我那位师傅道法高深,只是他深居简出,从未在世间露过面。”
艾离并未看到他的脸色,继续问道:“你是十六岁时上山的吧?听说你刚上山时曾被小四挑战,你是怎么赢过那个倔小子的?”
“四师弟那时候还是个孩子,我怎可能与他当真,劝了几句,他也就罢手了。”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你都与他说了些什么?”
二人聊起往事,虽然平日各有事忙,甚少见面,却并不觉生疏。
他的怀抱温暖而安适,艾离竟生出许久未有过的祥和之感,不知不觉间,疼痛缓和了许多。闻到自他身上散发出来的花香,她取笑道:“你一个大男人身上为何还用熏香?”
“熏香?师姐说的可是这个?”季怜月自腰间拉起一只绣工毛糙的香囊,“这是青青姑娘送给我的。”
艾离心中一省,做出困乏之态,“同你讲讲话,我倒是好多了,也许可以睡上一会,不如你帮我点了睡穴吧。”
季怜月点了点头,扶她平躺。
糟糕,忘记点穴亦需引动内力。艾离刚想说不用了,却见他已然出手发功。
她的眼皮沉重地合上。在失去光明的最后一瞬,她似乎看到,他眼底深处有一片莹润的浮光闪动。
那光芒,温柔至极,却又悲伤刻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