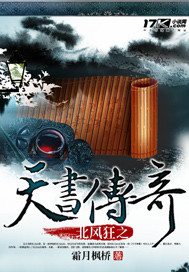落日,荒山,小道,号称东部最穷凶极恶的匪帮——岭西十一兽。
丁青山望着一个接一个从山道要害冒出来的悍匪,不禁苦苦思索: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
时间倒退回半日之前:
远山如黛,近水含烟。黄河岸边,一艘渡船正在收锚起航。艄公是名精壮汉子,几篙下去,船已离岸数丈。
正在此时,一名绿衫少年沿河岸急走而来,对着渡船唤道:“船家,请等一下!”
他表情焦急,声音却软糯好听,如厅堂倾谈时的细语,文雅而又谦和。可叹的是,此地位于汹涌的黄河岸边,这种斯文温柔的语音直接淹没于浪涛声中,专心起航的艄公根本没有听见。
连呼数声,却见渡船离岸越来越远,绿衫少年急得眼框透红,朦胧的水雾在眼底泛起。
四顾无人相助,他抺了抺眼睛,细致的贝齿咬上红润的朱唇。后撤数步,他猛然前奔弹跃而起,直向数丈之外的渡船扑去。
半空之中,河风鼓荡,青衫翩翩,他优雅飘逸得仿若刚从画中飞出来的仙子。一招飞鸟投林,使得煞是漂亮。
可叹的是,他对自己的轻功明显估计过高,离船尚有丈余,便已力竭。眼瞅着就要落入水中,绿衫少年吓得闭起双目。
“抓住!”
随着一声低喝,绿衫少年突觉双手似触碰到一物,本能地死命抓住。身体被那物忽悠悠地带起,面前河风急掠,紧接着脚下一顿,似是踩到实地。
耳听得浪涛声声,身上却没有湿凉之意,绿衫少年抓住救命之物不放,小心翼翼地睁开了一只眼睛。
一道颇具威压感的身影落入眼中,面前一人,正背阳而立。
抬头上看,那是一名手持长枪的少年,年纪与他相仿,个子却足足高出两头,蜂腰乍背,傲立如松。
是他救了自己?绿衫少年不由瞪大双眼,对着救命恩人细细打量。
但见那少年,皮肤晒得麦红,宽额直鼻,五官深刻,似带些胡人血统。一双黑目炯炯有神,灵光闪动,暗藏飞扬跳脱。常见的青灰色劲装穿在他的身上,箍出结实挺拔的身形,分外矫健硬朗。
绿衫少年忽闪着美眸,目露崇拜:烈阳下,那持枪少年仿若镀了层金属,铮铮铁骨,气势天成,真好似传闻中的战神一般哪!
其实,若论相貌,绿衫少年纤尘不染,翩然若仙,已是极美,与那持枪少年却是截然不同。
此时,持枪少年两道浓眉高高挑起,嘴唇微张,神情中带出几分孩童式的惊奇。沉默片刻,他双目一眯,沉声道:“放手!”
浓密纤长的睫毛缓眨,绿衫少年眼中一片惘然。
“滴嗒、滴嗒”,几滴鲜红的液体掉落到船板之上。
“还不放手!”持枪少年浓眉压低,似乎颇不耐烦。
顺着滴落的鲜红往上看去,绿衫少年漂亮的大眼凝视于他的手上。睫毛再眨,他终于有所反应,眼中的惘然渐被惊讶取代:别人持枪拿的都是枪杆,他握着的却是锋锐的枪尖,难怪他的手会流血……未及细想,但见对面持枪少年刚臂一抬,手中紧握不放的救命之物如同活了一般,奋力扭身而去。
这一下突如其来,绿衫少年被拽得脚步踉跄,险要摔倒。惊惶失措中,一股柔力将他撑住。抬眼间,枪影闪过,持枪少年不言不语地稳步离去,一杆长枪驯顺地伏于他的臂后。
绿衫少年保持前倾姿势不动,眸中笼上一层迷惘的薄烟。
良久,巨浪颠来,他身体一颤,眸中薄烟这才散去。双瞳缓转,他找到了目标:持枪少年已在船尾坐下,正心无旁骛地擦拭枪尖。
踌躇半晌,绿衫少年迈出小步,来至持枪少年面前,怯生生地开口:“……谢谢。”
不知是他说话的声音太小,还是他说话的对像太过专注,持枪少年头也不抬,继续一下接一下地擦拭着枪头。
河风寂寥地吹着,绿衫少年裹了裹略显宽大的衣袍,似是有些发冷。手足无措地站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落到那只一板一眼擦枪的手上。
那只手与常人的大为不同,不仅手掌比常人宽厚,每根指头也比常人粗壮,手背上的皮肤更是粗糙得不似少年人的手。仔细看去,那粗糙的皮肤并非天然,乃是由众多交错的伤痕组成,而指头粗壮则是因为每根指肚上都包有一层厚厚的茧皮。
绿衫少年不禁看了看自己细嫩白净的小手,不由想起师傅说过的话:手是人的另一副面相。……这人拥有这样的双手,定然吃过很多苦头。他如此爱枪,想必枪法不错。
一时间,二人一坐一立都不言语,只有一只手在上下运动。枪头已然雪亮,那只手却仍旧一丝不苟地擦着。
呆立一会儿,绿衫少年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从背后解下包袱。一通翻找后,他摸出一个拳头大小的玉盒,递到持枪少年面前,红着脸大声道:“那个……这是我做的伤药,请你收下!”边说他边偷眼瞄向持枪少年的手。与光可照人的枪尖相比,那只手上裹的那圈布条就太过随意,不仅随动作松松飘动,还隐约可见里面未干的血迹。
持枪少年终于停下动作,抬起头来。审视的目光顺着绿衫少年纤柔如玉的手上移,在细滑如缎的脸上定了定,他嘴角下撇,从唇中清晰地吐出两字:“白痴!”
绿衫少年如遭雷击,目光中满是震惊。瑟缩了一下,他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你说什么?”
持枪少年哼了一声,别过头去:“听不懂啊?我叫你白痴!”
眼中水雾骤起,绿衫少年猛然垂头,脚步踉跄地走去另一边,颓然坐下。拉紧衣衫,他蜷缩成一团,如遭人遗弃的小猫。片刻之后,强忍住的水雾终于凝聚成珠,一串接一串地无声掉落。
西风刮过,吹来一片秋寒。船外河水滔滔,船内小雨绵绵。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烦躁的声音出现在绿衫少年头顶:
“你到底要哭什么时候啊?”
泪眼朦胧中,绿衫少年扬起小脸,高大的身影再次把阳光罩住。
持枪少年脸上满是不解,想了想,他递过一张胡饼,粗声道:“喏,给你!”
绿衫少年瞥他一眼,默默转头,似在展示坚强不屈,眼中却涌出更多泪珠。
秋水盈盈!持枪少年心头一悸,脸色很有些发黑:“到底有什么好哭的啊?”
“我不是白痴……”随着一声哽咽,那秋水似有汇聚成瀑布的趋势。
啧,受不了!随口说说就能哭上那么久,不是白痴又是什么?
对面,绿衫少年仰起头来,那双哀怨的大眼睛正直直地瞅着他,似正期盼着答复。
持枪少年看到手中胡饼,急中生智道:“我说的‘白吃’是请你白吃东西,不要钱!”
潮水退去,茫然的薄烟笼起。目光落到饼上,绿衫少年吞了下口水,像只幼兽被食物诱惑,想吃却又不敢靠近。停了一会儿,他歪起头问道:“你真的不是嫌我太笨?”
持枪少年摇头道:“你一点儿也不笨。”
见他态度严肃,全无说笑之意,绿衫少年接过饼,斯斯文文地咬了一口,然后羞涩地笑了:“那我就白吃了。”
彼时,那长长的睫毛上犹自挂着一颗摇摇欲坠的泪滴,似新长出的荷尖上带着的露珠儿。持枪少年看得呆了一呆,随即“切”了一声,别过头去:男子汉大丈夫,只要原则不改,偶尔说说小谎,并无大碍。
……
“当”的一声,手中长枪受力大震,对面传来一声怒吼:
“臭小子,你到底打是不打?!”
眼见得对手在战斗中走神,匪首兽大只觉受尽侮辱。咱劫道的还谨守着劫道的规矩,哪有这样横插一杠之后却根本不把对手当一回事的人嘛!
丁青山横枪架住兽大力劈华山的一斧,猛发劲力将之震退,抬枪指点:“怎地?你自知不敌,想向小爷求饶?”
此言一出,如水入油锅,立时激得山贼们目放怒火,头冒青烟。
“臭小子,老大那是守规矩才跟你单挑,你当是我们兄弟怕了你不成!”
“老大!小子狂妄,咱们不必跟他讲道上的规矩!”
“一起上,干掉他!”
……
山贼们一片叫嚣,兽大阴沉着脸将手中板斧一挥:“一起上,把这小子给我废了!”发现不是对手,他立刻从善如流。
“杀!”齐吼一声,众山贼纷纷抄起家伙,自山道上纵身扑出。
丁青山满脸不屑:“打不过就一拥而上,真够丢人现眼。当不了山贼索性散伙,还是猫在山里打闷棍适合你们,也不用守什么道上的规矩。”他右臂前伸,左臂旁展,摆出个一夫当关的起势:“小爷时间有限,只能陪你们这些小贼玩一小会儿。”
“小子废话恁多,叫你尝尝厉害!”话音声中,兽二挺剑直刺,最先攻到。
丁青山摆枪招架,刚刚挡开兽二疾风般的一剑,兽三、兽四呼呼作响的双刀已砍至面前。他身子滴溜一转,双刀落空,趁隙向后瞟了一眼。
不远处的树后,某只被打劫的白痴正听话地躲在那里。从这里望去,可以见到他露出了小半个脑袋向场中窥视。微张着樱唇,黑润润的眼睛,以及那总是怯生生的表情,如同一只刚断奶的毛茸小猫,呆蒙蒙中还带了几分好奇。
丁青山自认倒霉地叹了口气:本来急着赶路,不欲多管闲事。可是这种一看就软绵绵、很好欺负的白痴,想放手不管也放不了手呀。原来自己的霉运就是从不小心捡到这只名叫莫小雨的白痴小猫开始的。
他没精打采地使出横扫千军,逼退三兽的棍棒合击,再抬枪格挡,弹开兽大的双斧。
“小子找死!”察觉到对手仍在走神,兽大只觉一口闷血憋在胸中上下不能。咱岭西十一兽的名号在江湖上也是响当当的。劫道这么些年来,就从没遇到过这么心不在焉的!
可恼呀,老虎不发威,你当是病猫吗!他双斧高举,威喝道:“兄弟们,摆阵!”
“杀啊,废了这个目中无人的臭小子!”听到兽大咬牙切齿的吼声,悍兽们兴奋的怪叫,老大终于要出绝招了!
场中气氛突变,本是冲向丁青山各自为战的山贼们在兽大身后依次排开。站在最前方的兽大威风凛凛地高举板斧,宛若龙头;在他身后是兽二的利剑,形似龙舌;接着是兽三、兽四的双刀,乃为龙翼;兽五、兽六和兽七的长棍展于其后,布作龙身;其余众兽分列最后一排,是为龙尾。
“盘龙三角阵!”丁青山眼瞳一缩,脸色铁青。有没有弄错!这不是早先军中号称最坚不可破的防御阵法吗?怎么现在一伙山贼都能随随便便地摆出来了?啧,麻烦!好不容易想当一回大侠,就碰上这么伙厉害的山贼,自己还真是倒霉啊!
“小子,害怕了吧!”见丁青山终于变了脸色,兽大得意地大笑,“如果你现在立刻跪地求饶,大爷我大人不记小人过,留你小命,还可以考虑收你入伙。”他笑得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刚才听臭小子一口一个小爷叫得好生气闷,这下终于有机会能还声大爷回去了!
丁青山双眉一轩,怒然道:“笑话!我丁青山大好男儿,定当沙场扬名,岂能与尔等匪类同流合污!”
“敬酒不吃吃罚酒!别以为叫出阵名就能破得了阵。”兽大沉下脸来。臭小子确实有些能耐,不仅枪法不俗,还能一语道破阵名。不过此阵可不是吃素的,阵下亡魂之中不乏高手!
“山猫野盗不知从哪里偷学了点皮毛就敢妄自尊大。”丁青山哈哈笑着拉开架势,手中长枪暴出一串低沉的鸣音:“好好睁大你们的狗眼瞅清楚喽!你们当中可有一人能识出小爷的枪法?”
“你小子的名字才没人听过!量你不过是个无名鼠辈。”
“爷爷才是使枪的祖宗,小子有什么能耐尽管耍出来献丑!”
几句话惹得山贼们纷纷叫骂。丁青山冷笑一声,枪杆猛然向下一戳,弹身而起。
银光乍现,枪旋如龙,刚健有力的身影飞跃半空,枪尖如泼雨般洒下。
山贼们不由得齐齐停口,凝神戒备:好炫目的枪法!
挑、刺、劈、扫、拧……丁青山将一套枪法狂风暴雨般使来。虽动作如风,每一招每一式却一丝不苟,令观者历历在目。劲风到处,虎虎生威,凛凛然一副大家风范。
眼见他迅捷之中不失威猛,山贼们面面相觑,都在对方的目光中看到困惑:自古武者大致可分为两种,或以力降敌,或以速降敌。以力降敌者必速不可达,以速降敌者必力不能及,这样即快且猛的枪法却未曾见过。这又是何种枪法?
但见一杆长枪被舞得银光闪闪,人却越离越远。
山贼们更是冥思苦想:哪家枪法是可以从十几丈之外远远攻来的?
“走!”堪堪舞至树后,丁青山将枪一收,拽起莫小雨回身就跑。
“嗯?”莫小雨一脸呆愣,被他拉得差点摔倒。
“前路不通,快逃啊!”丁青山急吼一声,索性将他连枪夹起,发步狂奔。
片刻后,兽大率先反应过来:“发什么愣,追!”
“竟敢使诈!”
“小子别跑!”
……
醒悟过来的众兽哇哇大叫,气急败坏地顺山路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