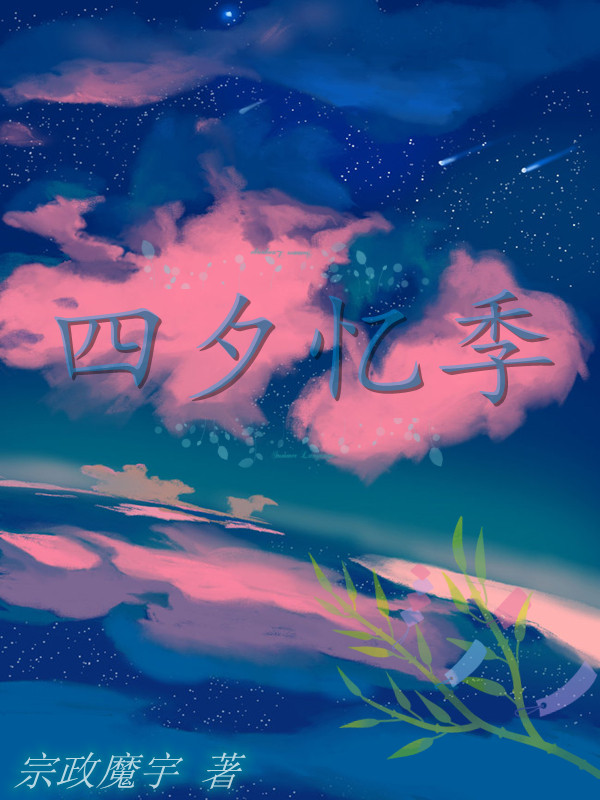这中华千年以来,常常便有人说,侯门一入深似海。这么说的,大都是循规蹈矩的老实孩子,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北京城虽有无数的豪门大院,但真正能说得上一入深似海的,满京城,只有一个地方——刑部大狱,天牢,那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入门,深似海。
这一日,又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有那新来的,刚刚一觉醒来,忽抬头,看见一张清秀的脸,顿时有些惊了。那人不信似的揉了揉眼睛,却发现,那张脸,愈发的清秀。
顿时心花就开了,那人一骨碌,翻身而起,隔着碗口粗的木栏就嚷道:“那边的白脸,你叫什么?”
谁料那清秀模样的人,对着叫声根本不做理会,呆了一呆,扭头回身,冲着墙壁躺倒,像是睡下了。
“嘿~,”那人抽了一声,又复嚷道:“老子叫你,没听见吗?把脸扭过来!让爷好好瞧瞧,瞧瞧你他【】妈【】的到底是男是女。真是绝了,想不到在这天牢里,还能碰见这么俊的!”
那张脸依旧没有转头,但一旁,已经有人接口冷冷问道:“新来的,安生着点,劝你莫要惹他。”
那人侧头一看,见是旁边牢房里一个白发白须纠结的枯瘦老头,他不禁一乐,“老头,你是见我新来,不懂这天牢规矩,是吗?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快刀飞腿赵大在外面,是何等威风!我赵大连清河知县都敢杀,今天想看看那兔爷儿的脸,怎么,不成吗?”
其实未等赵大说完,天牢里便轰然响起一阵哄笑声,有人还嘬唇吹了几声响亮的口哨。哄笑声中,便有一个声音大笑着说道:“如今这大清朝真是越来越不长进了,把天牢当成什么地方了?杀一个小小的知县,就够格进吗?!快刀飞腿?不入流玩意,也配在这天牢里过活?”
这话说的狠,赵大顿时心头火起,向着那声音来处怒叫道:“谁?有种站出来,老子跟你放对!”
那声音冷冷说道:“你猪狗一样的人物,也配和我放对?今日也就是在天牢,我卖王老一个面子,跟你这等废物多几句嘴。王老说的话,你给我记好了。你最好莫要惹那人!”
赵大生来一副暴脾气,最受不得人激,听那人这般的说,一怒便冲那清秀脸喊道:“那兔儿爷,给老子转过头来!让老子好好看看,也快活一回!”
话音未落,忽然从远角风声激荡,一物呼啸而至,登时打在赵大嘴上,顿时将赵大的门牙打的粉碎。
“再敢出言不逊,就要你的命!”那声音冷冷说道,自有一股威压沉沉压了过来。
见赵大捂住嘴,嗬嗬的抽着冷气,再不敢多言,一旁牢房里那个白发老者冲着远处拱了拱手,说了声“多谢!”
暗处那声音恭敬回道:“王老客气。忠臣义士,自然不能由人轻污!”
王老微微一笑,叹了一口气,自顾自说道:“到的这天牢,什么人,还不是慢慢混日等死……”
这时那赵大渐渐消停了下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不过略略说了几句,竟然惹来这么大的惩戒。赵大闷在肚里觉得难受,慢慢挨到那王老的牢房旁,小声的问道:“王老,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我想借问一下,那一边的人,究竟是谁呀?”
王老听赵大动问,呵呵一笑,“他是谁?他才名动天下,上至九天,下到阡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勇侠震古今,便是仇敌,也深深钦敬。你快刀飞腿,杀一个清河知县,便觉得已是天大的事情,你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吗?”
赵大听的心里有些发虚,弱弱的说了句:“不知道。”
“刺杀摄政王!”
王老这五个字一出,赵大噌的跳了起来,“刺杀摄政王?!”
赵大惊呼之后,便小心翼翼的望向那人,见那人依旧一动不动,面壁躺在稻草堆上。赵大的汗,一下子便布满了全身,把衣衫都打的透了。
“他是汪……汪……?”赵大隐隐约约记得这人,但急切间,却想不起来。
“难为你也知道。”王老叹惜的说道:“不错,他就是革命会党首脑——汪、兆、铭!”
赵大脑中嗡的一声,终于想起了这人是谁。一年前,刺杀摄政王案轰传全国。传言主事的,竟是同盟会三部长之一的评议部部长汪兆铭!
这汪兆铭,年少天才,不到二十,便夺了广州府县的案首,须知这案首,乃是秀才中的第一,小三元中的一元,许多人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得。后来,汪兆铭东渡日本求学,入东京法政大学研习法律,同盟会初创之时,便任三部之一评议部(司立法之责)部长,其后与梁启超等保皇党众人展开文战,文章恣意汪洋,文名逐步播于天下。其后数年,同盟会屡战屡败,形势越来越差,不少人心灰退出。汪兆铭心中激愤,便效班超,一把扔掉笔杆子,拿起手枪炸弹,相约一二同志,便潜入京师,欲杀摄政王而振奋革命精神。不料天意作弄,事泄被捕,下在这天牢之中。
若是到此为止,汪兆铭也不过一义士豪杰罢了。然而在追随汪兆铭进京之人中,有一南洋巨富之女,名叫陈璧君。其人爱慕汪兆铭才华,不惧万难,亦随在汪兆铭身侧。便在刺杀前夜,陈璧君对汪兆铭说:“君欲行此大事,我别无所赠。”便欲侍寝。但汪兆铭却摇头拒绝,不肯临死误人一生。其后被捕,生死不知之时,陈璧君买通狱卒,送来十数枚鸡蛋,中间藏有一书,尽言殉情之意。汪兆铭为其挚情所感,终于咬破中指,在信纸背面,血书了一个“诺”字!
这些英雄韵事,当日便轰传天下,赵大也曾在江湖上听人屡屡说起。此刻知道前面那清秀之人乃是汪兆铭,顿时有些懊悔。他本是一个粗人,粗人知错,便一下子站起身来,冲着汪兆铭那头大声说道:“汪先生,我不知是您,刚才言语冒犯,赵大这便给您赔罪了!”说完,反手就是两个大耳刮子抽在自己脸上。
听到这边动静,汪兆铭还是一动不动,躺在稻草堆上,仿佛这一切的事情,都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王老叹了一口气,正要开口,忽然天牢大门砰的一声开了,紧跟着好几个狱卒打着火把,急步的奔了进来。本来这天牢里黑漆漆的,只有汪兆铭所处牢房,依稀有些光亮。这些狱卒一进来,顿时便将天牢里照的亮亮堂堂。这一下由暗转明,众人都有些吃惊。有那待的长的,看架势,便以为又有人要被提到菜市口了。
不料等那些狱卒站定,外面悠悠然,进来几个人,那牢头前面恭恭敬敬的领着路,身后一个白须的富贵老人,迈着方步,悠悠的跟着,老人两边,有两个年轻人紧紧跟着。
看着这三人,牢房顿时叫声纷纷:“这不是肃亲王吗?今儿怎么有空,跑到这天牢里来了?是想看看老子还活着吗?”
“哟,杨皙子也来了。嘿,这不是北洋少主袁大爷嘛,今儿是什么风,竟将你们刮进来了。”
原来,这老者便是肃亲王善耆,那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杨度,字皙子,师从湖南大儒王闿运;一个叫袁克定,字云台,乃是北洋大臣袁世凯的长子。
牢头引着三人,一直走到汪兆铭的牢房前,见汪兆铭仍旧高卧,顿时有些着急,拍着木栏对汪兆铭喊道:“汪兆铭,起来,肃王爷来了!”
谁知那汪兆铭只是动了动身子,换了一个姿势,依旧躺着,口中却说道:“肃王爷活命之德,我汪兆铭铭记于心。但你我究竟道不同,你来,我自感谢,却不必相见。”
善耆还未说话,那边杨度已经开口说道:“精卫,莫不是已经不认得兄长了吗?”
汪兆铭不意这里有人能叫出他在东京的笔名,这声音又听得耳熟,他猛回头,却见是东京大学时的同学、杨度杨皙子!
汪兆铭翻身而起,大笑道:“皙子兄也想到来看望小弟了?”
杨度微微一笑,“你我同学,何必说看望二字。我此来,是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之命,与肃王一道,接你出去的。”
“不错!”肃亲王善耆点点头,“汪先生忠肝义胆,国之瑰宝,不能长久埋没在牢狱之中。本王今日便是奉命,来接汪先生出去。”
说话间,狱卒已经打开了牢门,又将汪兆铭手脚上的镣铐打开。躬身施了一礼,便退了出来。紧跟着后面几个小厮上前,搀起汪兆铭,走出了牢房。
这事来的突然,本是终身监禁,忽然就要出狱,汪兆铭虽然多才,但究竟没经过世事,一时有些茫然。那善耆等人趁着汪兆铭一时不知所措,半架半拖,不一会儿,就将汪兆铭请出了牢房。
牢门咣当一声关上,天牢便又是黑漆漆一片。众人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方才惩戒赵大的那个声音,响了起来:“王老,您觉得如何?”
那白发王老叹了口气,“多半是外面革命党人势大,朝廷抵挡不住,要借善耆,用活命之恩笼络汪兆铭。”
听王老这般说,那人沉默了一会儿,便又问道:“不过才一年,情势便逆转了吗?”
王老也皱皱眉,从一边抽出些稻草杆,掐成签子,随手在地上一抛,卜了一卦,那人像是黑夜之中能视物一般,急问道:“卦象如何?”
好一会儿,那王老才说道:“死中有生,生中有死,国势纷乱,十年一变。只怕中华的苦难,要从此开始了!”
那声音闻言,像是极为高兴:“嘿嘿,这乱世,终于要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