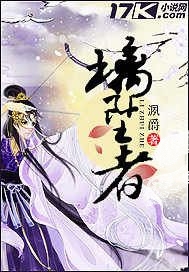堂前的大桌上摆着若干幅画轴,太原府最出名的三个媒婆把袁老夫人围在一起,时不时的推销着自己手中的女子。
“老夫人,您看这个,模样不错吧?手也巧,再看这身段,屁股大啊可以生儿子的。”
“老夫人,您应该看看我这个女子,是东门孙掌柜的二女儿,一听说您家大公子要找妾,马不停的就跑来找我,一定让我把着姑娘说给您。人家着品行可是能做正主的,不就是相中咱们家效儒公子的人品了吗?”
“你们两个的都不行,都太能干了。不知道老夫人的儿媳妇就是太能干?一定要找个端庄贤惠的,我这个啊,虽说不是大家闺秀,可也是小家碧玉,一定是听您的。”
……
紧跟着袁效儒而来的柳君眉还没有进门就被这阵仗吓了一跳,媒婆们纷纷将自己手中的画卷摆到老夫人面前,而且地下还散落不少。想来大户公子每一份婚事都是这么定下来的。若不是自己和袁效儒父辈交好,这场面肯定早就在袁府上演了。
君眉心里忽然想到了傅天翔,为什么现在都还不成亲,还嫌自己家来说亲的人不够多?
“娘,这些都是什么?”袁效儒气势汹汹的走过去,瞟了一眼画轴,“这都是什么啊,谁让您给我纳妾的?君眉挺好的,您请不要擅作主张。”
君眉听到袁效儒这么说,笑了笑,或许就是因为他这么维护自己,老夫人才更加想着百般刁难吧。
袁老夫人看着自己的儿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都不给自己好脸色,心里有些不满,又看到身后的柳君眉,火更大了。
“嫁进来这么长时间了,连个身孕都没有。你也老大不小了,还以为自己是二十二三的小伙子?什么都不在乎?你可以,我们不行,你看看我和你爹,操劳了一辈子,替你们四个兄弟挣家业,老了老了,连个儿媳妇都不能挑个自己满意的?连个孙子都抱不上?”
说着说着,老夫人哭了起来,抹着眼泪说,“我们马上都要入土的人了,这点事情都满足不了。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说是不是?”完了看着周围的三个媒婆,一起抹了泪,看着袁效儒还是没有反应,愈加嚎啕大哭了起来。
看到自己亲娘嚎啕大哭一般人是无法无动于衷的,更何况袁效儒虽面冷口毒,但君眉知道,他是一等一的孝子。袁效儒无奈的扶住老夫人,“娘,不是说这个意思。我是说好歹要告诉我一声,让我自己挑啊,我挑了之后娘在看还不行吗?挑个您喜欢的。”
“我喜欢这个!你不能娶她吗?”袁母指着画轴,“还有这个我看也不错。这些都是我看上眼的,你给我从里面挑一个。你挑不出来,我就不吃饭。”
袁效儒呆坐在桌子前,看着一幅幅美人画轴垂头丧气的,柳君眉端来水果,削好了一个苹果递给他,“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你垂头丧气的样子呢,你娘还真是威力无穷呀。看看有没有中意的,自己选一个。”
“好想和你没有什么事情一样,我还从没见过抢着给自己相公纳妾的娘子呢!”袁效儒埋怨到,顺势将画轴推到一侧。“你要找,你就自己挑!”
“哎,你说的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话不就成了我喜欢的了?”柳君眉叫过柳絮一起翻着画轴,这太原府的美人还真是多,一点不亚于苏杭,两个人一个一个翻着。
“姐姐,这女子我认识。是和我一起学武时的师妹。”柳絮拿起其中一幅画卷说道。
“是吗?”君眉拿过来看着,叶兰儿,模样不错,笑盈盈的样子,家世也算清白。“柳絮,这女子怎么样啊?”
柳絮笑着说,“我说不准,虽说是我师妹,可是我总和师父在一起,也不太了解。她对我倒还不错。我家里出事的时候她还给了我银子帮我呢。”
袁效儒听着她们两个的话,也拿来看看,至少用一个男人的眼光来看,画像上的叶兰儿的确很美,含情的眼睛,带笑的妆容,尤其是脸上若隐若现的酒窝,让人不由得想一亲芳泽。而且,这女子是母亲看上眼的。
屋子里柳君眉挑选着衣服,拿起了青色的,又放下褐色的。“明天要去看那女子了,穿的体面些。不过你也真是孝顺,你娘一喜欢,你就定了要选这个叶兰儿了?”
袁效儒看着忙里忙外的君眉说,“傻瓜,我挑选她是有别的原因。”看着君眉好奇的眼神,他接着说“我娘喜欢她那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柳絮认识她,是她的师妹。”
“这和絮儿有什么关系?”君眉猜不出。
"纳妾本来就已经难为你了。若是能选一个对你好点的那最好了。柳絮对你不错,如果那叶兰儿对你也好,我自然就满意了。如果叶兰儿有什么想法,好歹柳絮是师姐,也好说说她。不至于让你为难。”
柳君眉感激的看着效儒,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这么细心,为了自己才选择了一个女子。“效儒啊,你还害怕我这个正室夫人会被你的小妾欺负了?”
袁效儒走到君眉身边,郑重的对她说,“君眉,你我二人虽然只是有夫妻之名,但是却是好友,你是我的红颜知己,生活上能照料我,生意场上也能帮助我。"
"你说这话客气了,我虽是你的娘子,但却无法让你享受到琴瑟之乐,这是我亏欠你的。"
袁效儒摇摇头,“别这么说。我若娶了妾,就不一定经常能来陪你,你要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你要是有什么难处一定对我说,我袁效儒定会帮助你的。还有,不要再说休掉你的事情,我会替我找一个更好的人来对你。”
柳君眉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滴泪掉了下来,这是柳君眉第一次听到如此绵绵的情话,这情话与爱情无关。
桌上的红烛早已经息了,明天,或许再过几日,这屋子里的男主人就要走了,或者这屋子的女主人就要走了,就像并列的车马道,在某一个岔口,终会有一个离开。就此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