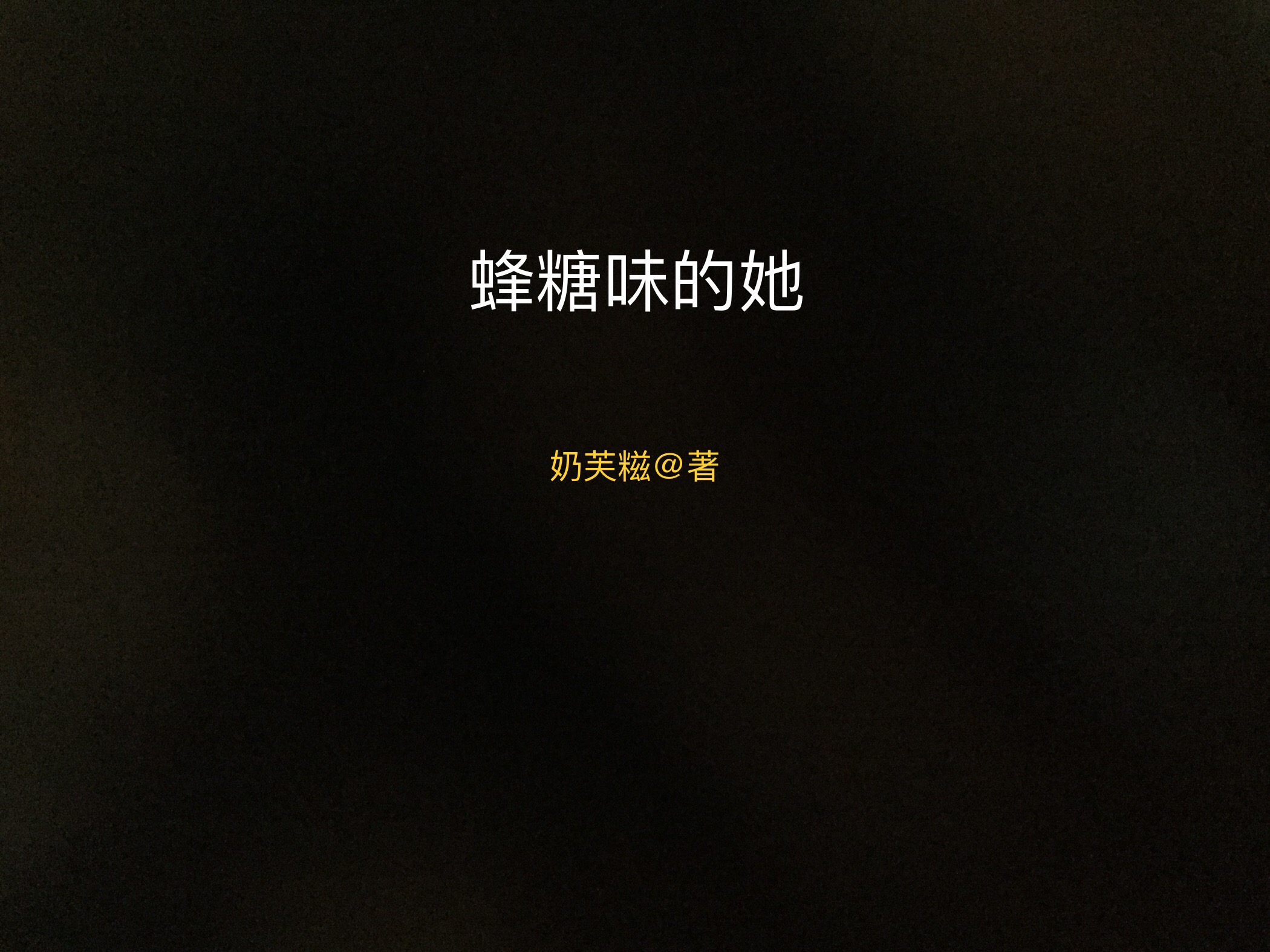白源鹤是这苏州的刺史,年仅四十便任此高官,在苏州可以说是一言九鼎。无论是钱还是权,他都具有,可他已经很久没有睡个好觉了。
“天知道,这些强盗是哪来的。”白源鹤在床上闭眼想着,“三个月便来一次,谁能受的了?”
“那些拥兵的州县一概不理,我这小小苏州,又哪里抵挡的住呢?”白源鹤翻身坐起,“哎,这也须怪不得我。”
看着远方火光四射,百姓遭受屠戮的哀嚎声传来,白源鹤内心感到十分复杂,他也曾立志为百姓做官,做一个“白青天”。可他现在竟然与土匪互谋,一想起这些,他的心理就会不安。
“朝廷?与那些江湖人士有何区别,今天党争,明天党争,闲的他们。”白源鹤心里鄙夷道,“江南道都出了个土皇帝,他那个真天子还坐的住?,要不是奏折上不上去,我又哪里会被人骑在头上?”
“我要保护我的家人和朋友,就算会下地狱又如何。”白源鹤自言自语道,随即又翻身睡下。
正当他闭上眼睛时,卧室的门被一脚踹开,白源鹤立马被惊醒。
“白刺史,您睡的可还好吗?”门外的人冷冷的说道。这人的声音虽是轻言之声,却掷地有声。
“你…你们是谁,擅闯刺史府,这可是重罪。白源鹤颤抖着,他的声音带着极大的惊恐。
“左散骑常侍,江叶。”门外之人道。
这踹门的是谁?不是旁人,就是这躲过强盗屠杀的江家父子。你看这江叶,披头散发,手中的长剑尚自流血,他江家父子从客栈逃出,路逢多批强盗,这强盗不是一般蟊贼可比,他们个个身怀武功。好教这江叶武功盖世,却也被划了几个口子。他二人来这刺史府,即是为了向这位苏州刺史问罪。
“原来是江大人,失敬失敬!”白源鹤松了一口气。“二位远到此处,鄙人未曾远迎,实在抱歉。”
“少废话,把兵符交出来,免你一死。”江叶将手中的长剑插入鞘中。
听了这话,白源鹤老大不愿,他这手中就只剩下五百残兵,全交出去,那不是成了光杆子的官吗?
“兵符不在我这,二位,请不要让我为难。”白源鹤阴阳怪气地说道,“二位,不要逼人太甚。”
只听嗖的一声,江旬拔剑而出,已是将剑架在白源鹤脖子上。白源鹤高傲的神情立刻转变,随之而来的是脸上的惊恐。
“还骗人,就你这人,兵符会不带在身上?”江旬怒骂道。
白源鹤看着脖子上的剑,心里虽想耍些花招,但看着眼前的两个人,他还是从枕头底下摸出了兵符。
“诺,兵符在此,但我奉劝二位,不要以卵击石,反误了自己的性命。”白源鹤一边说一边将兵符递了过去,他的脸色显得格外苍白。
江旬接过兵符并将它收了起来,又将剑从白源鹤脖子上缓缓放下。
“还请大人随我们走一趟。”江旬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没有大人,我们也使唤不了一众兵将。
“这…。”还没等白源鹤回应,只听江叶拔剑而出,向空中挥舞,剑在空中与铁器磨擦,发出刺耳的响声。
江叶环顾了四周,聚拢内力说道:“来者何人?,跟了一路了。不妨现身,鬼鬼祟祟的,好厉害么?”
“江大人,看剑。”
只见一柄长剑刺来,江叶挥剑相抵,那柄长剑在空中挥舞,突然剑转急下,刺向江叶小腹。正当这剑刺小腹三寸处,江叶剑锋一转,在空中挽了一个剑花,嚓的一声,两剑相撞,江叶已是将剑架在那人胸口前。这二人交手,只在一瞬之间,一旁的江旬刚要出手,看得父亲制服来者,却又将剑收入了鞘中。
“是你?”江叶淡淡地说道。“女土匪,武功倒不错,可惜轻功不行”
原来这袭击者便是半夜带人烧杀抢掠的女强盗,她一路跟着江叶来到这里,看见江旬取的兵符,便按耐不住,飞镖起手,拔剑而出。
可江叶,毕竟是江叶。
“杀…杀了我,你不会好过的!”女强盗叫出了声。“不,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谁指使你的?”江叶一边说一边将剑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是…是我自己带人来的。”女强盗颤抖着身子。
江叶冷笑了一声,将剑收了回去。
“那我来告诉你,是临安那个孙家的老**。”
听了江叶口中所说,这位女强盗一腿软了下去。
“我叫李离依,本无父无母,自小由山中的土匪带大。本来我们只扫荡十里之内的村子,后来一个更大的寨子兼并了我们,我因为武功好,就成了一个小头目,至于寨主…我是真的一无所知。”
“起来!”江叶放大了声音。“我最见不得女人哭哭啼啼的!”
李离依站了起来,脸上仍旧带着哭容。
江叶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想起了那个也喜欢哭的女子。心中泛起一丝涟漪,他摇了摇头,苦笑道:“我信你了,那你能不能叫你那些兄弟们停手?”
李离依抬起头看着这个突然柔声细语的男人,心里明白了些什么。
“好,但你要跟我过来。”李离依柔声道。
江叶转身过去对着江旬做了一个手势,又转身对着李离依说道:“走,快五更了!”接着牵起李离依的手,展开轻功,绝尘而去。
看着远去的二人,江旬看了看被暗器吓晕的白源鹤,又摸了摸身上的兵符,叹了口气。
他将白源鹤负在身后,也是施展轻功,向兵营而去。
“父亲,我马上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