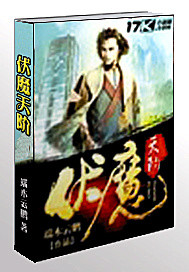韩伯忠带领窦成、韩成扬前往衡山祝融峰。来到峰前,好个南岳之巅,形如飞凤,四面峻峭,有诗云:“祝融万丈拔地起,欲见不见青烟里。”说的就是这祝融峰之高。
众人来到峰腰的上封寺,寺内方丈设茶管待,韩伯忠问道:“大师可曾听过江湖上有位武学高人,叫做祝融先生的。”方丈笑道:“岂止听过,祝融先生就在本山居住,与老僧交厚。”韩伯忠闻言慌忙站起,道:“大师,这祝融先生现在何处?”方丈笑道:“施主为何如此急着要见他。嗯,这个时辰,他想必正在雷池那儿练剑吧。”伯忠道:“既如此,有劳大师带领我等去寻,在下确实有要事,定要寻着这个祝融先生阿。”方丈闻言,换了衣帽,带领伯忠等人出了寺,来至崖边,见有一小石池,方不过一丈,深不过一尺。池侧山壁上有隶书竖刻一诗:
“上封峰头帝所宇,傍有雷池亘今古。去天五尺银河通,帝遣雷公宰云雨。我来正值秋雨时,再拜乞龙龙勿拒。快得此雨洗甲兵,免使中原困胡虏。”
原来相传此处每当峰顶雷霆怒发之时,这青苔满壁的石池上便会金蛇乱闪,暴雷炸裂,池旁有一洞,俗称风穴,使得此处风烟缭绕,涛声震震,故此地叫做雷池。雷池虽小,却是衡山名景,雷池虽在,却不见祝融。那方丈道:“咦,他怎么不在?不妨,我等去他家中寻他。”遂带领三人穿林过涧,来到山坳旁一座茅屋前,方丈上前叩门。
不多时门内出来一农夫模样的中年人。那农夫道:“原来是大师啊,快请。”遂将众人请到屋中,各自落座。那方丈道:“怎么令兄不在家里么?”农夫道:“大师也知,我那个哥哥性喜漂泊,浪荡不羁。时常几年也不回次家。上月刚回,这才几天,唉,昨日啊,又下山去了。”韩伯忠忙问道:“令兄去了何处,不知几时回来。”农夫道:“无非是八方游历,四海访友,也没个准子,不知几时回来。几位也是我大哥的朋友么,找他有什么要事,这般焦急?”韩伯忠道:“在下是镇南将军韩伯忠,只闻令兄之名,未曾会过面。这次找他是想问些京里的事。”农夫听后连忙施礼,道:“原来是韩大人,韩大人可是爱民如子啊,哎呀,我这却也没什么好东西款待...”韩伯忠道:“不必忙了,既然令兄不在,那我等告辞了...”
那农夫道:“大人别忙着走,方才你说要问我哥哥京里的事,他曾与我提过些,不知是不是那件大事?”韩伯忠道:“令兄说了什么?”农夫道:“我虽僻居山野,却也知道前些日子京城出了大事,听闻朝中有大臣作乱,是大人您把皇上救了回来。”韩伯忠叹口气道:“正是。”那农夫又道:“我大哥那时候确实是在宫里,他曾与我说,那晚皇城大乱,皇室宗亲全都陷在城里了,他却救了太子出来。”韩伯忠闻言跳起老高,问道:“他救了太子?那太子现在何处,没接来这里吗?”农夫道:“我也这么问他,为何不把太子接来,他说,后来知道事情经由,是侯爷救了皇上,本也想带太子回来,可太子却不肯,说什么不愿做太子,更不愿将来做皇上。要独自个隐姓埋名,漂泊江湖。这正合我那哥哥的性子,竟就由了他。唉,我这大哥,当真不知轻重。”韩伯忠听后低头沉吟,窦成道:“侯爷先别烦恼,我们既然知道太子还活在世上,这已经是大喜特喜了。只要我们尽力寻找,定能找的到。就算一时找不到,等那祝融先生回来,也一定能有些线索了。”韩伯忠点点头,向那农夫道:“令兄若是回来,烦劳您告知于我,到时再来拜访,多谢了。”说罢,谢别了农夫和方丈,回到衡阳城,一面派人北上暗访太子下落。一面亲自写帖,发给与自己交厚、忠正可信的各处诸侯将官,先不告知他们缘由,只是邀请众人赴会。
且说当时那延熙皇帝飘飘渺渺,昏昏沉沉,一缕魂灵出了城门,独自个正行走于荒郊草野之间,忽见前边有一对青衣童子,各手执白幡,叫道:“那人间的皇帝,随我这边来!”延熙走近细看时,那二童都是面白唇红,双目朦胧,褐发蓬松。当下口也不能言,身也不自主,跟在二童身后,跌跌撞撞向前走去。不知有多少时候,走至一座大城前,城门上写的是“幽冥界鬼门关”。青衣童子将白幡摇动,引着延熙进城,直至森罗大殿。延熙抬眼观看,殿上坐的十代冥王,是那: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仵官王、阎罗王、平等王、泰山王、都市王、卞城王、转轮王。两边列立鬼使判官一类,牛头马面之属。气氛阴森,一派肃严。
那正当中的秦广王道:“你便是阳世天子,延熙皇帝了?”延熙道:“寡人正是。”一旁的阎罗王拍案叫道:“是便是,不是便不是。在我等面前还敢称孤道寡,这是冥界酆都,不是你那皇城洛阳!”楚江王道:“就算在那洛阳,我等叫你三更死,你也活不到五更!”延熙听罢,慌得跪倒连连叩头。秦广王道:“我等乃阴司鬼王,他也是阳间人主,造化不差,休要再吓他了。”遂令鬼差将延熙扶起赐座,又命判官从司房中取出载有天下帝王寿辰的一册生死簿,翻到记有延熙处,该着六十一岁寿终。
与延熙对问无误后,秦广王道:“你阳寿已尽,正该今日赴我阴司。你生时,一世为君,无甚权谋,致使朝纲失统。但念你本性非恶,未曾做下甚害理之事,我也不教你受那十八层地狱之苦,便让你再转为人,生于村野,做一世平民罢了。但你来生若不安分向善,再见我时,管教你尝尝地狱之苦。有道是:莫言不报应,神鬼有安排。去罢!”延熙连忙叩谢,道:“绝不敢为恶,只是有一事敢问大王,我家室血脉可还健在,祖宗基业还能延续否?”秦广王道:“前些时侯,你一族中人已尽数来我这阴司点了名,或分入十八层,或轮回六道,早已处置毕了。只有你那太子阳寿未尽。旁的不归我管,不知,不知。”延熙听后双眼含泪,由牛头、马面押解,前往轮回投胎。走不多时,见一大山。怎样大山:
高盖昆岭,险过蜀道。阴云翻滚,黑雾弥漫。闻不见鸟兽语,只听得鬼魅嚎。望不清草木状,惟看遍阴邪魂。
延熙问道:“二位上差,此山怎地如此可怖,我等绕路走罢。”那狠牛头、恶马面听后怒喝道:“有我等在此,你怕甚么?此处乃是背阴山,须从这走,休再啰嗦。”延熙只得跟随二差走进山中,眼前黑蒙蒙山岩,耳边凄惨惨鬼泣。正吓得双腿发软时,忽觉肩头一紧,原来牛头按住自己停下了脚步。只见牛头手指前方说道:“哎呦!他...他...”延熙顺着方向望去,只见对面山岩小路上有一身穿黄衣的人影晃晃悠悠的行走。马面道:“啊!是他,快!”说着话两人分别抓住了延熙的双臂。延熙只觉双脚离地,耳边生风,随着牛马二差向着对面山上纵去。
一眨眼间已追到那人身前,牛头把铁锁在胸前一横,道:“小师父,你逃也没用,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回去罢!”那人一见如此,‘啊’了一声,闪身便奔,但脚步踉跄,显见甚是惊慌疲累。这时牛头、马面急追上前,又拦在那人身前,那人喊道:“让开!我要去见菩萨!”说着两袖一拂,牛头、马面脚下不稳,都被带了一个踉跄,那人在二差头顶跃过,拔足便走。
只见牛头站稳脚步,扬起头来一声长啸,啸声起伏,响彻山谷,延熙直听的毛骨悚然。不出片刻,阴风骤起,四面八方聚来无数阴兵,将那黄衣人团团围住。牛头、马面携着延熙走上前去,只见那黄衣人全身已被铁锁缚住,动弹不得,嘴里仍自不住叫喊:“放开我!我要面见菩萨!菩萨...”延熙细看这人,只见他乃是一年轻僧人,周身泛出金光,但是容颜颇为憔悴,一席黄袍破旧不堪,隐隐觉得他的相貌有些眼熟,似曾在何处见过。
牛头道:“小师父,你还是好好的回去等候罢。此事早已注定,你逃是逃不掉的。”又转身对马面说道:“兄弟,你带领阴兵一起押送小师父回去罢,好生看管,莫要与他为难。我自带这个延熙去投胎。”马面答应了,率领阴兵押着那小僧去了。牛头领着延熙转身继续上路。
延熙心中狐疑,只觉适才那小僧相貌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究竟在何处见过,便问牛头道:“敢问尊差,适才那位小师父是何身份?不知他所犯何事啊?”牛头瞪着眼睛道:“这是你该问的么?”延熙低头道:“是,是,原不该乱问...”走了片刻,牛头道:“此事说来奇特,反正走路无聊,便跟你说说罢。待你重投人世,也就甚么都不记得了...”延熙心中惆怅,嘴里说道:“咳,尊差请讲...”
延熙随着牛头转过了一个山坳,这条路上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寒风凛冽,耳边呜呜声响,摄人心魄。牛头说道:“那是数年之前的事了。那日和今日一样,我与马面路过这背阴山,正走间,听得前面不远处有呼斥吵闹之声,我们上前观瞧,驱散了围聚的饿鬼,只见黑石亭旁有一个黑大汉将一个僧人按在地上殴打,那僧人虽被人家按在地上起不得身,但嘴里骂声不绝,他便是刚才那个金光小僧,法名叫做金珠子...”
原来那天牛头马面在黑石亭旁见到金珠子和尚被一个黑大汉按在地上殴打,石亭下还站着一个女子。牛头、马面连忙上前,使铁链隔开黑汉与和尚,可二人火气不消,还要动手上前。牛马二差分别扯住一个,牛头见金珠子满脸是伤,问道:“这不是金珠子小禅师么,你不陪伴菩萨,怎地在此?”马面打量那黑大汉,只见他脸色青黑,面容丑陋,甚是凶悍。又转头看看那女子,只见她生的冰肌玉骨,美艳绝伦,正在一旁啼泣。遂问那黑汉道:“你们在这干什么的!”
那金珠子与黑大汉却不理会牛头马面相问,各自挣脱开来,又打在了一处。牛头马面见止他们不住,心中也是恼怒,忙唤来阴兵,众人一齐将二人用铁锁套了,连同那美艳女子,一同押往森罗殿去。
三人被带至森罗大殿,牛头马面向上告诉经过,十王一面差人去请地藏王菩萨,一面坐殿升堂。秦广王居中一坐,道:“这小僧,你不是给地藏王菩萨侍茶的金珠子么?一旁这二人是谁,报上名来!”那黑大汉道:“我叫百百罗,这个女子是我的老婆,名叫婆摩娑。”秦广王喝道:“原来是一对阿修罗夫妻。怎么如此大胆,敢在我阴司撒野!”男阿修罗道:“大王怎地忘了,昨日大王才判我们夫妇前去转世,仍入阿修罗道。”秦广王道:“既是如此,你等不快去轮回,却为何停留闹事?”那女阿修罗道:“大王容秉,昨日我夫妇等了许多时候,可那转轮却久久不开,执事的鬼差说,轮回道中雾气阻塞,走不得,教等候一日,我们便在背阴山下寻处歇息,我那丈夫在黑石亭子内睡了,小女闲来生闷,便独自游走,观看幽冥之景。不觉走到了一座云牵雾绕的殿阁之后,看见地上长着一片花儿,我见那些花儿长的奇特,味道又香,便忍不住采摘了几株把玩,却被这和尚远远的看见了,他满口说些难听的话儿,冲我走来。我慌忙逃走,他便追着我到了黑石亭,与我丈夫言语不和,这才打了起来。其实都怪这和尚蛮横,怪不得我夫妇。”那男阿修罗道:“这和尚辱人太甚,不过是为了几株破花儿,便说出那等难听的话来,不打他却打谁!”秦广王道:“如此小事,竟闹得这般汹汹。金珠子,你骂他们甚来?”那金珠子道:“那本是前些日,弟子奉地藏王菩萨之命,往九华山道场移来的茶花,此种世间少有,菩萨让我日日不离,悉心打理。如此栽培不易,今日却被这泼贱人偷去好几株。我要追上讨个道理,岂料在那阴山黑石亭,撞见这黑厮,他不问道理,见面便打...哼,话说回来,只是为了花儿便也罢了,恼的是那泼贱人,玷污了佛门宝阁净地。阿修罗于六道中虽也属上三道,但依小僧看来,实乃是下下等之物!阿修罗无端正,不敬神,男者至凶至暴,女者至贱至婬。此等秽物,岂容践踏菩萨宝地。故此弟子心中起火。”那男修罗听后大怒,喊道:“这贼和尚方才就是用这套言语侮辱我们。来来来,今日撕碎了你便罢!”说完便欲扑去,亏得众鬼差努力按住。
此时有小鬼来报:“地藏王菩萨到了!”十王连忙迎接菩萨入殿,备陈事由经过,菩萨拿锡杖指着金珠子道:“好一个愚昧的金珠子,难道不知为师因何要在这幽冥界常驻?既在阴间,怎有拒鬼之理?况且佛言众生平等,你既不思度恶扬善,却还怎可生这等歧视之心?救度众生,令离灾难。这乃吾之大愿?你,你可能知错否?”金珠子叩首道:“菩萨大愿,渡空地狱。是弟子慧根不全,现今已知错了。只是这黑汉殴打弟子,此气难咽!”那男阿修罗指着金珠子道:“你轻慢我等,还出言侮辱,就算你认错服软,我也难饶你。”一旁的女阿修罗也不心服,三个人各怀怒气,又争吵起来。菩萨诵念佛号,不再理会,向着十位阎王点一点头,又朝金珠子望了一眼。便驾着莲台,头也不回地出殿去了。
十位阎王喝止争吵,秦广王道:“金珠子你怪他重手打你,难消嗔念。阿修罗夫妇因他心中轻贱你,口中侮辱你,怒气难填。是这样吗?”三人同道:“正是。求大王辨个公道。”十位阎王又聚在一旁商议了一番,秦广王归座,皱一皱眉头,缕一缕胡须,扔下个令签道:“如今教你三人分别前往转世为人。那阿修罗夫妇,来世你二人还做夫妻,金珠子做你二人之子,敬重一生,偿你们这轻辱之恨,如何?”二人俱皆点头。
金珠子听后却是大惊,刚要开口。秦广大王又道:“金珠子,虽是如此,我也教他受你的刀剑,还你一条性命,以报这殴打之仇...”金珠子忙道:“大王,不...不了,我不再计较此仇了,还是让我回菩萨处吧!”众王尽皆大笑,秦广王道:“此事已定,断不能更改,这一去自有安排,不必再说了!”遂派四名鬼使先押着阿修罗夫妇前往人道轮回,那鬼使教二人分别投入转轮之中,谁知这二人乃是宿世的夫妻,情深意笃,又是智慧浅薄,不懂天道神奇。心里害怕这一分开,再也难寻对方,因此紧紧拥着,各不肯撒手。那鬼差强拉硬拽,定要拆开,可恼了这二人,推倒了众鬼差,依旧相互紧拥着,一起跳入轮回道中。
鬼差慌忙奔回森罗殿,禀道:“禀大王,那对阿修罗情愫难舍,不尊纪序,推翻了小人,拥在一块儿投胎去了。只怕这一去生甚差错,故此不敢不报!”十殿阎罗听后相顾失色,喝退了鬼差。一个个瞪着眼,张着口,颇为尴尬,堂下站着的金珠子见状,问道:“敢问诸位阎君,是出了甚么差错么?”那秦广王正自沉吟,闻听此言,忙厉声道:“谁说有差错了,此事...这怎能...不能更改!”随即派人将金珠子带下去扣押起来,只等时到投胎。
就是如此,金珠子已被扣押了数年,抵熬不住,趁机逃脱,欲求菩萨讲情。却被牛马二差撞见,重新押了回去,终究逃脱不过。
延熙听牛头讲罢,甚是感慨,忽然脑中一闪:“那画...那画...”
再说这一日,江南各地诸侯、太守应韩伯忠之邀,秘密聚集于衡山南岳大庙。韩伯忠在庙内第二殿的奎星阁摆下香案,设供一个“天”字。带领诸君叩拜已毕,诸君各自归座。韩伯忠站立正中,道:“诸位同僚,今日韩某邀各位到此,一则请罪,二则想和各位商讨一件大事。”众人道:“侯爷但说无妨,只是不知陛下近日来龙体安泰么?”韩伯忠闻言一跪在地,道:“韩某有罪,辜负了各位重托,陛下他病逝归天了!”
殿上登时大乱,众人吃惊不已。韩伯忠这才讲述了缘由经过:皇帝如何病故归天,自家如何寻访得太子讯息,打算联合众人以求光复朝廷云云...众人听后乱哄哄的交头接耳,其中有一个长沙太守阎宁说道:“侯爷这般说,教我等如何尽信,如今天下大乱,莫不是侯爷做下了这事,想用我等之力,图个自家的霸业?”当下也有几人出言附和。这话惹恼了一旁的公子韩成扬,成扬走上前道:“我父为这朝廷,费了多少心血。我父子在洛阳拼死救驾之时,旁人却在何处?这时出了事,竟这等猜忌侮谤,我看,只怕想图个自家霸业的,却是旁人吧!”
韩伯忠喝退了成扬,对众道:“今日韩某当着这个“天”字,想对诸位说些肺腑之言,韩某平素为人,想必天下皆知,今日所言更是绝无半分虚假。我为朝廷,肝脑涂地全不足惜,各位若是相疑,韩某今日便死在面前,以全清白。只求诸位,在我死后,结心一处,寻着太子,以保全我天朝江山!”说罢拔剑就要自刎,左右有许多人众上前拦住,俱道:“侯爷忠心,谁不知晓。只是事出突然,我等错想了。事到如今,还要仰仗侯爷主持大局啊!”那长沙太守阎宁也上来扶住道:“下官胡言几句,侯爷切莫...切莫如此。”
此时那韩伯忠泪如涌泉,冲着供天的香案又叩拜了许久才起身说道:“韩某怎敢妄谈主持,蒙诸位不疑,我已不胜感激,只求大家莫生异心,共图光复之事啊!”当下有人道:“常言道: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侯爷有德有功,远胜我等,你不做这主,谈何光复啊。”众人齐道:“还请侯爷主持大事!”此时有窦成上前,对众人道:“诸君请听小人一言,自从那张之翼作乱之后,在京都妄自称尊,意欲让天下归附于他,可他无服众之德,更无安邦之道。北方各地早已乱如滚沙,各地豪强俱怀异心,划分领土,相互攻杀,乱世之局已成。幸亏我江南各诸位大人,心怀忠义,又有韩侯爷主持大局,依小人看,大家应当结成联盟,奉侯爷为盟主,才能保全住半壁江山,所谓:合则成,分则败。当务之急,应先寻访到太子下落,有了太子在,北方人心必定归附,就算有人不附,那也只是散沙一般,诸位群雄联合,强若磐石,何愁天下难平,怎怕江山不复?”众人俱皆称善。
当下奉韩伯忠为盟主,议定一处有难,联合支援。诸君各回领地,整顿人马,设立城防。并各自秘派差人,身上携带妙手丹青画的太子相貌图形,分别前往天下各地寻访太子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