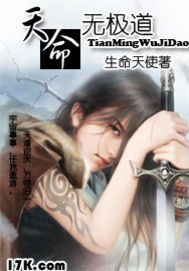一
“哗”的一声,坐在大石上的少年打开手里那把扇子,扑扇几下,清风微拂,他却觉着对这神扇太不尊敬,玩闹了片刻便又小心翼翼地合上
少年脚边卧伏着一只毛茸茸的小兽,皮毛是黄白相间,或伸伸懒腰,或眨眨眼睛,却绝不去打断主人的思考,乖巧极了
四周是一片森林,放眼望去尽皆树木,而且是普普通通,毫无特色的树木,一人便抱得过来的枝干,密密麻麻的宽厚的叶子,偶尔有蝉鸣鸟叫,清脆动人
他曾翻阅族谱,讲到这扇子的来历时,他的先人只用了寥寥数语概括:斩杀一凶兽,以其皮为扇面,以其骨为扇骨,以其爪为扇刃,制得此扇,戾气十足,有灵,自择其主,千年未有主
这扇子扇面无山无水,细细一看却有似肌肉纹理的天然纹路,倒真有来源于上古凶兽的可能,扇骨光滑似绸缎,轻轻一转便是流光溢彩,无愧流光之名
这便是流光扇
“小贼,哪里跑?”,隔着远远地突起一声怒喝,这一声中气十足,想来是一位四五十的中年男子,此处树木遮挡本应消去不少音响,这男子想必是个高手
少年左手持扇插入腰间,右手握剑,匆匆站起身来,眼里却有着些许兴奋:走了这么多天,终于遇上一个人了
从树林间第一个跃出的却不是他以为的中年男人,却是一个和他一般大,或者还比他小了几岁的小少年
那小少年一身白衣劲装,配红腰带,扎着高高的马尾,眼珠看人时先一转溜,寻常人一见便知此人必是个调皮捣蛋,不甚安分的货色,这小少年手里抓着一把破扇子,扇面是石竹图,词题于左侧,不知被什么武器连戳了好几个大洞,他只能看得个大概
那小少年却径直朝他奔来,从树枝上一跃而下,隔空虚踏几步落在他身前,他近看此人眉目清秀,竟生出几分女相,险些被这副皮囊镇住,回神见他伸手向自己腰间抓来,立时警惕不已,正欲拔剑相向,那小少年却是抓住了他的手,随后另一只手行云流水般扔掉了原本残破不堪的扇面,抽出他腰间的流光
“兄台,江湖救急,暂借此扇一用!”
流光不是凡品,原不能随意出借,但他已在这林中转转悠悠了十来天却还似在原地一般,实在需要一个识路的人把自己带出去,不然别说找回族中七宝,他所剩干粮仅供他三天饱暖,三天后他便是一命呜呼了,这时让小少年领自己出去才是真,流光借他一用又有何不可,况且看他面相,不似是穷凶极恶之徒
从林中陆续又跃出十余人来,带头的是一中年男子——刚才喊话的那位,这些人都打扮得一副土匪样,粗布条,大砍刀,他一看就全无好感
中年人挥刀向着小少年,“小贼哪里逃?今个儿你段爷爷我必将你挫骨扬灰,祭我二弟在天之灵!”
那小少年却慢悠悠打开扇面,打量了一会,又摸摸上头的刀刃,品评道,“扇倒是好扇,只是没什花色,不合我意,若是描上一枝红杏,这刃上再抹一点‘梨花雨’,那便是极品了……”,待看完了扇子,小少年似乎才有了余光去瞟几眼这些个粗鄙大汉,“家师曾与我解一词,叫做‘贼喊捉贼’,原以为做贼会心虚,更别说作这等引火烧身之举,如今方知,恩师所言非虚呀!”
小少年这一番话,不仅嘲讽了中年人倒打一耙,非英雄所为,而且文文雅雅,反显得对方狗急跳墙,咄咄逼人了
中年人冷冷笑着,“你毒杀我二弟,此等阴险手段,又有何资格与我论英雄贼人之辩,况且这里除了你我二人,便只剩我一干兄弟在此,这些大道理,我们兄弟的家伙什可听不进去!”,说着举起砍刀就向小少年直直劈砍而来
小少年合扇侧面接下,中年人占了朝上的势机,一把大砍刀光是看着便觉凶险异常,那小少年看似娇小羸弱,却不想也是个中高手,两人就此僵持不下
中年人身后的弟兄正待一拥而上,他却大叫道,“别过来,待我自手刃这贼人,段某闯荡江湖十余载,还怕了这小娃娃不成?”
小少年却是个停不下嘴的人,笑嘻嘻道,“这不还有这位仁兄吗?”
那姓段的中年人向他看了过来,“这位兄台与这小贼莫不是一丘之貉?”
这下他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看看现今局势,必是要择一方相助了,不然谁愿意替他带路,想起扇子还在小少年手里,自己又瞧得他颇合眼缘,左手抽出剑来,对准中年人身后的一干兄弟
那小兽见势不妙,“跐溜”一声钻进草丛中藏起来了
适才光说那扇子了,却忘了这剑也是一件难得的珍宝,剑身通明,没有特别的装饰,但剑的好坏自不是那等俗物添缀得了的,小少年见得这剑出鞘,寒光泠泠,脱口赞道,“好剑!”
那中年人见了这剑,也叹此剑乃平生所见,不愿兄弟一行再平添伤亡,之前想着凭一己之力擒住这小少年也是这道理,如今他横插一脚,中年人便退缩了,想着自己以后再找这小少年也不难,君子报仇,端的是十年不晚!
“兄弟们扯呼!”,中年人退出,原本便是他的刀压着小少年的扇,这一撤倒也容易,只见他纵身一跃,便轻巧巧落到树枝上,距地足有十多尺,实是惊人,一挥手,那一帮弟兄便如虾米游入远海,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少年再抬头看时,那中年人也已没了踪影
他收剑入鞘,突然觉得一件软软的重物压到自己背上,急欲转身时,那小少年的脸贴着他从后方探出来——原来是他攀上了自己背部,还咿咿呀呀叫着痛,“哎呦,这儿好痛!那儿也疼,兄台好心,不如背我一程吧?”
那小兽也趴在小少年的背上,如今一看,倒像少年背着小少年,小少年再背着那小兽
本来也是要跟着他同行的,如今他自己提出自然更佳,不然他都不知如何开口是好,稳稳地背住了小少年,“你千万别睡着的,否则会掉下来……”
两人一问一答地便聊起来了
“兄台经常背人吗?背得这么熟练……”
“嗯……家里有几个小孩……”
“结亲了?我看兄台年纪也不大嘛!”
“没有……”
“哦,那兄台叫什么名?我们交个朋友,总叫你兄台也不大合适……”
“我吗?我叫……刑九”
“刑九?刑兄高义,小弟……飞鱼……”
二
有了飞鱼指路,刑九这个路痴终于顺顺利利地在两天后找到了一间酒馆
这酒肆开在荒郊野外,门前四个大红灯笼,上书“樵家酒馆”,屋里摆了许多木桌木椅,一个客人也无,靠着墙角砌了一排烧着旺火的砖头,刑九走近点一看,里面蓄着热水,暖着小酒呢!
他自己嘀咕着,“这馆子好怪,天又不冷又没人,却暖着吃食……”
“刑兄此话差矣,我们兄弟二人难道是山野里的孤魂野鬼不成,掌柜的!掌柜的!来几个小菜!再上半斤酒!”,飞鱼手握流光,从刑九背上跳下,伸伸懒腰,拉过长凳就坐下,“不知刑兄可愿陪飞鱼一解千愁?”
刑九有点犹豫,慢慢坐下来,临行前长老们给了他满满一袋银两,说这是外面才会用到的,无论拿别人什么东西,都要先给这个,神婆临行前把他拉到一边,叮嘱他道,“到了外头,不管别人要你多少锭银子,你先砍一半,他要是轻易允了,你就再砍一半,一直到他拖了一柱香也不肯再少要时,你就答应他,懂了吗?”
“樵家?这户人家当是以砍柴为生的……”,刑九这样想着
那只小兽跳上桌来,飞鱼只觉着它毛茸茸的好玩,招手唤它,“毛毛过来,快过来哥哥这里……”
刑九揪着那只小兽的脖子就把它提起来,它也不挣扎,眼珠子盯着主人,通人性似的摇了摇头
飞鱼看不明白这一人一兽的眼神交流,就把头趴在桌上,侧着脑袋想一探究竟
“二肥,快吐出来,你不吐就别想回族里了,我把你一只狼扔到垃圾堆里去……”,刑九和它平视,假意威胁
“它它……它是狼?”,飞鱼很是惊讶,他没见过狼,但从书本里也看过,狼……不应该是“足有三岁幼童之高,凶狠残暴,伺机而动,扑食兔犬,撕皮扒肉,饮血吐骨,嚎嚎月明,鸟雀夜惊”的吗?这个小不点儿……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刑九一遍,“刑兄怎么瞧……都不像会说谎的人哪……”
二肥心不甘情不愿地被送回桌面上,爪子上下拨动,好像人在运气一样,过了一会,它的肚皮突然鼓起,整只狼被撑成足有原来的两个那么大,张开一张大口,骨碌碌地滚出一个红底绣花袋和一青花小瓶来,这绣花袋就是刑九的钱袋了
刑九拉开钱袋,不确定地看向飞鱼,“不知鱼兄适才叫的菜要多少银两为好?”
“诶……对了对了,你不说我都忘了,掌柜的!”,飞鱼扯起嗓子又叫了半天,喉咙都快哑了,还是没人答应,他拉拉刑九的袖子,“唉,刑兄,这……这儿不会闹鬼吧?”
刑九似乎是习惯性地摸了摸他的脑袋,“乖,没有鬼的……”
飞鱼愣了,他……他还是第一次被人像个小孩子一样哄着呢……不过,他想起刑九说过的他家里有几个小孩,就知道他只是把自己当成他的什么侄子侄女之类的了,心里释然,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鱼……鱼兄,你不是识路吗?这间馆子你……没来过?”,刑九突然发现一件重要的事,两个不认路的人,这下可怎么办?若这儿真是一间空着的馆子……他们还能偷了那里的东西顶几天的肚子不成?
不……不能偷的,族有训诫,偷为不劳而获,害人钱财,是不义之举,不可为之……不可为之……
飞鱼怪异地瞧了他一眼,从怀里揣出一个小罗盘来,“我是不太识路,可是我懂方位呀!夜观星象,众星所拱之为北,磁针指南,日出于东,中则昃,夕薄之西,这里是西蜀西南方,只要一路往东北,总不至于……走错吧?”
刑九指着那个罗盘,他一路见飞鱼拿出来对了好几次,原来是靠这个,“这是什么?是会认路的吗?”
“刑兄,你是从哪里来的呀?”,飞鱼已经相信他是这南疆中某个小部落里的蛮人了
“你这个要多少银子?可以给我吗?我……从小就不记路,你能教我用吗?”,刑九扒拉着钱袋,他是真想要一个
飞鱼直接把罗盘塞进他手里,然后从怀里又摸出一个新的来,“一个罗盘而已,刑兄你想要我便送你了,反正我出门时从二师哥那多拿了一个,你看这个指针,不管你站哪……”
他把自己手里的那个来回转了一遍,“你看,它指的都是南方,你面对着南方,左手就是东,右手就是北,往后走就是南,懂了吧?”
刑九拿着那个罗盘,有点不知所措,外面的东西不都是要用银钱换吗?那现在他这是怎么回事?
“哪边是右手?”,刑九不知道的东西多了去了
飞鱼差点崩溃了,他耐下性子解释着,“就是你拿剑的那只手,另一只叫左手……”
刑九似懂非懂地举起自己的左手瞧了一会,“我懂了……”
飞鱼没有注意他使的是左手剑……
“喂喂,你们两个,刚才不是要上菜吗?现在怎么做起买卖来了,我可有话在先,我这店里唯一能做的买卖就是姑娘我的酒!你们不买我的酒,就麻溜点给老娘滚!”
两人聊得忘我,这时才发觉一个姑娘正站在桌边,绑着头巾,穿着暗红小袄,挽起两边的袖子,脸蛋倒是不错,要是打理一番,也是秀色可餐的一位佳人,只是她显然没有一丁点要打理的意图
飞鱼打开扇子扇了两下,赔笑道,“姑娘切莫生气,老人们常说,怒则衰,乐而殊,姑娘本倾城之色,何自苦如是?”
那姑娘却不领飞鱼的情,“哼!像你这样的花花公子,姑奶奶见得不算少!我色衰色殊干你哪门子事?就算我年老色衰,我当家的都不敢有二话,轮得到你来管!还殊色殊色,当心你哪一天就殊死(殊死:古另称斩首之刑)了!快说要什么菜!不要就快点走人!”
飞鱼合上扇子,倒也没多介意,“小生适才要半斤酒,再添几个小菜!”
“几个是几个?要是任着我来信不信我就给你来十个!”,这姑娘脾气火爆,一点就着,现如今看起来还没灭呢……
“三个吧……来三个……”,飞鱼见刑九一个劲地盯着袋里的钱,对他要什么菜好像一点异议都没有,全凭他来的样子,估量着要了三个
“那客官您就委屈您的贵体稍等一会吧!我家的灶台只有一副锅铲,两个伙计兼掌柜,不过酒嘛……你自己到那边拿,老娘不伺候你!”,她转头往后院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嗓门喊着,“来客人啦!炒三个小菜!下酒填肚子的!”
飞鱼“呼”地长吁了一口气,拍着刑九的肩膀说道,“总算能吃上一顿好的了!多少天没闻到酒香了……”
刑九从他的钱袋里抬起头来,“什么是酒?”
三
刑九扶着醉醺醺的飞鱼,跟着樵女来到楼上的客房
“真是不公平……一点也不,为啥刑……刑兄你……不会醉呀……”,飞鱼一边抱怨着,到了房中,樵女已经为他们备好了洗脸的冷水盘,桌案上还有一碗冒着热气的醒酒汤
刑九把他放到床上,想去把毛巾冷一冷替他降降酒气,刚触到汤盘里的冷水,禁不住浑身一哆嗦,“好冰啊……怎么这样冷的水?”
话接上回说起,刑九没听过“酒”这种称呼,却并非不懂酒,事实上,在他们那,酒不称酒,唤作“火汤”,火是五行之火,汤是药石煎汤,他们餐前先饮火汤一碗,除寒保温,连三岁小孩也不例外,这回出来神婆又说了,外面没有族里的“火汤”,所以制了六瓶所谓之“流火”的药丸,融于水中即成“火汤”,一粒可稀三碗清水,如此要他定时“喝汤”
“外面真的和族里有着天壤之别呀……神婆婆说的到现在一个都没灵验……”,刑九叹着气,他想回去了
啊……不行不行,他要找回七宝的,“七宝,七宝……”,他默念着,给自己打气,“对了对了,流光!得找鱼兄拿回来了!”
飞鱼醉得一塌糊涂,他的扇子是樵女替他拿上来的,如今放在醒酒汤旁
刑九走到案边,端起汤碗,勺子轻轻搅了一会,放到嘴边吹了两口气,自己试喝了一点,“还行,不过还是有点烫,先凉一会吧……对了,流光收起来先……”,他伸手就要去碰一旁的流光扇
“噔……”,飞鱼被这突如其来的刺耳响声搅醒了一场好梦,但酒劲还没消,眼皮都没睁开,昏昏沉沉又睡了过去
刑九的左手上,青紫的一片,经脉隐隐约约显现出来,描出血红得不正常的一笔笔脉络,他累得一屁股坐在床边的地板上,靠着床柱,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他没想到——千年无主的流光认主了,认了现在躺在床上的那个醉鬼为主……
族中有九宝,他手上的剑就是其中之一,若是宝物认了外人为主,族人再触之,便有如祭泉之痛楚,现今该如何是好?他一宝都没来得及找回,这就先丢了一宝……
他早说自己带着流光出来也没用,可神婆婆偏偏要他带,还神秘兮兮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万物自有定数”
“除非……除非宝物所认之主身死……”,刑九拉下袖子,内力运于奇经八脉间,把窜入体内的毒素聚于血流中,“呲”的一声,他的右手食指尖迸出一道口子,一时黑血如注,“不行不行,族有训诫,杀人夺命,乃伤天害理之举,切不可为……不可为……”
床下垫鞋用的毯子上,染上了一大片乌黑,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在四周
二肥慢慢溜过来,吐出一卷白缎
“怎么办?该怎么办才好……”,刑九扯下一截擦拭干净伤口,盯着床上呼呼大睡的飞鱼,还是决定先喂他喝下醒酒汤,至于流光……再做打算吧……
“客人歇下了吗?”,外面传来敲门声,叫门的却是男声
应该是樵女的丈夫吧……刑九还没有和这位老板见过面……
他走上前去,打开雕花木门,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在门口,长相只能说是一般,或者说是平凡应该更为贴切,“樵兄可有事?”
“无事,只是刚才经过这里,闻到屋里传来一阵异味,恐贱内大意,没除净一些虫蚁朽烂之处,扰了客人的安宁,这……这位小兄弟可有大碍?”,他看见床上的飞鱼
异味……莫不是指他刚才排血逼毒时的血味?这老板的鼻子也太灵了点吧……
“没有大碍,很干净……”,刑九想着,待会要不要偷偷打桶水,把毯子给人家洗好了……
“那客人睡吧……”,男子也没有什么疑心,只是临走时看了一眼他的袖口,刑九被这一瞥弄得挺不自在,好在他只是看,并没有说什么别的,刑九合上门又来到飞鱼身前,其实就算没有族规,他也没法对一个与自己无冤无仇,也并非恶贯满盈之人下手
他坐在床边,把飞鱼扶起,让他靠在自己身上,手里端着汤碗,照例先自己试一遍,吹一会,等到凉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喂下去,有时汤药从嘴里流出来,他就把碗放在底下接住,外面月影西斜,才好歹把一整碗一滴也不漏地让他咽了下去
刑九把空碗放在一边,现在去叫醒樵女他们夫妻二人来收拾碗筷也不太好,屋里只有一张床,酒馆里也只有一间客房,他只能坐在那条毯子上,把头枕在床板上草草睡了一夜
山林里落了雨
这几天来,飞鱼第一回睡到了真正的床上,又因为和刑九较劲喝了个烂醉如泥,再加上刑九灌的那碗醒酒汤化去了酒力,这一觉睡得真是踏踏实实,安安分分,五更天时就醒了过来
看见刑九东倒西歪地躺在床边,他松了一口气,伸伸懒腰,捡起掉在地上的流光扇,推开窗户,“昨日喝得是过分了……”
“晨曦初露,玉秀其间,月魄留影,日照乍临,蔼蔼云峰,霏霏林雾,伊人入室揽芳馨,映映莲子心……”,林间踱步过来一对男女,男子手里挎着个篮子,小声哼着歌谣,走走停停,在树下挑挑捡捡摘蘑菇,一边自言自语,女子背着个竹筐,筐里满满的刚砍下的木柴,左手提着一捆用藤蔓绑好的细长树枝,右手拿着把斧头
女子就是樵女
飞鱼摸摸自己的脸,房里正对着窗户是一面大铜镜,他回头对着镜子仔细瞧了一会,看看流着哈喇子呼呼大睡的刑九,又看看樵女的丈夫,“我怎么看都是长得最好的那个,她怎么就偏偏对我没有好脸色……”
这时他们停下来了,樵女把木柴搁在地上,左手抽出一条手帕来,她的丈夫比她高上半个头,他就屈下膝来,樵女很温柔地替他擦着额上的汗珠,他用另一只手顺便提起了放置于地的木柴
樵女把帕子收好,伸过手去像是在问他要回来,做出小女儿家嗔怪的姿态来,她的丈夫则是摇摇头,篮子架在手臂上,空出的左手就去牵她的右手,樵女好像挣扎了两下,左右顾盼害怕别人看到,当然没有见到飞鱼,但飞鱼很想凑个热闹……
“两位‘伙计’真是恩爱呀!”,飞鱼手撑窗台,一个翻身从窗口跳出去,也不闪躲,径直向那牵着手的二人走去
他那声是喊出来的,樵女很快就看向他来,脸上的表情由羞转怒,她似乎对着她的丈夫说了什么,他转过身来,还是紧紧牵着他妻儿的手,却不像樵女那样恼怒,而是微微笑着,好像活在这里,就很满足
樵女半个身子藏在她的丈夫身后
或许飞鱼是有点嫉妒,嫉妒这份岁月静好……
他想到,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陪伴终老,熬过这漫漫余生,东篱野菊,南山悠然,也还不错……
四
酒馆里
这个小馆子有着一个家所有的一切,丈夫、妻子、孩子,虽然这些都不是飞鱼的,但他觉得,这里实在比万洲门好多了,至少不是一群大老爷们尽在舞枪弄棒,一个陪着唠嗑的人都找不到
“这儿真暖和,乐不思蜀呀!我都不想回万洲了……”
“这里就是蜀州……”,刑九出门前背下了外面的地名,可惜治不好他的路痴……
“好好,我是乐不思‘乔’了……”,飞鱼心情正好,也不和他一般见识,挑逗站在一旁和丈夫依依不舍的樵女,“樵妹妹,上壶酒,哥哥不想走了怎么办?”
樵女一个好脸色也没给他,“呯”的一声拿过柜上的酒壶砸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哝,酒,我男人酿的,得贵一点,二十个铜板,准保不掺水”,转头却又温情脉脉地对着站在门口的丈夫——如果这不能说是“花枝招展”那人间就只能说是一片荒芜了,“快去吧!我和冉冉等你回家……”
“我去去就回!”,飞鱼看着樵兄回给他的妻子一个类同的浅笑,背着一个大竹筐离去,一步三回头,竹筐上盖着一层白布,飞鱼他们不知道里头装的究竟是何物,而且他们也没兴趣知道
“鱼兄,我们不能跟着樵兄一起走吗?他比我们识路,也能相互帮衬一二……”,刑九看着飞鱼,心里断定他的酒疯还在发呢……
“刑兄,来,我敬你,敬你的好酒量!”,飞鱼答非所问,大碗满上,“饮完我们就启程,到时去追樵兄也来得及!”
刑九犹豫不决,他们刚吃完早饭,“火汤”是饭前喝的,“我家里人说……”
飞鱼哪里听得了他的长篇大论,直接上手按住他,把刑九弄了个措手不及,一碗给他灌下去,“咕噜咕噜……咳!”
“你还算不算是个男人,我们要的……”,飞鱼接连自饮三碗,拍拍刑九的背——他刚才险些呛住了,现正扶着桌子猛一顿咳嗽,“就是大口喝酒,大碗吃肉!”
“蠢货……”,樵女抱着她儿子走近,把案上的酒壶收走,“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对……对对……”,飞鱼渐觉头晕脑胀,不对劲……他酒量可没这么差,“你怎么……把酒拿走了?”
彻彻底底晕死前他看到樵女露出一个预料之中的笑容来,心道,“大意了,中计!”
“确实没掺水,可是我掺了蒙汗药……”
刑九是第一回出远门,飞鱼何尝不是,是故他们根本没想过:这荒郊野外,再过半里地就是匪窝的人烟稀少之地,如此突兀的一间馆子,究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是匪寨据点无疑……
飞鱼醒来时,正和刑九背对背绑在一处,两个人被塞在桌底下动弹不得,段律,段老大那张脸就在离他们不过三步远的地方,身边三四个小弟,人尽藏在橱后,和樵女在一块说着话,此时夜色已深
“我师兄说,鬼寨最秘密的就是这个五当家了,男女不知,年纪不知,样貌不知,武功路数不知,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哪……”,飞鱼想起二师兄给自己的消息,说鬼寨五位当家,其余四位姓名画象俱全,独独缺了老五的,杀人越货从没她的份,却原是个看门望风的,“我本看着你丈夫秉性淳善,不争世事,以为你们俩是隐避世外的居士,不想土匪窝里也能出个白净净的伪君子,嗯……你从哪抢来的压寨夫人?”
“你说我不要紧,我娃娃他爹可是正正经经安分守己的小老百姓……”,樵女的死穴有二,丈夫为一,儿子为一
“呵,就是他还不晓得自己娶了个土匪头子喽!”,飞鱼记起一早樵兄出门时说的似乎是“去去就回”?听樵女语气,她定不愿让丈夫知晓自己的事,这或是个逃跑的出路
老江湖段律看穿了飞鱼内心的想法,“四妹,妹夫怎么办?”
“还是叫我老五吧!冉冉他爹在睡,今晚的菜里我下了点料,不会那么容易醒的……”,樵女估摸着时辰,“老大,你们来得也忒晚了,算了吧!扮作客人在我这歇下脚,那两笨蛋就晾在这,天亮你们再带他们走……”
飞鱼似自言自语,“女子有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哎呦!”
却是樵女一脚踩上飞鱼的鞋面,还用力来回踏了两下,“你咒谁呢你!老大,就是这个小贼吧?”,樵女光看着他那张脸就能把所有好心情都败得一干二净,“把老二毒死了,害我从老五变成了老四,知不知道‘四’不吉利呀!”
“托我的福,让你升迁,你这是恩将仇报不是?”,飞鱼希望樵兄晚饭吃得少点,别让这母老虎再在这肆无忌惮地虐待他了,“喂,你孩子他爹出来了!”
说句实在的,飞鱼本意只是想吓吓樵女
可老话不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飞鱼的嘴就是惹祸的乌鸦嘴……
帘后的内屋传出一阵婴儿哭闹声,然后是一阵铃响,光突然亮起,窸窸窣窣披衣裳的音响,樵女的丈夫抱着孩子提着油灯出来了,“孩子娘,你是在解手吗?冉冉饿醒了……”
“惨了!”,樵女一拍脑门,“他晚间是到城里吃的!”
“樵兄!”,飞鱼趁机放声大叫,“你家的母老虎吃人肉啦!”
但是……抱着孩子四处游荡的这位“樵兄”始终一动不动,仿佛飞鱼根本没有发出丁点声音来,他颇有君子风度地仍然候在屋外,不远就是茅房,时而轻轻唤一句,“冉冉娘?你好了吗?”
飞鱼卖力地喊了一阵,围在他旁边的一众匪徒却完全是任由他乱叫,一点制止的意思都没有,段律古怪地看着他,好像他做的是什么不理智的事一样,飞鱼也逐渐察觉了这股尴尬透顶的氛围,声音越来越弱,“樵兄……樵……”
“冉冉娘,孩子哭得可厉害了,你是不舒服吗?”,“樵兄”走到另外一张桌边,掀开锅盖,盛了一点隔夜的米粥,叹息着准备给怀里的孩子喂下
飞鱼差点就想喊他:你以为的里面又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是你孩子他娘,你直接闯进去不就得了,磨磨叽叽个鬼!
“冉冉爹!”,樵女在段律的生推硬拽下终于出去了,看着丈夫疑惑的神情,她思量了一会,把冉冉抱过来,“你先睡吧……我这就给儿子喂奶去……”
樵女的丈夫头脑简单,也没问妻子去了哪里,一句话就被哄得要乖乖回屋了
这下飞鱼和刑九唯一一根救命稻草……断了——连根拔起的那种……
飞鱼推推刑九,“刑兄,想不到我们俩死在了一块,我今早说的话不算数了,虽然有你陪我也好,可我……还是……师傅,大师兄,二师兄……”,他说着说着动了感情,刑九却似不为所动,“扼”的一声从他紧闭着的嘴里发出,刑九张开口,一道血从嘴角蜿蜒而下
——他咬破了自己的唇
五
将要走进内屋的樵女丈夫动了动鼻子,在隔帘前停下,“冉冉娘,你受伤了?”
他把那只狗鼻子凑进樵女和她抱着的冉冉,从头到脚嗅了个遍,“不是你们……”,然后开始向屋里其余地方搜寻,循着血腥味慢慢靠近几人藏身的角落,眼见段律惊慌失措,飞鱼对刑九这招出奇制胜佩服得不得了,“刑兄,这招高!”
樵女忙拉住自己的丈夫,假咳两声,眼珠子滴溜溜转上两圈,“冉冉爹,我……我还是不瞒你了,今早走的那两个华服公子,就是城里通缉令上的土匪,段律和胡旮……”,她见自己的话果然拖住了丈夫,趁机在身后打手势让段律速速离去,段律即刻叫上那几个小弟,押着飞鱼刑九摸黑从后门溜走,樵女的话还依稀能听见,“他们把杀来的人肉人血藏在咱们家了,我正要处理掉呢……”
“那赶紧报官吧!”,樵女的丈夫被吓得不轻,“怪不得,我之前就闻见这血臭味……”
“你别急,先去歇了,明儿一早我就进城去和官老爷说这事……”
出来就好办了……
段律几人远远离开樵家酒馆,对这两个半大的孩子——至少相较于他们来说是这样没错,慢慢放松了许多,认为那绳索结实得很,他们的剑和扇子又被收在自己手里,还能掀起什么风浪来?他们一路向深山中的鬼寨走去,一边议论着要将他们的头颅砍下,祭前二当家的在天之灵
可段律不知道,樵女也没和他说,一起来到酒馆的不只有他们二人,还有一只发育不良的二肥
转过一片山林,山道贴着峭壁极尽所能地缩短了它的影子,鬼寨就建在这得天独厚易守难攻之地,段律没好气地提醒身后的手下把两人抓紧,别掉下去了,飞鱼隔着朦胧夜色,被这仅供半人过的险路和下头黑蒙蒙的无底悬崖惊住了,刑九却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一声响亮的口哨在黑暗中鸣叫,宛如人临死时凄厉的哀嚎从地府唤来了索命的黑白无常
段律不愧是鬼寨的带头大哥,率先镇静下来,“莫慌!别被他乱了我们的阵脚!”
话音刚落,押着刑九的那个匪徒就觉着什么东西从脚边攀上了他的脖子,随即脖子一痛,叫出声来,瘫倒在地,原是二肥一道跟着主人的气味爬上山来,听见那哨声,便得令来救主人
“你!”,段律气急,“三狗子兄弟!你……你这是什么暗器害人性命!”
说到杀人,刑九挣脱绳索,这黑锅他不背,“二肥不会杀人的,它咬死了人是要被拉去祭泉的……”
段律睁大眼在黑暗中仔细看看,三狗子果然又从地上爬起,只是还捂着自己的右脖子,但伤势并不重,“看来你倒慈悲,三狗子,你过来我这边,从左边来,那两个小贼堵在右边……”
这伸手不见五指之地,他却随随便便说清了众人的方位
“看来……二师兄知道的还是少了点,没想到……你竟能夜视!”,飞鱼在刑九的帮助下解开束缚,不觉赞叹,在这一片漆黑里,纵使他们有千军万马,也是两眼一抹黑,形同虚设,轻易就能被段律擒回,但……段律可不只他一人,还有一群拖后腿的手下呢……
飞鱼往身边一抓,拉住刑九的手——他感觉得出来那就是刑九,往山崖下跑去,幸好他们并没有过那个惊险的弯道,否则回头时恐怕得费好大一番周折,把在黑暗中撞到的其他人尽皆推开,飞鱼料定,段律不会不顾那些人的生死,必得折返去救人,这样他们逃脱的胜算就能大大增加
“鱼兄,我们是不是太……”,刑九心有愧疚
“你傻吗?”,飞鱼反过来训斥他,“他们是土匪,每个人手上的人命比你我加起来都多,死了算数,将来阎王爷的功过簿里,我这还能说是积德行善之举呢!”
训完后他默了默,又解释道,“我有分寸的,他们死不了,再说还有段律在呢……”
“你是在骗我吗?”,刑九很认真地思索着
“你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骗你干嘛!”,飞鱼气鼓鼓地,“你又留意到了什么?”
“我在想,那人……我指的是樵兄”,刑九一边被拉着拼命地跑,一边剖析着,“他理应是……聋子……”
飞鱼惊讶之余步伐加快,“怎么会?之前我们刚来时,樵……不,是五……呃,死(四)老虎她明明叫得可起劲,让樵兄炒几个小菜来着?”
“可神婆婆也常说我聪慧的……”,刑九自知自己笨到要死
“什么?”,飞鱼半会才领悟过来,“哦,你是说……他们夫妻俩在自欺欺人?”
刑九点点头,神婆婆总算说对了一点:外头的人常常说谎,尤其是对自己看重的人……
“你要学会去说谎……”,神婆婆还这样和他说
“不妙!”,刑九刚才被拽着匆匆离开,忘了自个的佩剑,那可不能丢,“我的剑和扇子!”
“咱们命都快丢了……”,飞鱼哪还管得了这许多,段律随时就会追上来,“是剑要紧还是命要紧?”
刑九挣开飞鱼的手,一点犹豫都不带,“剑比命重要!”
那是他们族人的神物,丢掉了九幽剑,他这个族长难辞其咎
飞鱼恼火地看着刑九往回跑,嘟囔了两句还是决定跟着他一起回去,不料人正在气头上,没留神就一脚不慎踩空,刑九没跑远,见此赶紧去拉飞鱼,却失手跟着一道摔了下去,还好他们那时离山脚只几丈高,下面也不是硬邦邦的山地,而是一条滚滚大江,水波汹涌澎湃,下流是距这里最近的城池
山城,未明,秀河
湿漉漉地从河边爬上一个“水鬼”,刑九拉开头发,哗哗吐出一滩胃水来,眼前模模糊糊地辨清是一条冷淡淡的小街,河道沿着路边,家家户户门口都架着条木板往外铺,权充桥梁,肚子“咕咕”地叫着,他费力地爬到一栋阁楼前,那门户上挂两个大红灯笼,一股胭脂香粉味飘荡,薰得他鼻子都不大透气了
抓起门上的拉环,咚咚咚!咚咚咚!
“小天,快藏起来,定是妈妈回来了!”,女孩家的轻声
门吱嘎一声开了,刑九累到站不起身,坐在门前,浑身上下不对劲,破落得和乞丐没啥两样
一个只穿着亵衣,胡乱披着长发的姑娘从门后探出头来,看到刑九还算正派的脸,“你……没事吧?”
“没有,姑娘,我想问,我这是到哪了?”,刑九一时不知怎么开口是好:他流落他乡,饿坏了,要讨饭吃?还是实话实说,他和土匪结仇了,和朋友走散了,要个住处?
“寻欢楼,青楼,我是……”,女子打量他,苦笑着,“我是乐妓……”
“乐妓?什么意思?”,刑九摸不着头脑,只能歉意地笑笑,看见女子衣裳单薄,不好意思地撇开头,“姑娘你穿得着实少了些,不冷吗?”
“我们这种人,能穿得多少?”,那女子看了他一会,终于完全把门打开来,“你……那要不,你进来换身衣服吧?”
当一只鸟爱上一朵浪花,它就只是一条会飞的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