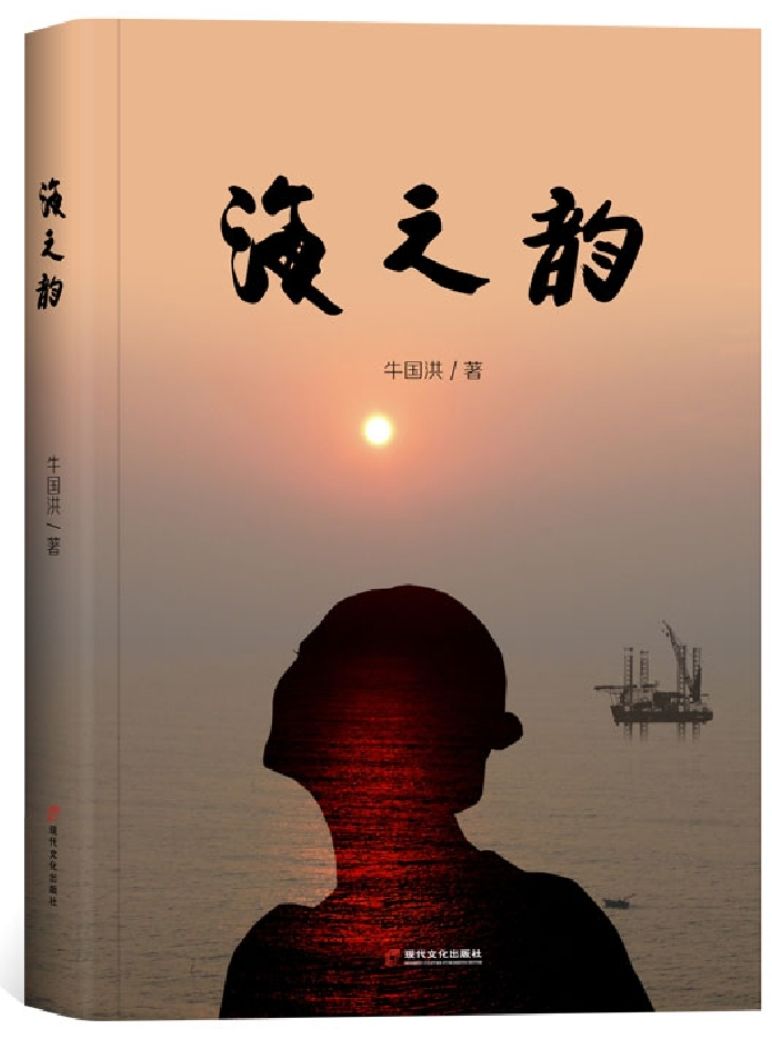刚抱着木桶放在地上,准备走。
山匪见她还算好唆使,笑了一笑,再次道:
“莫急啊,再去一趟我屋子,我那儿有一堆脏衣服,帮我抱过来,全都洗了。”
这就过分了!还真当她是打杂的么?温瑶脸色一动,冷冷:“这位大哥,洗衣服不是我的分内事。”
“呵,你是最晚来寨子的,不是你洗,还能有谁洗?别以为你给老大治了一次伤,就还真成我们山寨的贵客了!我可告诉你,你现在跟我们一样,甚至还比不上我们的资历!”
温瑶冷笑:“好啊,那不如你去跟瞿六爷说说,若瞿六爷让我洗,我就去帮你洗!”
山匪恼羞成怒:“你别用老大来压我!你以为你是谁,不就是一个刚入入寨的小喽啰么,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仍旧是掌管十八家药铺的老板了?我可告诉你,刚进山寨的都得这么做!”
说着,便一手伸过来,欲抓住温瑶,准备拽去自己屋子。
温瑶一个闪躲,对方扑了个空,更是气得不行,竟直接拔出刀。
温瑶想逃,却因为脚上绑着重重的脚镣,根本跑不动。
山匪很顺利地用刀尖直抵住温瑶腰身,狠狠道:“要是不去,信不信老子宰了你?别叫出声,否则,老子刀子不长眼,刺进去了可别怪老子!”
“你敢!我就不怕你家老大责罚你?”
“老大怎么会为了你这么个初来乍到的小白脸动我们这些兄弟!快,跟老子回屋——”
温瑶见他不停逼自己去屋子拿衣服,再看他越发轻邪的目光,终于意识到什么,眸色一凉:“你到底想干什么?真的只是让我去洗衣服?”
“嘿嘿,小白脸倒是挺聪明,”山匪目光轻薄地落在她脸上,一派肆无忌惮:“你这双小手,我哪里舍得叫你洗衣服……走,先去我房间聊聊……”
温瑶心脏咯噔一下,自己这几天一直都是女扮男装,没有哪里露出破绽啊,这土匪怎么会打自己的主意……
她是哪里暴露了女儿身么?
“我是男人,又不是女人,你疯了吗?想找女人去青楼!”
山匪嘿嘿一笑,更加满脸淫邪:“你若是女人,我还不会看你一眼!”
从没见过这么细皮嫩肉、眉清目秀的小二郎。
早就心痒难捱了。 今儿不将这小白脸搞到手,他睡不着!
温瑶顿时明白了!
我擦!这山匪竟然是个有龙阳之癖的!
他并没认出她是女人,就喜欢男人,这会儿也是想——和她搞基!
不过现在这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快走!”山匪已经基情难捱了,抵在她腰上的刀子转动了一下,狠狠威胁。生怕再闹下去会惊动了屋子内的老大。
她眼色继续冷下去,正这时,却听箭矢划过空气的声音,直直朝自己这边射来——
还没回过神,只听身边那山匪惨叫一声,后退两三步,跌摔在地上,胸前正中了一只箭!
瞿六爷在哑四的陪伴下,已经走出屋子,手里还拿着弓,此刻正冷冷看着地上的山匪。
院子外面的山匪被惊动,跑进来,看着这场景皆是一惊!
只听瞿六爷冷声:“把这个不守寨规的杀千刀的拖下去,关在宅牢中,若还没死,明天便当着所有兄弟的面,棍责三十!以儆效尤!”
中了箭的山匪还未及哀嚎,就被人拖走。
有人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看一眼温瑶,似乎不想寨内兄弟为了一个新来的受罚,不禁劝道:“老大,算了……”
瞿六爷鹰隼般的眸子厉视一眼说话的人:“算了?那你去替他受过,好吗?”
那人再不敢作声了。
瞿六爷厉声吩咐下去:“我再说一次,我烈焰寨的规矩,只要进来,便不分前辈后辈,不可在内部互相倾轧,更不欺辱兄弟!”
几人都虎躯一震,深吸口气:“下属们谨记!”
直到众人散去,温瑶才缓过神,见瞿六爷要进去,才赶紧上前两步:
“瞿六爷,刚才多谢了。”
瞿六爷转身,嗤笑一声:“不用谢我,我可不是为了你这个小白脸。他既损了寨规,便活该要受罚。还有,烈焰寨中若再遇到有人欺辱你,你便直接告诉我。”
说罢便摸了摸还没完全好的左臂,估计是刚才用力拉弓,扯到了伤口,皱眉骂了声:“还真疼!擦!”
哑四忙搀着瞿六爷先进去了。
温瑶则深深呼吸了一口气。
这个瞿六爷,倒也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可理喻。
只是走错了路,倒是可惜了。
**
又是两日划过。
中午,待瞿六爷吃过午饭,温瑶进去给他换药。
平日都是她调制好药,由哑四去给他换药、上药。
但今日哑四有别的事,便有她亲自给瞿六爷换药了。
瞿六爷退去上衣,趴在床榻上。
她瞥一眼他精壮结实的上半身,这一看,倒是一怔。
倒不是因为害臊或者尴尬。
作为医生,眼里只有患者,根本不在意男女性别。
况且,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两年多以前,她便也这样照顾过那个男人……
脑子里浮现出元谨,她立刻压下念头,目光再次停留在瞿六爷的身上。
让她惊讶的,是这男人身上的伤痕。
古铜色健康阳刚的皮肤上,层层叠叠都是新伤旧痕。
蜈蚣一样,爬满了男人的后背。
那伤痕,看起来,要么是刀伤,要么是鞭打过的,要么是烫过的。
看着惨不忍睹,触目惊心。
就算看过不少病伤,她还是为之心尖一动。
每一道疤痕,都应该代表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吧。
床榻上,瞿六爷见她久久没动静,这才回过头,看见她的眼神,似乎猜到了这小白脸在想什么,哼笑一声:“怎么,怕了?”
温瑶回过神,这才走过去,弯下腰,给他拆起纱布,摇头:“没有。只是没想到这么厉害的瞿六爷,身上居然有这么多伤痕。我以为,只有瞿六爷让别人受伤呢。”
瞿六爷倒也不在意她的讥讽,双臂折着,趴在床上,喃喃——